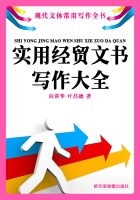王学泰:自清末以来出了数代知识分子,李泽厚1978年写的《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把知识分子分为六代,“辛亥的一代,五四的一代,大革命的一代,‘三八式’的一代”,“再加上解放的一代,(19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和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的一代”。李文发表之后至今又可以说产生了两代知识人。这八代知识人到底有多少人,由于标准不同,也难以数计。各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学养、思想意识有很大差别,社会责任感也有重有轻。我属于李泽厚所说的从40年代至60年代的一代。他说:这一代人“虔诚驯服,知识少而忏悔多,但长期处于从内心到外在的压抑环境下,作为不大”。最初看到这个意见不免有些惊悸,仔细一想也确实如此。我们不仅欣逢不许读书的时代,而且那也是被训斥要做“驯服工具”,还要时时不忘“要斗私批修”的时期。在这样的条件下,造成我们这一代无知和卑琐也就不奇怪了。因此,我在很早以前就对社会大转变的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有几分向慕和敬仰,成为我心仪的对象。其中我最为感佩的还是蔡元培、鲁迅、胡适。我之所以钦佩除了他们的博学多才以外,还有三条:
第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强烈的社会关怀,对于当时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强势群体的为非作歹,他们都以自己习惯的方式进行批评、批判,扶助处于弱势的社会群体。批评与批判不一定都是体制外的,体制内的批评更能搔到痒处。蔡元培、胡适有时是属于体制内的人物,但是他们从未放弃对当时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批评的权利。
第二,明确而坚定的独立自主意识。他们不仅能够顶住横逆势力的压迫,更重要的是在他人的奉承之下,也不就坡下驴。鲁迅讲过一个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故事。易卜生写了《玩偶之家》以后,受到社会上的普遍赞扬,一次力主妇女解放的组织宴请他,说他为妇女解放做了很好的工作。易卜生站起来致答辞时说:“我是在写戏,并没有其他的意思。”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作家身上,大多是要顺竿爬的,就是我恐怕也难以免俗。而鲁迅就是不肯顺竿爬,宁肯“煞风景的人”。胡适对他人的赞扬也常常持批评态度。
第三,宽容精神。胡适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其实鲁迅也是有宽容心的,特别是对于青年人。
朱竞:您认为中国20世纪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是哪些人?
王学泰:上世纪优秀的知识分子大多生活在工20世纪一二十年代,也就是李泽厚所说的辛亥的一代。读一下包天笑所写的《钏影楼回忆录》就可以感到这一点,该书所记多是当时三四流的知识分子,就是这些人物也多是个性鲜明,不随人俯仰,具有独立人格,有学、有品、有趣的人。把他们与我们这些一望尽是“黄茅白苇”的芸芸众生相比较,则高下立见。为什么一二十年代知识分子优秀者特别多呢?其关键在于:他们真诚。那时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间,新型的知识分子是刚刚从旧式士大夫进化来的,他们既有传统士大夫的朴诚,又有新式知识分子的敏锐和献身精神。他们大多出身于富裕之家,或者本人就是在仕途上有所成就的人士(如蔡元培出洋留学时已经是翰林了),他们不缺少物质上的东西,一心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没有什么个人的打算,更不是解决个人出路问题。因此,他们的政治理念、救国方案尽管有很大差别,但一心为国的赤忱是后世许多人无法企及的。
鲁迅称这些人为“老新党”。他说,甲午战争之后,他们以为要救国“于是,要‘维新’,便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看‘算学笔谈’,看‘化学鉴原’;还要学英文,学日文,硬着舌头怪声怪气地朗诵着,对人毫无愧色。那目的是要看‘洋书’,看洋书的缘故是要给中国‘富强’。现在旧书摊上还偶有‘富强从书’出现,就如目前的‘描写字典’‘基本英语’一样,正是那时应运而生的东西”。他还说:“老新党们的见识虽然浅陋,但是目的有一个:图富强。所以他们坚决、切实。学洋话虽然怪声怪气,但是有一个目的:求富强之术。所以他们认真、热心。待到排满学说播布开来,许多人就成为革命党了。还是因为要给中国富强,而以为此事必自排满始。”从鲁迅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这一代的真诚与献身精神。蔡元培、章太炎、陈天华、秋瑾、宋教仁都是其中杰出的代表,鲁迅可以说是他们的殿军。二三十年代上海是中国新知识分子的摇篮,然而,此时跑到上海的人们多是寻求个人出路,上海又是殖民化很深的大都会。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新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比他们的上一代逊色很多。求个人出路的迫切性远大于“图富强”(这里仅就一般而论),因此连流行的畅销书都变了,以前是“富强丛书”,现在是“描写字典”“基本英语”,这活画出两个时期知识人不同的精神面貌。章克标的《文坛登龙术》在三十年代大畅其道,正是那个时代以文化谋生的知识人的精神写照。鲁迅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大会之后,回家写信给朋友说,他所见的那些左翼“革命”青年作家“皆茄花色”。这种太过分注重个人利益、太精明的人生就不免堕入传统中的游民文化的恶道。我在拙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提到了“游民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所谓“知识分子”当然非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只取其有一定文化知识之意),游民知识分子的特征在于价值取向的非规范性,而且为了个人利益,能把这种非规范性推到极端。鲁迅曾讽刺这种类型的人说,当有些气力与人竞争的时候就信奉达尔文主义,当需要别人帮助时就推崇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各有各的用处。鲁迅自1927年以后到他去世之前的杂文大多是剖析这一代知识人心路历程的。
这一代知识人对于以后(可延续到八九十年代)的知识人影响极大,而且大有一蟹不如一蟹之势,因为后代的知识人还缺少了他们那个自主选择的过程,即便是有些选择的话,也是“鸟笼中的选择”。当然这些说的是总的趋势,鹤立鸡群、出污泥而不染者,无代无之。这是不言而喻的。近世以来,废除了私有财产,人们没有了赖以维持独立的经济基础,人的独立性也就被剥夺了,知识人也是如此。当有权者掌握了你的饭碗的时候,说什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侈谈。侯宝林有个相声叫《关公战秦琼》,其中有个韩复榘老太爷叫演员唱“关公战秦琼”,演员没法唱,老太爷发话说:如果不唱,不管饭,饿他三天看他唱不唱?因此,没有了个人财产,自由必然消失,这样精神退化就是必然。50年代以来,知识界中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作媚世媚俗之论、被批判围攻而不屈不挠、始终不肯低头认错者,不过一二十人而已(指为世人所知的)。现在仍为广大民众所知者如陈寅恪、梁漱溟、马寅初、周谷城、李平心等人,是不肯认错中的佼佼者。
这些人中除了对李平心不太了解外,其余四人无不是早就享大名的,就是与当时的高层领导也有较密切关系的。大家常说的陈寅恪,实际上陈氏不仅门第显赫,四海知名,而且陈家在血缘、婚姻、交往上与国共两党某些要人皆有关系,所以他提出“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政治”,这种空谷绝响的声音也没有受到什么特别的待遇。如果换上冯友兰、贺麟这样只与国民党有较密切关系的人物,其结果就很难逆料,而发生在陈氏身上只不过给学界增加了点谈资罢了。周谷城两次与批判他的所谓“马列主义学界”反复论辩,决不认错、屈服。而且他们只是坚持个人的观点,与社会关怀关系不大,他们仅能算孔子所说的“狷者”,是“有所不为”的人。真正关心国计民生,又能坚持己见,只有梁漱溟、马寅初两人而已。梁先生有点旧时代的文人士大夫气,他内心深处有些以忠臣自负的观念;马先生是新知识分子,是勇于坚持真理的人,但马先生也不是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识”有很深刻的认识,上世纪50年代初,他老先生做北大校长时是要求“知识分子改造”的首倡者。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能称得上的知识分子却寥寥无几,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剧。
二、关于人生和个人体验
朱竞:您最痛苦和耻辱的体验是什么?讲一件苦恼的事。
王学泰:90年代末,与孩子一起看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其中有个情节对我震动很大,引起我许多回想。剧中演道,乾隆皇帝大兴文字狱,用穿凿附会的办法使许多文人只因为只言片语,便陷入罪中。刘罗锅认为这太荒唐了,他准备好奏折,打算面见乾隆皇帝时,把这件事情说清,制止文字狱泛滥。他入宫见到皇帝正准备开口时,听到文武大臣的一片赞颂之声。赞颂文字狱怎么样打击了梦想复辟明朝的“反动分子”,又如何保障了大清的江山。在这种氛围下,刘简直没有了发言的可能了。此时他要面对的不仅是皇帝,而且还有那些已经“一边倒”的群臣。刘罗锅十分尴尬,不知该要干什么了,他满面惭愧,汗如雨下。这使我想起1971年在北京房山县农村我参加“一打三反”运动的情景。
一次在某中学召开的揭发批判会上,军宣队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材料,揭发某位刚刚从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的教师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并且说他仇视毛主席,用气枪射毛主席像(其实这个材料是文革初期打派仗时对立派同学所揭发,大家都知道不可靠)。这个材料一抛出来,不管真的假的与会者都表现出“极端”的气愤,有的老师为了表现自己对这个“反革命”的痛恨还上手打他。这位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教师,面色煞白,一言不发,低头弓腰,站在人群之中,黄豆大的汗珠从额角渗了出来。我们几个师院来的都知道他是冤枉的,可是谁也没有勇气为他说句公道话。在巨大的压力下,他精神失常了,后来被送进了神经病院。听说90年代末,他还住在精神病院。这件事过去了近三十年,我也经历了许许多多事情和苦难,“一打三反”仿佛早就该忘记了。可是稍有类似的情境出现,就有所触动,可见此事对我影响之深。
朱竞:对您影响最大的书和人是什么?能说说您和它(他或她)的故事么?
王学泰:我是学中文的出身,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文学作品。古今三位作家对我影响最大。即司马迁、杜甫、鲁迅。《史记》《杜工部集》《鲁迅全集》都是我读过数遍的。《鲁迅全集》主要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时没有书可以读,所以我读了鲁迅和马恩的集子(二十卷本)。有人说文革禁了许多书,不对。禁书是不准看一些种类的书,清代乾隆时期禁书最多,也不过近两三千种而已。而文革中只许读几种书,如《毛泽东选集》、“马恩全集”、《鲁迅全集》之类,除此而外,全属禁止阅读的“封、资、修”。文革前我就喜欢鲁迅的书,但理解不深,到了文革期间,反复读鲁迅,证之以现实,才真正认识到他的伟大。中国有幸出了鲁迅,他是中国历史的光荣;中国也不幸,其走过的道路,往往不断论证鲁迅的远见卓识。中国知识分子有幸,有鲁迅这样人物为我们作出榜样;中国知识分子也不幸,有了鲁迅这样的人物,益发令我们感到羞耻。
高中时读过一二百首杜甫的诗,但觉得不如李白的诗发扬蹈厉、精彩逼人。也是经历苦难,当我一人下放到农村时,深夜孤灯,再看杜诗感觉就不同了。仿佛自己的感情和想法都靠杜甫替我表达了出来。而且杜诗中所表达的那些从人性迸发出的至爱,给读者的抚慰也只有在不幸中才能更好地体会到。《史记》也是在农村读的。
“文革”到达“批林批孔”阶段时,因为有些不同的想法,进了监狱。对犯人看书控制的非常紧。“评法批儒”时好了一些,一些线装书都可以叫家里送来。《左传》《韩非子》《小仓山房集》《文心雕龙》《诗品》《龚自珍集》都送了进来,只要说一下这些都是“法家著作”就可以了,当时“法家”几乎是与“马恩列斯毛”平起平坐了。可是鲁迅的书却不让送。有一次中队开会,该“指导员”训话,讲到为什么不让送鲁迅书的问题。他说:“有些犯人的家属,送来了鲁迅的书,我们没有让收,过去没有讲为什么这样做。这次讲一讲,鲁迅的书是揭露旧社会的,你们是揭露新社会才犯了罪。让你们看鲁迅的书,你们更要揭露新社会了。所以鲁迅的书不能看。以前不让送,没有讲道理,这次讲了道理,你们口服,心里也会服了。”
朱竞:您是否有成功感和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