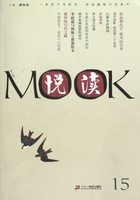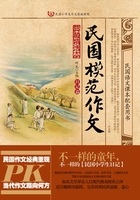《水浒传》还通过它所创造的影响受众。书中许多话语成为流行语,活跃在后世人们的口头,甚至成为人们认识社会和行为的指导。例如“好汉”这个词唐代就有,可是那时多指读书人,而《水浒传》中专指的是绿林英雄。这种词义被后世人们普遍接受。《水浒传》之后人们便称那些勇武有力、敢于作奸犯科,又稍有点义气的人们为“好汉”。过去我们碰上劫道的,你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为好,现在就可称之为“好汉爷”了。又如拦路抢劫,入户偷盗,总觉得不是什么好事情。有了《水浒传》的智取生辰纲的故事,人们知道“不义之财,取之无碍”这个短语,而且在《水浒传》的语境中这句话是绝对正确的。于是,凡劫人财者,无不以此为说。这“不义之财”是谁定的?反正由强取者定,实际上它就成为“强盗逻辑”。其他如“聚义”“江湖”“招安”“上梁山”“逼上梁山”“替天行道”“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等等。它们既反映游民的思想意识,也表达了他们的向往。这些话语所负载的思想情绪播及到各个阶层,对无依无靠的游民影响最大,因为《水浒传》告诉他们的道理符合他们的生活体验。
《水浒传》中特别歌颂“聚义”,描写了与主流社会对抗的人们,在与相同命运的人结合起来之时所显示的力量。《水浒传》为游民的组织化构造了一套完整的操作和运行的规则,这与它建造的话语体系是相辅相成的。后来许多游民组织借鉴于《水浒传》,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天地会最为明显。
天地会的建立及其性质学术界都有争论。但是它建立以后受到的《水浒传》影响则争论不大。加入天地会手续繁杂,其“入门诗”开头两句“桃园结义三炷香,有情有义是宋江”,就可看出受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影响。天地会有严密的组织结构和细密的组织规则,如天地会的内外八堂的建构都是借鉴于《水浒传》的。《水浒传》中游民懂得了江湖上同道的交往应该是有规则的,这就是被江湖上认为最高准则的“义气”。实际义气是游民的道德,义气正是由《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描写而登上江湖殿堂的,从此深入江湖人的心,甚至极大影响了其他阶层的人们。为了义气不怕两肋插刀,“江湖义气第一桩”这种游民的通俗道德观念的如此深入人心,应该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功劳。《水浒传》创造的江湖话语,也由于这些话语活跃在人们的口头,它们被江湖人所接受,并成为江湖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或基础。
《水浒传》书中的江湖是丰富而生动的,在其受众中有极广泛的影响。鲁迅所说的我们的社会有“水浒气”“三国气”,这固然是由多种原因所造成的社会存在,不能否认《水浒传》的广泛传播也是其原因之一。清代学者钱大昕在《正俗》中说,“三教之外,还有一教”,那就是“小说教”,极言小说对于民众思想影响之大。现在也是如此。因此通俗艺术的作家们更应有社会责任感,更要慎重。令人遗憾的是,现在一些通俗艺术的创作者,历史观念和思想观念甚至是落后于古代的江湖艺人,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产生的作品搬上银幕、屏幕,把他们播散到更广泛的民众中去。其结果可想而知。
傅光明:有有问题的朋友吗?找一个或者两个。
听众提问:王老师你好,请您说一说在文革当中,评《水浒传》的好坏跟现在的观点有什么区别?
王学泰:文革中的评论是一种政治运动,不属于“水浒”研究的范畴。是“四人帮”根据毛主席说的几句话搞的一次政治运动,其目的是针对周总理、邓小平副总理的。跟我们的研究没有任何关系。毛主席对《水浒传》的评价也是一家之言。但其晚年对《水浒传》的评价与早年不同,如果按他晚年说的作为定论的话,我觉得我也有不同的意见。比如说《水浒传》不反皇帝,被认为是《水浒传》的最大缺点,我觉得不反皇帝不一定是什么缺点。鲁迅先生也说《水浒传》不反皇帝,但鲁迅先生的出发点和毛主席不一样,这里就不细说了。我认为不反皇帝不是什么缺点,中国人想做皇帝的多了,不想做皇帝倒是一个优点。中国甭说那些起来造反的皇帝想做皇帝,就是没能力的人也想做。每年中国要出好多皇帝,直到现在还在出皇帝,皇帝给中国造成的危害还少吗?民国时章太炎先生对康有为很反感,他说过:有人说康有为想做皇帝,这没有什么,皇帝人人想做;康有为的可恶之处在于他想当圣人,千古以来圣人就一个。所以说我觉得不反皇帝本身并不是什么缺点,《水浒传》之所以这样写,我们要考虑它出现的时间,当“水浒”的故事最初流播在平话艺人之口时,是南宋初年的临安。
当时金人入侵在即,在南方流行的“忠义”,无论是什么要想被社会普遍接受,必须打出“忠义”的旗号,这样才能在社会上通行。反皇帝不仅仅是主流社会不允许,当时的社会风气也不能接受。此时“八字军”就在拱卫着杭州,他们本是北方平民组成的民军,因为抗金,被视为是“忠义”的代表,后来辗转到南方,受到南宋官民上下的欢迎。“水浒”的故事之所以强调“忠义”正是在这种社会风气下产生的。《水浒传》在南方的故事之所以与“忠义”联系起来,与抗金非常有关系。当时怎么能反宋皇帝,除非你与汉奸刘豫等合流,刘豫做了皇帝,受到万众斥骂。难道能跟他们同流合污吗?所以说不反皇帝不是《水浒传》什么缺点。应该说明,这与它产生的时代背景有关系。中国两千多年来都是皇权的思想意识作为主流意识,甚至皇帝没了之后,人们的皇权意识还没有消失,现在到处歌颂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可以看出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匍匐在皇权之下。所以说反皇帝根本不是这《水浒传》所要深入描写的问题,因为这不是它要反映的主题。我特别关注古代通俗小说在社会上的负面影响。这些社会现象确实给我们进入法制社会和公民社会造成了障碍。我不知道大家阅读这些作品时有没有这种感觉?
傅光明:《水浒传》反映了江湖人的生活,王先生刚才在演讲当中也为我们勾勒出了水浒中的游民世界。至于游民的思想、生活特征和行为特征,我想看了《水浒传》电视连续剧的观众会对刘欢那首歌中的一句歌词印象深刻——“该出手时就出手”。我想这种对于造反有理的游民意识和游民理念,一定得历史地、科学地、客观地和理性地来分析和对待。最后感谢王先生带给我们的精彩演讲!
庙堂很远,江湖很近
——访著名学者王学泰
此篇发表于《南风窗》(2008年第7期),熊培云先生大约在2008年春末夏初到舍下采访,后来又在电话与电邮往来中做过数度修改。
转型期中国向何处去,一直为世人瞩目。在有答案之前,必先对中国社会的隐性与显性的特点有所认识。为更好理解此一时期的时代特征,窥视未来前景,本刊特地就若干问题访谈了著名学者王学泰先生。
“小说教”里的中国人
熊培云:记得有一年在柬埔寨旅行,当地人就和我说很喜欢不久前热播的《水浒传》。
王学泰:清代有个史学家叫钱大昕,他提出自古有儒、道、释三教,但从明代以后又多了一教,叫“小说教”。为什么呢?因为小说太吸引人了,不仅士大夫们喜欢,而且连不识字的妇女、儿童以及连圆都画不好的阿Q也都喜欢,论及影响它比儒、道、释三教还要大些。像阿Q唱的“悔不该手执钢鞭将你打……”就是《龙虎斗》的唱词。钱大昕说,如果说佛教、道教等是教人为善的话,那么小说教则是教人“作恶”。他主要举了两个例子。一是以《水浒传》为代表的“以杀人为好汉”的一类作品,包括戏曲、曲艺;一是以《西厢记》为代表的“以渔色为风流”的一类作品。当然,现在不同于那个时代,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长期以来,像《水浒传》、《三国演义》那样的作品既反应了底层社会的游民意识,同时也强化了这种意识的扎根与流行。
熊培云:这些小说在中国社会运动中究竟起了怎么样的影响?
王学泰:宋以后,中国社会受戏曲曲艺影响极大。不仅在民间的,如太平天国运动时的装束、官职、作战方式,受通俗文艺影响也很明显。义和团中的成员在重大活动中都要化装为通俗文艺中的人物(在义和团中这些人物变成了神),如化装成孙悟空、猪八戒、黄忠、马超等。包括辛亥革命也一样,它受到天地会的支持,而天地会也是一个戏剧化程度很深的组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江西有了苏维埃共和国,大家不懂苏维埃是什么意思,就以为最初来这造反做皇帝的是苏兆征,而苏维埃则是“太子继位”。
熊培云:透过这些分析,此时我们更能体会现在的帝王戏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究竟起了多少负面的影响。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塑造双重性格,一是游民,二是臣民。
王学泰:游民性格不是我空想出来的,而是根据《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等总结出来的。这些小说由江湖艺人初创,再经过文人改写,因此留下了许多游民痕迹。中国历史表现出的“五十年一小乱,两百年一大乱”,社会垂直流动,变化最大的两个阶级便是皇帝与游民。有时皇室降到最底层,甚至性命不保,而游民则有可能做了皇帝。比如朱元璋,有人说他是农民,他没有土地,数年间做游僧,以乞食为生,真正的身份是游民。
熊培云:统治者对这些具有反叛性质的小说通常采取什么态度?
王学泰:历年来统治阶级对类似作品采取一种压制的态度。比如清代甚至为此颁布圣旨,禁止一些作品的出版和演出。《水浒传》几度被禁。不过有时它也会被皇家改编。如乾隆年间的宫廷大戏《忠义璇图》便是关于水浒人物的。也就是说,在反传播的同时,统治阶级也想将其纳入到主流意识形态中去。
熊培云:《水浒传》是如何传播并影响中国社会文化的?
王学泰:《水浒传》除了用其生动的故事(如逼上梁山、智取生辰纲等)昭示它所说明的道理外,还通过它所创造的话语影响受众,我称之为“话语植入”。书中许多话语成为流行语,活跃在后世人们的口头,甚至成为人们认识社会和行为的指导。例如“聚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逼上梁山”“替天行道”“好汉”等等。“好汉”这个词唐代就有,可是那时多指读书人,而《水浒传》则专指的是绿林英雄。这个词义被后世人们普遍接受。《水浒传》之后,人们便称那些勇武有力,敢于作奸犯科,又稍有点义气的人们为“好汉”。过去我们碰上劫道的,你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为好,现在就可称之为“好汉爷”了。又如拦路抢劫、入户偷盗,总觉得不是什么好事情。有了《水浒传》的智取生辰纲的故事,人们知道“不义之财,取之无碍”这个短语,而且在《水浒传》的语境中这句话是正确的。于是,凡劫人财者,无不以此为说。这“不义之财”是谁定的?反正由强取者定,实际上它就成为“强盗逻辑”。
熊培云:哲学家黎鸣先生曾经和我谈到,中国的四大名著其实反映了“四大绝望”:《三国演义》里“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使天下人负我”的统治者,《水浒传》里贪赃枉法的官僚,《西游记》反映社会体制的固化和僵死及对未来深沉绝望,而《红楼梦》体现的是传统儒家理想的幻灭,等等。
王学泰:和《红楼梦》不同,《西游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是由说书人等慢慢发展来的,反映的是底层的事情。我想黎鸣讲的四大绝望更多是从精神层面的。专制社会本来就是没有前途的社会。中国社会在过去一直没有逃出战乱、治乱的循环。但是,在我看来,一切“乱”其实都是始于“治”,或者说是“治中之乱”为“未来之乱”埋下伏笔。
贵族传统与游侠精神
熊培云:如何理解中国人津津乐道的“侠义精神”?《水浒传》热播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便出手”。
王学泰:“侠义”的“精神”实质是什么?我认为最少有两点,一是为他的;二是反主流的。它最早源自游侠。《水浒传》是游民讲给游民听的故事,游民自诩为侠,实际上宋代和以后是“江湖侠骨已无多”时代了。《水浒传》中只有鲁智深才算侠,他不仅反主流,而且救人不求回报。相反,其他人的打抱不平大都是从自己利益出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