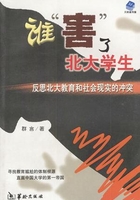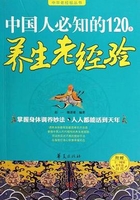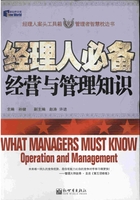天桥的艺人个个能说,所谓“金皮彩挂,全凭说话”。前一句是江湖隐语,“金”(或写作“巾”)是算卦的,江湖上有七十二“金”之说,也就是说算卦看相可分为七十二类,“皮”江湖上卖药的,“彩”指变戏法的;“挂”指打把式卖艺的。也就是说走江湖卖艺,第一要会说、能说,其次才是“艺”。但只能“说”,没有“艺”,事情就走向了反面。在天桥我也见过只能练不能说的,这就是练武术的“山东徐”。他叫徐源伦,他往往在非黄金时间演出,一般是上午九点以后,下午两点以前。我见他上场时只是低着头在地上写下自己的字号——“山东徐”。他把“山”字中间那一竖写得特别长,然后他就操着山东口音说几句的场面话,不到一分钟就开练。他一套七节鞭虎虎生风,能够定点打物。练完了,面不改色,心不跳,口不喘,可是看热闹的人纷纷走散了。挣不了多少钱,谁知道这一脸尴尬的汉子就是1947年全国武术比赛中梅花螳螂拳的冠军呢!
附:老天桥的复兴恐怕不那么容易
《新京报》一个标题引起了我的兴趣,《宣武欲兴4000万,再续天桥记忆》。这篇报道中说“天桥演艺文化是老北京市民文化的缩影”“天桥地区与生俱来的文化历史等优势是推动宣武区开发演艺文化产业的重要因素”。因此,宣武区将投资4000万元,启动天桥复兴计划。以修建城南文艺休闲乐园为开端,然后,整治天桥乐茶园及周边环境,并建天桥演艺中心和民俗博物馆。计划很庞大,初看也很兴奋,可是深入一想,恐怕不那么简单。
天桥是我幼时看热闹、玩耍和开心智的地方,给我留下许多温馨快乐的记忆。我还写了一篇《天桥杂忆》,收在前几年出版的一个集子里(《平人闲话》)。每当想到天桥总是与童年的无忧无虑、贪玩欢乐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时光如能倒流,老天桥又重现,当然很高兴。然而,我们毕竟不是生活在童话中,时光隧道也只是幻想。当老天桥的生存背景都不存在的时候,再造老天桥大约只是个美丽的幻想。
老天桥是什么?从经济角度看它不过广义的综合的跳蚤市场,是满足购买力不高的群体消费需求的。清代北京内城有八旗居住,汉人一律住在外城(乾隆之后,汉人高官有在内城赐第的),外城形成“东富西贵、北贱南贫”。这是说外城东部(崇文区)多手工工厂,有钱人多;西部(宣武区)多汉官居住,地位较高;北部靠正阳门一带多娱乐业,被社会轻贱;南部靠永定门一带居住的多是破产入城谋生的农民,很穷。天桥正处在东西南北的中心,逐渐形成了以满足穷人消费为主的市场。南城形形色色的穷人们也要消费,可是珠市口大街(外城的南北以此为界)以北较高档次的消费,他们一般承受不了,于是就有了应运而生的天桥。
天桥首先是个综合市场,卖什么的都有。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穷人,穷人那一点点物质上精神上的需求确实都能在这里得到满足。如吃饭、喝酒、喝茶、买估衣(旧衣服)、洗澡、买药、下棋、听各种曲艺、看杂技、听戏、看电影等等。凡是穷人能想到的那里都有,而且一切消费又那么便宜。廉价是天桥最大的特点。至于所提供商品与服务的品质,是不是像现在一些回忆中写得那么好,是不是能做到物美价廉,则不能一概而论。
一般说“一分钱,一分货”,拿到天桥卖的,大多是旧货或者处理品,或来路不明的商品,不会比正经商店好。这些我们从一些老相声段子都可以感受到(如《卖估衣》《卖布头》)。这是物质上的。就活跃于天桥的艺人来说,也并非都是艺人中的精英。那时艺人作艺的正经地方是珠市口大街以北的剧场茶楼,在那里扬名立万,被观众追捧。天桥演员很少红的,天桥京剧老生演员中的梁益鸣艺术不错,声音做派很像马连良,大家称之为“天桥马连良”。冠以“天桥”就有点讽刺或鄙薄,是歧视而不是赞美。解放后提高了底层艺人的地位,他才能拜马连良为师。珠市口以北剧场中有位置的艺人都害怕沦落到珠市口大街以南的天桥撂地。我读过一篇老艺人魏喜奎的回忆文章就写到艺人这个心理。当然我们也不能以撂不撂地划线,认为撂了地的艺人都是才艺不高的。因为沦落天桥有多种原因,不单单是才艺一个因素。不过要红,最终还是要冲出天桥,而不是回归天桥。
说到这里,是不是“天桥演艺文化”毫无价值呢?当然不是,中国演艺中的许多门类是发源于民间的,其演出地点也往往是从撂地走向剧场的。百年来的相声产生发展就是一例。清末以前说的“相声”是口技,我们现在熟悉以逗笑为主的相声是产生于清末国丧期间戏剧演员不许化妆彩唱,当时一位名丑为了生活在天桥撂地以说些笑话谋生,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相声。相声是从天桥走出来的,但是成了名的演员一般是不会再回天桥了。作为这些演艺门类的发迹地,天桥还是值得纪念的。另外,撂地演出,与观众面对面,亲和力强,便于演员即兴发挥,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当这种演出形式消失的时候,易于引起人们回忆。总之,老天桥这种满足人们廉价消费的市场,很难存在于工商业高度发展的现代;但把它做成一个博物馆,把某些经营方式(如撂地演出)做成非物质文化遗存保留下来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附中小记
1954年是教育大发展的一年,中小学都在踊跃招生。那年北京师大一附中的初一年级一下子招了10个班。如果按照一班45个人计算就有450人了。这么多学生肯定超过了学校的容纳能力了。五十年代,北京师大附中正常招生额是每届4个班,3个男生班(当时是男女分班的),1个女生班;我们那届10个班都是男生班。到初二时,因为要求住宿的人多,附中的学生宿舍只有两处,容纳不下,才从10个班中抽出2个班,调到一○一中学(当时还称为二附中),剩下8个班,直到毕业。
校园剪影
从师大附中毕业以后,只回去过两三次,还是去附中本部。师大附中本部在和平门大街东面,校门朝西。进门就是篮球场和大操场,再里面就是几个小院。它除了图书馆楼外都是平房,容纳量是很有限的。我们这届学生在本部对面的北京师范大学原址上课。而老师大的校园我已经有四十多年没有回去了,记忆也已影影绰绰了。这里写到的校园只能说是一些片段的剪影。
那时北师大已经在北太平庄盖了新的校舍,大多科系早已搬走,只留下了音乐系、美术系高年级的学生在那里坚持到毕业。这些未来的艺术家们,生活随便,带有点浪漫气质,例如夏天里,男女同学穿着短裤、背心、拖鞋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傍晚时,成双成对的男女散步谈心,这些在当时都是不多见的。
大批大学生已经迁走,偌大的校园空出了许多。靠北部的房子给了教育行政学院,这是培养教育系统干部的学校,当时它只是培训从各地来的中学校长和地方教育局的领导;我们入学不久社会上就开展了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肃反运动,教育行政学院搞得热火朝天,有时到他们所在的院子去玩,要听听屋子里开会便经常可以听到激烈的质问声、叱责声、谩骂声和怯怯的乞求声。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只是让我们感到社会真复杂。
大学的校园自然比中学宽大好多,附中在大院的南部,包括运动场,两栋清末民初建的半西半中式教学楼,一座办公楼,紧靠南头的一个院子作学生宿舍(当时住校很容易,约有百分之三十的同学住校,最初我没有住校,到初二才住校)。南院有正式的足球场,有四百米跑道的运动场,运动场的周围植有高大挺拔的杨树,南北院都有篮球场。运动场的西南角是大礼堂,学校开大会、演戏常常在这里进行。校园里还套着许多小院子,像迷宫,还没有脱离小孩儿气的我们,常常在院子里捉迷藏。院子里树木特别多,我有个不良的习惯,爱走路看书,当时北京只有一百万人口,街上很空旷。在校园里走路看书比外面还危险,我几次碰到校园的树上,前额被碰破,从鼻梁骨往上常擦红汞水(当时叫“二百二十”),为此,同学还给我起个绰号“串红”。校园的中心有座钟,这是一座人工敲打的钟,竖在花坛之中。我们的上下课就靠它报时,后来才安了电铃。这座钟是1949年师范大学全体毕业生送给母校的礼物。在钟座上还刻有我们老师的名字如钱雱……
附中的图书馆藏书极为丰富。不要说在一般中学,就是与历史短的大学相比较也占上风。图书馆在四楼、五楼。下面三层是高中教室,每层一个年级,每个年级四个班。也就是说书库至少有四间教室大,藏书至少在十万册以上。我在这个图书馆曾经借过解放前出版的书。如《宋词通论》《宋诗研究》等。
师门记盛
早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说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在于有大师。中学也是这样,好的中学不一定有好的校舍,但一定要有德才兼备的好老师。北京师大附中就是如此。它不仅有众多的好老师,而且有一些名师——也就是名闻北京中教界的优秀教师。有的老师讲课之佳甚至带点传奇色彩。例如,时雁行先生是附中著名的语文教师,我只听过他的讲座,没有听过他的课,因为他教高中。传说他讲课能让学生听得如醉如痴,有个高中同学说:“听时先生讲完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和《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比听一场梅兰芳的戏都过瘾!”又如韩满庐先生是教数学的,是位年高德劭的老教师,听说“范氏大代数”是他翻译过来的。师大附中的体育教师都是正规体育系毕业的,是有学问的体育老师,不像有的中学体育教师用复员转业军人来凑合。听说张汝汉老师是清华体育系毕业的,是马约翰先生的高足,北京的“三铁(铁饼、铅球、标枪)冠军”。五十年代师大附中的排球常在北京市运动会上拿冠军,听说其原因就在于有张老师的指导。1957年张先生被划为“右派”以后,这个荣誉也就丧失了。
学生一般爱传老师的毛病和缺点,如果老师的优点长处能够在学生中广泛传播,那是因为这些优点长处给学生留的印象太深了,他们以有这样的老师而自豪。实际上我亲历的优秀老师也很多。经过了四五十年的变迁至今记忆犹新的是钱雱老师、王树声老师、朱正威老师。钱先生并没有给我们上过课,她是我们这届的教导主任。因为我们在师大旧址上课,附中本部管理困难,有点鞭长莫及。于是在这边另设教导处,钱先生任主任。我们称她为钱主任。她可能是学化学的,1949年毕业于师大。她虽然年龄不大,比我们这届学生也就大十多岁吧,可是她那慈爱的微笑好像母亲。管理四百多个半大小伙子,也不容易呢!男孩子爱闹事,有时甚至发生肢体冲突,在楼道里扭作一团。
她还敢于给这些浑小子去拉架,她那瘦弱单薄的身躯真是经不得他们的推来搡去的。上初二时,10个班分走两个班。我从六班调到一班。我初到这个班时,班上的同学欺生,常找我的麻烦,有一天实在忍受不了,就找到钱先生(其实这事本来不归她管),她与我谈了一个下午,从上学的目的说起,一直说到不应以小是小非处世。这次谈话给我留的印象很深,可见当时老师的耐心。钱老师有非凡的记忆力,直到七八年后,有一次我在和平门大街遇到她,还在十米以外,她就高声叫:“王学泰。”上学时我还是个小孩子,一米六高,此时我已是一米八的大人了,她还能认出我来,使我非常感动。那时已是文革前夕,她处境不好,调离了师大附中(仿佛是调到九十五中),鬓边已经有了丝丝白发。
初中一年级时,王树声先生是我的班主任老师,他是教自然地理的。那时的王先生面白如玉,高而直的鼻子架着一副银丝眼镜,是典型的现代白面书生。他讲课时姿态及声音都很优美,我觉得比现在一些电视播音员的声音还好听。他为人和蔼,无论在什么情况都是面带笑容,我不记得他生气时的面孔是什么样子的,也许我没有见过他生气,不过教初中男生班的老师没有生过气是不能想象的。王先生与同学之间是一种完全平等的关系(五十年代初还是很重视师道尊严的),同学们聚在一起时,他也常常加入进来。有一次教室里同学们围成一圈,王先生也站在最外层向里面看,我从外面进来,也想向里面看看,就用不太干净的手扒着王先生的肩膀向里面看。王先生穿的是一件洗得非常干净的灰白色的中山装,我的脏手扒在上面,他也不以为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