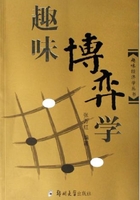可以看出他们的生活有几个要点:第一,他们是很贫穷的,往往“陷于饥寒,危于冻馁”;这是因为他们不务农,不作务,是一种不耕而食的寄生阶级。第二,他们颇受人轻视与嘲笑,因为他们的衣食须靠别人供给;然而他们自己倒还有一种倨傲的遗风,“立命,缓贫,而高浩居”,虽然贫穷,还不肯抛弃他们的寄食——甚至于乞食——的生活。第三,他们也有他们的职业,那是一种宗教的职业:他们熟悉礼乐,人家有丧祭大事,都得请教他们。因为人们必须请他们治丧相礼,所以他们虽然贫穷,却有相当崇高的社会地位。骂他们的可以说他们“因人之野以为尊”;他们自己却可以说是靠他们的知识做“衣食之端”。第四,他们自己是实行“久丧”之制的,而他们最重要的谋生技能是替人家“治丧”。他们正是那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这是儒的本业。
从这种“小人儒”的生活里,我们更可以明白“儒”的古义:儒是殷民族的教士,靠他们的宗教知识为衣食之端。
(《说儒》)
老子
老子因为迷信天道,所以不信人事,因为深信无为,所以不赞成有为。他看见那时种种政治的昏乱,种种社会的罪恶,以为这都是人造的文明的结果。如今要救世救民,须得“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须得“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以复回到那“无名之朴”。他真要把一切文物制度都毁除干净,要使:
小国寡民……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用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八十一章)
这种议论,把“退化”当作“进化”,有许多流弊,后来孔子、韩非,极力挽救,终不能完全打消老子学说不良的影响。这便是老子的缺点了。
(《先秦诸子之进化论》)
孔子
孔子虽不主张复古,却极“好古”。他的好古主义,全从他的进化论生出来,他把历史当作一条由简而繁不断的进行。所以非懂得古事,不能真懂今世的事。譬如看一问算学演题,须从头一步一步看去,才可明白最后的等式。又如下棋,若要知现在这一子错在何处,须回想先下的几子,方可明白。所以唐太宗说:
以古为鉴,可知兴废。
孔子的“好古”主义,正是如此。
(《先秦诸子之进化论》)
道家的弊病
总之,老子、列子、庄子都把“天行”一方面看得太重了,把“人力”一方面却看得太轻了,所以有许多不好的结果。处世便靠天安命,或悲观厌世;遇事便不肯去做,随波逐流,与世浮沉;政治上又主张极端的个人放任主义,要挽救这种种弊病,须注重“人择”、“人事”、“人力”一方面。
(《先秦诸子之进化论》)
道的观念
他们的大贡献在于超出天地万物之外,别假设一个“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道。使中国思想从此可以脱离鬼神主宰的迷信思想。然而他们忘了这“道”的观念不过是一个假设,他们把自己的假设认做了有真实的存在,遂以为已寻得了宇宙万物的最后原理,“万物各异理,而道总稽万物之理”,有了这总稽万物之理的原理,便可以不必寻求那各个的理了。故道的观念在哲学史上有破除迷信的功用,而其结果也可以阻碍科学的发达。人人自谓知“道”,而不用求知物之“理”,这是最大的害处。
况且他们又悬想出这个“道”有某种某种的特别德性,如“清静”、“柔弱”、“无为”、“虚无”等等。这些德性还等不到证实.就被应用到人生观和政治观上去了!这些观念的本身意象还不曾弄清楚,却早已被一种似是而非的逻辑建立为人生哲学和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了。这也是早期的道家思想的最大害处。
(《淮南王书》)
暮气的出世哲学
服食养形,冶炼黄金,按摩导引一类的神仙方术,虽然含有不少的幼稚迷信,然而其中事事都含有自然科学的种子,都可说是医学、生理学、物理学、化学、冶金学的祖宗。我们试翻《淮南万毕术》(茆泮林辑本)的残章断句,都可以想见此种方术之士确是在那里寻求自然界的秘密。搜集民间的经验知识,作物理的试探。此种向外的寻求,尽管幼稚荒谬,往往可以走上科学发明的道路。不但阿刺伯与欧洲的学术史可以证明比象,即论中国古来的一点医术、药物学、冶金术的知识,其中大部分何尝不是这班方术之士的遗赐?不幸这种向外的寻求一变而成为向内的冥想,幼稚的物理试探一变而为暮气的出世哲学,这才是走上万劫不复的死路上去了。试问“恬然无思,澹然无虑”,“不学而知,不为而成”,“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忘其五藏,损其形骸”,“存而若亡,生而若死”,——试问这种理想能带我们走到哪种去?为什么不做活泼泼的人却要歆羡那“存而若亡,生而若死”的槁木死灰境界?为什么不住这现实的人世界却要梦想“休息于无委曲之隅,而游遨于无形埒之野”,“上游于霄霓之野,下出于无垠之门”?
故这种暮气的出世哲学的完成,乃是中国民族的思想大踏步走入中古世界的信号。这时候印度的宗教还不曾开始征服中国.然而中国人已自己投人中古的暮气里去了。中国人已表示不愿做人而要做神仙了,不愿生活而愿意“存而若亡,生而若死”了!
(《淮南王书》)
自然是个最狡猾的妖魔
须知人类所以能生存,所以能创造文明,全靠能用“智故”,改造自然,全靠能“用己而背自然”。“自然”是不容易认识的,只有用最精细的观察和试验,才可以窥见自然的秘密,发现自然的法则。往往有表面上像是“背自然”,而其实是“因任自然”。一块木片浮在水上是自然,造一只五百斤重的舢板是因任自然,造一只两万吨的铁汽船也是因任自然。鸟用两翼飞行是自然,儿童放纸鸢是因任自然,轻气球是因任自然,用重于空气的机器驾驶载重万斤的飞船也是因任自然。自然是个最狡猾的妖魔,最不肯轻易吐露真情。人类必须打的她现出原形来,必须拷的她吐出真情来,才可以用她的秘密来驾御她,才可以用她的法则来“因任”她。无为的懒人尽管说因任自然,其实只是崇拜自然,其实只是束手受自然的征服。
(《淮南王书》)
懒惰消极的人生哲学
道家认定一切有皆生于无,故先造为无中生有的宇宙论,以为无形贵于有形;又造为“有衰(等衰之衰)渐以然”的古史观,以为无知胜于有知,浑沌胜于文明,故今不如古,于是有“返性于初而游心于虚”的人生哲学了。其实是他们先有了这种懒惰消极的人生哲学,然后捏造一种古史观来作根据。这是古代学者文人的普通习惯,风气已成,人人信口开河,全不知道这是可耻的说诳了。
(《淮南王书》)
阴阳感应的宗教
人受天地的精气,人的精神也是一种精气,物类能以阴阳同气相感动,人与天地也能以阴阳同气相感召。在这个“像煞有介事”的通则之上,遂建立起天人感应的宗教。这本是阴阳家的根本理论,却渐渐成为道家与儒教公认的原则,成为中国的中古宗教的基本教条。在这一层薄薄的自然主义的理论幌子之下,古代民间的感应宗教便得着哲学的承认而公然大活动,不久便成为国教了。
(《淮南王书》)
自然主义的熹光
道家是一个杂家,吸收的成分太多,“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遂成了一部垃圾马车;垃圾堆积的太高了,遂把自己的中心思想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埋没了。直到二百年后伟大的王充出来,自然主义才得从那阴阳灾异符瑞感应的垃圾堆里被爬梳出来,刷清整理,成为中古思想界的唯一炬光。
(《淮南王书》)
怀疑的态度
思想线索是最不容易捉摸的。如王充在一千八百多年前,已有了很有力的无鬼之论;而一千八百年来,信有鬼论者何其多也!如荀卿已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而西汉的儒家大师斤斤争说灾异,举世风靡,不以为妄。又如《诗经》的小序,经宋儒的攻击,久已失其信用;而几百年后的清朝经学大师又都信奉毛传及序,不复怀疑。这种史事,以思想线索来看,岂不都是奇事?说的更大一点,中国古代的先秦思想已达到很开明的境界,而西汉一代忽然又陷入幼稚迷信的状态;希腊的思想已达到了很高明的境界,而中古的欧洲忽然又长期陷入黑暗的状态;印度佛教也达到了很高明的境界,而大乘的末流居然沦入很黑暗的迷雾里。我们不可以用后来的幼稚来怀疑古代的高明,也不可以用古代的高明来怀疑后世的堕落。
(《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
同一个时代的作者有巧拙的不同,有雅俗的不同,有拘谨与豪放的不同,还有地方环境(如方言之类)的不同,决不能由我们单凭个人所见材料,悬想某一个时代的文体是应该怎样的。同时记苏格拉底的死,而柏拉图记的何等生动细致,齐诺芬(Xenophon)记的何等朴素简拙!我们不能拿柏拉图来疑齐诺芬,也不能拿齐诺芬来疑柏拉图。
(《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
怀疑的态度是值得提倡的。但在证据不充分时肯展缓判断(Suspension of judgement)的气度是更值得提倡的。
(《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
孝的哲学
孔子的人生哲学,虽是伦理的,虽注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却并不曾用“孝”字去包括一切伦理。到了他的门弟子,以为人伦之中独有父子一伦最为亲切,所以便把这一伦提出来格外注意,格外用功。如《孝经》所说:“父子之道,天性也。……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
又如有子说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
孔门论仁,最重“亲亲之杀”,最重“推恩”,故说孝弟是为仁之本。后来更进一步,便把一切伦理都包括在“孝”字之内。不说你要做人,便该怎么,便不该怎样;却说你要做孝子,便该怎样,便不该怎样。例如:上文所引曾子说的“战陈无勇”,“朋友不信”,他不说你要做人,要尽人道,故战陈不可无勇,故交友不可不信;只说你要做一个孝子,故不可如此如此。这个区别,在人生哲学史上,非常重要。孔子虽注重个人的伦理关系,但他同时又提出一个“仁”字,要人尽人道,做一个“成人”。故“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只是仁,只是尽做人的道理。这是“仁”的人生哲学。
那“孝”的人生哲学便不同了。细看《祭义》和《孝经》的学说,简直可算得不承认个人的存在。我并不是我,不过是我的父母的儿子。故说:“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又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的身并不是我,只是父母的遗体,故居处不庄,事君不忠,战陈无勇,都只是对不住父母,都只是不孝。《孝经》说天子应该如何,诸侯应该如何,卿大夫应该如何,士庶人应该如何。他并不说你做了天子诸侯或是做了卿大夫士庶人,若不如此做,便不能尽你做人之道。他只说你若要做孝子,非得如此做去,不能尽孝道,不能对得住你的父母。总而言之,你无论在什么地位,无论做什么事,你须要记得这并不是“你”做了天子诸侯等等,乃是“你父母的儿子”做了天子诸侯等等。
这是孔门人生哲学的一大变化。孔子的“仁的人生哲学”,要人尽“仁”道,要人做一个“人”。孔子以后的“孝的人生哲学”,要人尽“孝”道,要人做一个“儿子”。这种人生哲学,固然也有道理,但未免太把个人埋没在家庭伦理里面了。如《孝经》说:“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难道不事亲的便不能如此吗?又如:“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为什么不说为人之道不当恶人慢人呢?
(《中国古代哲学史》)
苏格拉底传统
古代中国的知识遗产里确有一个“苏格拉底传统”。
自由问答,自由讨论,独立思想,怀疑,热心而冷静的求知,都是儒家的传统。孔子常说他本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好古敏以求之”。有一次,他说他的为人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过去两千五百年中国知识生活的正统就是这一个人创造磨琢成的。孔子确有许多地方使人想到苏格拉底。像苏格拉底一样,孔子也常自认不是一个“智者”,只是一个爱知识的人。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