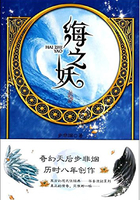后来,我们的小女儿科琳·露丝也出生了,这个家可以说真正的完整了。我们现在有五个人,感觉还不错。跟康纳儿一样,我们也带小女儿去我们位于波卡拉顿的新家附近的一间教堂参加了集体洗礼。这次的洗礼甚至没有神父在场,一位已婚的执事主持的洗礼。我年事已高的父母这下可以放心了,他们的孙子孙女们终于不用在主的等待室里度过永生了。我也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任务,可以歇一歇了。
就像妈妈预言的那样,看来主真的还有很多事情需要爸爸去完成,因为他已经用和温神父驱逐撒旦同样的力量驱逐了前列腺癌。经过几轮的放射治疗,医生宣布爸爸的癌细胞已经完全消失了。他还说:“以后就是死也不会死于这个病了。”爸爸把他的好运气全都归功于祷告的力量,他又变得强壮起来。
主一定也安排了更多的工作给妈妈。科琳出生后第二年,妈妈的心脏病医生就已经断言她的动脉基本已经完全堵塞了,只要激动过度就有中风或者心脏病发生的危险。到了医院,医生们试图用分流器疏通动脉,但最终却害得她被紧急送去做开心手术。做完开心手术又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妈妈总算捡回了一条命,感觉比生病前还要好。她不用再停下来歇气或者服用甘油三硝酸酯控制心频了。这次的四重分流手术治疗只留下了一个负面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医生们早就提醒过我们,由于手术期间依赖外部辅助呼吸的时间过长,妈妈可能会在术后几周变得健忘、精神游离。他们说对了。但是他们没料到的是妈妈的大脑看起来不会再完全恢复了,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犀利了。妈妈做手术的那天标志着她今后漫长的失忆生活的开始,这种状态开始时还不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日渐严重。
她的关节炎也越来越严重,身体变得一天比一天虚弱。爸爸开始承担起更多的家务——用吸尘器做清扫、去商店购物,甚至是开始锻炼厨艺。他还是会料理他的那片草坪、清理车道、修剪篱笆,并抽时间为教堂周边的花圃锄草浇水。
作为一对夫妻,我的父母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费在对信仰的坚持上。教会朋友们几乎每周来访一次,而与死亡擦肩而过的亲身经历使他们对死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一直觉得这不太可能,然而他们一年比一年变得更虔诚。除了晚间新闻以外,他们不看永生信言电视网之外的任何节目。永生信言电视网由一个整天皱着眉头、总是摆出一副教训人的架势的名为安杰丽卡的修女建立。她经常发表一些抨击社会罪恶的守旧的长篇大论,我父母对此却十分笃信。他们觉得自己跟现代社会日益疏远,而安杰丽卡修女正好迎合了他们的感受。她提出关于生活复杂性的“黑白削减理论”,她让他们为坚持着旧有理念感到安慰。约翰·保罗二世教皇来美国的时候,我父母黏在家里的电视机前好多天一直收看永生信言电视网,并把他和车队的每一次露面都录了下来。
我们的生活似乎在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绕道而行,渐渐形成了一种规律。我和爸妈每周或两周都会通电话,在生日和节日的时候也会互送卡片。每年冬天,他们都会飞来南佛罗里达和我们待上一周,而一到夏天,我和珍妮也会用小货车载着孩子们跑三十个小时的路去和他们住上几天。跟之前的那些拜访不同,他们再也不会安排什么日程,甚至都不在我们面前大声地做饭前祷告了。每天早晨他们都会起床悄悄地出门做弥撒,也不叫我们去了,甚至都不告诉我们会去哪儿。我和珍妮都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碰他们对永生信言电视网的虔诚这个话题,也避免谈论家里日益增加的圣女玛丽们。妈妈和珍妮都获得了各自的平静,并在孩子们身上找到了共同的联系,谈话的内容也始终围绕着这个中性的话题。我和爸爸也一样,也找到了一片谈话的安全地带。我们谈论职业问题、房屋修补和对园艺的共同热爱。我还帮着爸爸在花园里干些零活,有时候带孩子们去圣母庇护所的操场玩耍、去潟湖钓蓝鳃鱼或者去港丘的海滩游泳,我和汤米、石头、布袋当初可在这些地方度过了太多的时光。
一个夏日的傍晚,我们正准备在带屏风的走廊坐下来吃晚饭,科琳坐在一把高脚椅子上,男孩子们跪着坐在他们的铸铁制的椅子上,这样下巴就不会碰到玻璃餐桌,我出其不意地问道: “爸爸,你不领着我们祷告吗?”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这样说,但是我知道,我想让我的孩子至少能够体验一下我在他们这个年纪所感受到的安全、有序的世界。同时,我也想让父母知道,在孙子面前,他们可以做他们自己。爸爸抬头看看我,眨了眨眼。把这个老头吓一跳可并非易事,但是我做到了。他顿了一下,然后一边把指尖举到前额准备划十字,一边开始说道:“因父及子及圣灵之名。”男孩子们学着他的样子,努力地祈福:“主啊,求您降福于……”最后,他即兴说道:“感谢您,主,感谢您把约翰、珍妮和三个漂亮的孙儿赐给我们,感谢您保佑他们安全地回来看我们。”孩子们跟着他们的爷爷大声说道:“阿门。”
孩子们都还小,因而很容易假装他们受的是宗教式的教育。但是很快,帕特里克上二年级了,到了该准备做首次忏悔和领圣体的时候。爸妈都暗自着急地等着我下令,但我是不会那么做的。不仅是对帕特里克,对他的弟弟妹妹们也一样。从帕特里克出生以来,我和珍妮就已经建立了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模式。我对手上的三个弱小生命所负有的美好责任让我能够很好地看待和处理和父母的关系。现在珍妮和孩子们在我心里是排在第一位的,我已经欣然接受了自己作为丈夫、父亲和一家之主的角色。我就是我,就像婚姻理疗专家亚当斯医生在几年前跟我说过的,这都取决于我的父母,看他们是不是接受他们的儿子,或者说,接受他所长成的样子。我敢说他们正在努力往这上面靠拢。
我渐渐越来越舒坦地接受了自己作为一名业余天主教徒的角色:并非对天主教思想怀有特别的敌意,却也受够了那些不适合我的说教。因为自打我记事起,爸爸最喜欢抨击的对象就是那种选择遵守或者无视宗教裁定的人,就好像是对待菜单上的菜肴一样对待信仰。爸爸在这世上最痛恨的差不多就是这种人,他们选择他们想去信奉的信仰,就好比站在麦当劳的“得来速”窗口一样。
不提我们关于宗教信仰的分歧,在这一点上我俩倒是十分一致。我的许多同龄人都称自己为职业天主教徒,然而事实上他们只有在有需要的时候才变得 “职业”。他们接受那些感觉良好的方面,同时很自然地漠视那些他们不喜欢的教会等级制度。他们可能会习惯了节育,支持堕胎的权利,对教会谴责同性恋的行为嗤之以鼻,也会质疑为什么女人不能当神职人员,即便这样,他们还是称呼自己为天主教徒。我知道爸妈都对我的选择感到相当失望,但至少他们不能谴责我随便把天主教当做客饭菜单在上面挑挑拣拣。
孩子们上小学的时候,神职人员的性虐待丑闻暴露在公众之下,这可能会撼动天主教教会的根基。它也蒸发掉了我那最后一点日益瓦解的信仰。那些有恋童癖的神父伤害最脆弱、最无助的群体的行为已经够使人生厌的了,然而更为可恨的是他们的上司蓄意装聋作哑、掩盖事实真相的行为。我知道,每一个掠夺成性的神父和每一个试图保护他的无德的大主教身边都有着成百上千的人在怀着基督式的虔诚履行天职,就像我的两个舅舅。然而疯传的丑闻喊出了最高位的伪善。猥亵者和他们的包庇者一面做坏事,一面却在每个周日穿着雪白的法衣作为基督的化身站在人前。他们才是彻彻底底的快餐式基督教徒,不过我是不会对我的父亲说这些的。我能想象,现在的他听到丑闻会多么的震惊和崩溃,尽管他最终又会说他们仅仅是被教会中的自由因素和现代社会中的堕落文化污染的几颗 “坏老鼠屎”。我只能闭口不谈。有一次深夜打给蒂姆,我说:“是时候不做天主教徒了,该歇歇了。”不同于我的是,他已经余怒未消地远离了教会。
而我和珍妮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尽力地把孩子们培养成有道德的人,教给他们善良、爱和宽容。我们绝不需要任何有组织的宗教的帮助。
爸爸妈妈一句话也没说,他们也不敢说。看着一个一个的孩子烙上又脱去天主教的印记——从第一次做忏悔、第一次领圣体,直到坚信礼,他们都闭口不谈。珍妮已经很明确地表示她决不能容忍再多的干涉。她多次的突然发怒和与她的权力斗争已经让爸妈明白珍妮不是说着玩的。他们也逐渐接受了我向着珍妮的事实。他们不再发表意见了,生怕会失去接近儿子和孙子的机会。
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开始给我们邮东西。第一次是一本巨大的、笨重的家用《圣经》,每一页都镶着金边,还附着一张便条,鼓励我们把读圣经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后来又寄了一个一面墙大小的十字架,也附了便条,建议我们始终摆着家里。之后寄了一座圣母玛利亚的雕像,还有一本厚厚的专著,详细地解释了天主教教义。还寄过一些儿童祷告用书和《圣经》故事,以及玫瑰经念珠生日礼物。
最后,爸爸寄来了一本《天主教式的教育》杂志和一封亲笔信,上面说他已经为我们订了一年的杂志。“希望你和珍妮在每篇文章里都能读到有用的知识。”他写道。
我们已经回避这个话题很久了,我知道我欠他们一个解释。因为他们虽然不再逼我了,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担忧。在一封感谢他们订购杂志的信中,我这样写道:
“我知道我们没有按照你们喜欢的方式养育孩子,但是我希望你们能了解,我和珍妮为孩子们精神的成长倾注了非常多的心思和精力。我们很努力,尽最大的努力把他们培养成品德高尚、有操守的人。我们有自己的方式,但是最终的目的,我想,跟你们是一样的。”
几个月前,我成为了《费城调查者》的一名大都市专栏作家,针对一些话题发表未加粉饰的观点。这个工作跟我前些年在劳德代尔堡的报社的工作差不多,但是最大的不同在于:这个专栏是在线的。爸妈可以在文章发布出来的当天就马上读到,爸爸尤其热衷于关注我的文章。我已经不再试图瞒着他发表我的看法,我的专栏里严厉控诉了天主教教会包庇虐童者的行为。但是,我想我还是该向爸妈解释一下这件事。
“你们可能已经从我的专栏里看到了,我已经厌倦了人类的这些制度——政治的、司法的、商业的,还有,对,还有宗教的,”我写道,“但是那并不意味着我厌倦了这些制度所代表的含义——民主、正义、进取心、信念。我们人类是脆弱的、不完美的。一群不完美的人试图告诉另一群不完美的人该如何生活,这不是我的个性。再说,你们知道我向来就不喜欢凑热闹。所以我在雷区中小心地探索着我自己的教子方式,努力地指引一条正确的道路,并在沿途不断调整教育方式。我唯一能保证的就是我将会保持开明的思想。”
我在结尾说道:“我知道在这件事上我给您和妈妈带来了很大的痛苦,为此我很抱歉。不过我也知道您向来推崇一点,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遵守自己的道德准绳。请您,不要太过担心,我知道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您对我来说是一个伟大的父亲,我也正在努力成为我的孩子们的伟大父亲。谢谢您为我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爸爸过了两个月才回信。在回信中他为自己那么久才回信道歉,并解释说是为了要照顾妈妈。妈妈现在已经越来越依赖他,即便是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照顾你母亲已经成了我的全职工作了。”爸爸又解释说,“我不是要抱怨,我还要感谢圣主给了我照顾露丝的机会,还要祈祷他保佑我能一直这么做下去。”
然后他笔锋一转,谈到了我之前的话题。
“听你说和珍妮正在每天努力地给予孩子们精神方面的精心照料,以便让基督教义成为他们成长过程中价值体系的基础,我感到既高兴又欣慰。”他说他明白我们是想在没有宗教组织的帮助下做这件事。“尽管如此,我还是真心地希望你们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他又写道,“带他们领略天主教传统之美。”
“我从未放弃对教会的希望,但是我真的觉得有必要谨慎地走下去,不能一味地崇敬,”我回信说道,“我知道你们一直在为珍妮、孩子们和我祈祷,我真心地感激你们。我们会利用所能得到的一切帮助。”
而且我心里的确就是这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