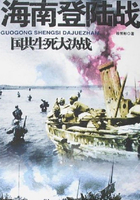我气得跑到图书馆查一本我曾经浏览过的书——关于激进派地下新闻报道的书。我对这个话题着迷好几年了,从反战运动高峰时我去玛丽乔姐姐所在的密歇根大学开始。在卧室里,我通读了各种地下新闻报的实例研究,其中很多都是在六十年代末的反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我觉得它们不可思议的浪漫和锐利,和主流报业比起来,犹如纯咖啡对速溶咖啡,味道浓多了。我尤其沉浸在《第五村》,底特律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在父母的地下室里创办的地下报纸。它成长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运行时间最长的另类报纸,为密歇根白豹党头目约翰·辛克莱尔之类的激进分子提供了平台。如果那个小孩能成功,我为什么不能?
我开始狂想。如果我在西布卢姆菲尔德发行我自己的地下报纸会怎样?如果我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用通过上级就能发行会怎样?我们用文字作为武器挑战全能的学校管理机构会怎样?脑子飞速运转着,我抓来一个笔记本开始捕捉我的思想。接连几天,我几乎没有睡觉。到那个周末我的策划案定下来了,一份指责陈述书、几个备用名单,还有一个备用话题列表。我把计划拿到石头和布袋面前,他们立刻签字上任为我的合作编辑。我们一起又收纳了一小帮迫切想要参与进来的同学。很多别的学生询问
我们想加入。似乎每个人都把它跟《那个人》①联想在一起。
大多数积极参与的是男生,但是其中有三个女生,她们跟我在同一个年级,我在校园里经常看到她们,但不是很熟。还记得去年有一次我被其他学生欺负,她们三个在走廊对我投以同情的微笑。在西布卢姆菲尔德小团体的等级中,洛丽、苏和安娜是属于嬉皮小鸡行列的。她们从不化妆,喜欢穿农民式棉布衫,带仿珍珠装饰。苏长得娇小,满脸雀斑,小卷发像个帽子一样扣在头上,这让我想起“孤女安妮”。洛丽身材高挑,沙色的头发总是用她手上的任何工具捆成辫子:花、串珠、纱线、丝带。安娜是她们三个当中长得最具异域风情的,深咖啡色皮肤、一丛黑色卷毛比我的还要蓬爆。在夏天她皮肤更黑,陌生人有时会误认为她是黑种人。她们三个时常在一起,在一起的时间之多以至于在校园里引起了一个笑话。人们叫她们的名字时好像把三个人作为一体:洛酸娜。我想可能正是因为我在学校里的弃儿角色使得她们对我感兴趣,我觉得她们也挺有趣,再实在点说,可爱,虽然我甚至不敢把这些告诉我最好的好朋友。女孩对我来说就是异域的天使,只能远远地爱慕,而没有勇气接近她们。现在我竟然要跟这三位美女一起工作,想着就开始兴奋起来。
我们的萌芽发行刊物命名为《内心洞察》,灵感来自史提夫·汪达前一年夏天发行的同名专辑(这可能会被人指责是剽窃)。我们在下面加了个副标题:西布卢姆菲尔德学生独立报。新
① 美国小说家欧文·华莱士于1964年出版过一本以黑人总统为主角的畅销小说《那个人》( THE MAN)。故事讲述一个黑人议员雄心勃勃,竞选总统,经过许多似乎难以克服的难关,终于成功。
组成的成员组每天下课就集合起来,写文章,编辑修改,然后设计版面。我们唯一的发行工具就是两台电动打字机,也就是说我们唯一的排版方式就是动手将文章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排成窄栏,一旦打错字了就得重来。真是累人又令人上火的工作,但是我们坚持着,一天接着一天。当我们的文字最终都上了栏目里,就拿剪刀把每个栏目剪下来,各自贴到纸上,再附加上大字标题、照片和简单的素描画。布袋的那一篇《究竟什么叫亵渎?》用他能想到的所有脏话有力捍卫了下流语言。石头对学校不准学生出去吃午饭发表了长篇大论;而我则批判了我的绘画老师给了那些买篮球比赛票的同学高分,那个篮球队由他执教。我还写了首页短文来描述本报的使命:“这份报纸不会因为害怕家长、奉承家长和其他社区长辈而只刊登他们喜欢看到的。”我用大字写得很显眼。
虽然我这么夸口,为这件事辛苦地工作数小时,我始终没有胆量跟父母透露半句。《内心洞察》里充斥着污言秽语、毒品笑话和对权威人物的不敬描述。在一张卡通画里,副校长的脚踝处贴着标语“一级放屁精”,另一个是对连载的《花生漫画》中人物的恶搞,上面画的是“露西”和留着山羊胡子的查理·布朗在史努比的狗窝里吸食香草。以前我种在西红柿中间的大麻,在被爸爸发现和拔掉之前,幸亏我给它拍了照,现在这张照片用在了报纸的第三页。那是一首无礼的——有人以为会遭天谴的——模仿《圣经》的打油诗;标题是“大麻与酒的寓言”。里面是一位名叫弥赛亚的摇滚明星,周围有十二个忠诚的随从,每个人手拿两包大麻和四瓶酒,这是足以让五千名与会者醉倒的精神食粮。我知道妈妈和爸爸在这里面品不出半点幽默。
我把精力全部放在这项我认同的事业上,我为它骄傲,因为它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成就感。然而我不能把这种感觉跟父母共享。他们知道后肯定会失望的。我能看到他们受伤时的表情,能听到他们沮丧的声音。实际上,报纸上很多会触犯他们的内容也让我不舒服。几乎所有的吸毒笑话都来自于一个学生,贾斯廷·乔根森学长,他是第四个签字成为合作编辑的,之后他将一箩筐的创造天分融入少年幽默中。我和他针对创造性思想控制的问题吵得很凶。我支持大力度抨击社会,他支持冲击青年思想的嘲讽打油诗。我想让报纸成为反映平凡学生内心世界的平台,贾斯廷却想将疯狂的报纸融合到学生狂妄的浪漫中。吵到最后,终于把最差的部分删掉了,但是仅仅是最差的那部分。
1974年4月7日早上,我和同党携带900份《内心洞察》来到学校,对这八页一份的报纸进行首次发行。我们在走廊、厕所和院子里散开,悄悄地卖它们,一份10美分。人们好奇心高,我们卖得就很活跃。老师是我们最好的顾客,经常会成倍的买。他们中的一些会顺手给我们5美元、10美元,以帮助我们支付印刷费。整个学校都在议论“新地下报纸”,到了第三个小时,我们已经卖出了750份,足以让我们支付75块钱的印刷费。由于老师的捐助,我们不仅赚了些钱,而且还有150份报纸可以卖。作为地下报纸的编辑的生活就像我想象中的那般浪漫。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四个编辑(我们失策地把我们的名字登在了报头)被叫到了卡温校长的办公室。他邀请我们坐下,然后以友善的口气开始了谈话。他告诉我们当他看到我们的“小简讯”时是多么吃惊,还赞赏了我们的首创经历。“坦白说,”他评论道,“我认为你们四个没这样的头脑。”
他说,作为校长,他经常喜欢鼓励学生去追求他们的热情,即使我们的热情被误导了,并且不成熟。“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他说,然后顺手丢了一份报纸到我们面前。他走到香草卡通的右边,然后弹了弹纸,严肃地用手指敲着我的大麻种植的照片。“潜在的毒品信息。”他语气沉重地说。“还有这个,”他边说边用他的手掌拍弥赛亚寓言,“你们觉得这有意思吗?不仅赞扬滥用毒品,还攻击宗教信仰。”他一页一页地浏览那份报纸,指出许多足以令《内心洞察》不适合在校园传播的违法之处。
“而这个,”他说着指向挂“一级放屁精”标签的副校长卡通画,“这个有损科尔先生的形象。”
“那不可能,”贾斯廷,我们中最爱顶嘴的一个回击道,“科尔先生没有什么形象值得我们损坏。”
“住嘴。”卡温命令他。
最令他恼火的是我们打印出来的被我们爱戴、敬重的人文学老师的完整的一封信。琳达·米勒·爱金逊几乎把我转变成希腊建筑师和罗马雕刻家。她教我欣赏波拉克式抽象和莫内模糊的水彩画。每节课开始,她都关上灯播放史特拉芬斯基的《春之祭》。现在她要带着沮丧和憎恶的心情离开这个地方——临走给了我们一份她的辞职信。这是《内心洞察》的独家报道。内容是:“我被几个心怀敌意的、压迫人的领导排挤了,他们把那些热衷事业、勤勉认真的老师当做顽固豚鼠对待,直到把他们的能量和人性压榨干。我看到西布卢姆菲尔德的教育日益下降到了我必须走的程度,因为它实在让我恶心。”
“你们没有权利印这些东西。”卡温说,他的声音发抖,让我明白我们想用犀利语言打击敌人的目的达到了。“这是工作往来信件。”然后他翻腾出一长列的我们违反了的学校管理规定:未经批准的校园活动,未经授权筹集资金,使用不敬的言语,蓄意进行违法活动,诽谤他人,概括起来就是“不顾学校颜面描绘学生和教员形象”。他勒令我们停止活动,打消念头,并上交所有未发出的报纸。
如果我们想继续发行这份报纸,卡温不会阻止,但是有两个条件:我们必须免费发行,而且每个字都要经过学校行政部门审核通过。
“这么一来,更多的审查程序了。”我说。
“你们知道的,孩子们,言论自由是要承担很大很大的责任的,”他说,“比你们想象的要大。你们的表现已经说明没有能力承担那个责任了。”
他警告我们如果不顺从他就会使用严重的纪律处分。“我的学校里不允许有这种狗屎东西,明白吗?”他说。然后停下来看着我们每个人的眼睛,“我还会给你们家长打电话。”
我们顽强的自由报纸发行了总共有四个小时。交上所有剩余报纸我们飞速跑出来。我们很快发现被拖进校长办公室严厉斥责并不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一群孩子——包括那些从来不屑于关心我们的存在的女生——围住我们,询问细节。我们眉飞色舞、添油加醋地讲述了在出版自由的祭坛上殉难的细节。这是我来到西布卢姆菲尔德后第一次成为公众关注的中心。我动摇了现有的学校管理体制,我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引发了周围人们的讨论和思考。就在那时,我突然决定了以后要做什么,我要当一名新闻工作者。
那晚爸爸回到家,我在门口用我家的握手方式给他打招呼。然后给了他一份《内心洞察》,又给了妈妈一份。卡温还没有打电话来。我心想最好自己告诉他们这件事。再者说,社区周报因为要介绍西布卢姆菲尔德的未经允许的新学生报而采访了我们几个,从我的经验看来,爸爸不可能缺得了那份周报。
“这是什么?”他问。 “就是我这几个月一直在做的那件事,”我说,“我想让您读一读。”
他和妈妈坐到餐桌旁静静地读起来,我则站在隔壁屋里等着,似乎在等着终生宣判。当叫我进去时,他们没有大声吼叫,也没有威胁说把我送回赖斯修士学校,而是问了好多问题。我告诉他们整个事情经过,从校长最初检查删节我们的学生报开始。
“你完全自己一个人搞的这个东西?”爸爸问。 “是的。”我说。 “没有人帮你把这些整理到一起?” “就我们几个人自己弄的。”
他又重新浏览了一遍。“我一点也不同意你这里所说的,”他说,“完全不同意,但是我尊重你所做的。你坚持了你所相信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时我看见了他的表情,一种曾经出现过但不是经常显露的表情。它告诉了我他如果不践踏校长的权威就说不出来的话,然而他的表情如同写出来的文字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父母的骄傲。我的保守、老实本分、循规蹈矩的父亲为了儿子能够打破条款、为觉察到的不公平伸张正义而骄傲。我猜想,他为我骄傲,是因为我终于有魄力做一件需要专心和自律的事,不论什么事。或许最主要的是我在为一项事业奋斗,虽然那不是他期待的那种事业。
“如果你问我,我觉得校长是罪有应得,”妈妈说,“把那位女
老师的事情瞒住不告诉任何人,怎么可以这样?真是厚脸皮!” “能吃晚饭了吗?”我问。 “天啊,当然,”妈妈说,“洗手去。”
如果说那周《内心洞察》在西布卢姆菲尔德引起了大家小声议论,皮特·格雷鲍斯基的大派对就是第二周开课后每个人挂在嘴边的话题了。我从圣母庇护所一年级就认识了皮特,我们那些十三岁男孩中最小的一个,他和我一起做过祭童和童子军。尤其在刚上学时,我们有很多时间在一起混,我经常坐在他爸爸把胶合板放到长铁管腿上做成的长饭桌旁,那是为了适应他家孩子多的特点。格雷鲍斯基先生以修火炉为生,家里生活很简朴。格雷鲍斯基夫人每次把晚餐端上来都如同重复演绎变出面包和鱼的戏法,食物不断地从炉子上的锅里取出来,一次一次直到每个人都吃饱了肚子。
到了高中,皮特成了《大麻硬汉》的创办人,他从不错过任何派对。这次他爸妈要参加一个有关加热与冷却装置的会议,留他一个人在家过周末,他紧锣密鼓活动起来,组织发起这个派对以超越以前所有的派对。我们学校每个人都知道要在周六晚上举行的这个户外大派对。
当我和汤米、布袋、石头到那时,派对已经全面展开了。一排排汽车停放在临近几个街区的各个街道上。院子里全是十几岁的孩子,其中很多我都不认识,他们吸着烟,用塑料杯喝着酒。屋里,人挨人地挤成了闷热的沙丁鱼罐头。大麻和香烟使人几乎窒息。齐柏林飞船在音响里大声吼叫。那时密歇根的法律规定的饮酒年龄是十八岁,皮特却带领了一帮高三学生买了好几桶啤酒,冷冻在洗衣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