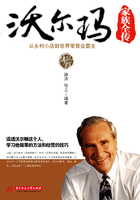然后南宫穆瞟了眼放在床沿上盛满了桔子皮的盘子。
“郡主很喜欢吃桔子?”他第一次开口。
“有吗?”她歪着头想了一下,“还真是!”
他无奈地暗自叹了口气,心想:“就这还需要想!”
然后有个漂亮的丫鬟端着不知名物品进来,两人凑一块盯了盯他的脸,郡主便侧身接过那不知名的物品,对那个不亚于大家小姐打扮的丫鬟说:“木一,让我玩玩。”
于是她拿了个东西,黑黑的,涂在自己的手指肚上,之后轻柔地擦在他脸上。他当下就震惊了,其震惊程度不亚于7岁那年被偷香。幸亏脸被匀匀地涂黑了,否则两个女人一定看出他脸红的。
“这是青雀头黛,郡主说了,你长得太标志了,出门不方便的,而且,容易被仇家发现,以后你就学郡主刚才那样,每天给自己抹上,”漂亮丫鬟对着他说,语气像是他们熟络了几百年一样。
见他抿紧了嘴不说话,郡主笑了,直起身子拉着丫鬟观赏了他一番,然后赞叹:“即便这样仍然是人上人的美色!”临了便回头告诉他:“这青雀头黛被我加入了天然无味花料,不会伤害皮肤的,别担心。”说完翩然离开。
于是艳名满江湖的南宫少主留在召南郡主府做起了贴身护卫。
想到这一幕幕,南宫穆突然兀自微笑起来,忘了身边早已经泪眼婆娑的女子。简采箫瞥了他一眼又一眼,一年未见,他原本白皙的脸黑了些,棱角更加分明,退掉了一层奶油小生的稚气,让人莫名心动又有点不敢造次。她原本也就是嫌他长得太漂亮,如今这模样才是她最最理想的。
“你跟我纠缠怎么就幼稚了?我何时又妨碍你对南宫家负责了?”见他一个人端着茶杯已然游神开去,简采箫终于有些忿恨了,语气没了初时的调侃。
“我几次三番上门求亲,你死活不肯;我这一年不打搅你了,你又跑来招惹我?这不是幼稚是什么?”南宫穆侧过头看了她一眼,她的眉梢一如既往的不羁。
“你!”简采箫顿时语塞,他说的没错,可是,可是,有什么地方不对。气呼呼地拉了拉他的手,见他仍然扭着头一副冷然的样子,简采箫终于明白什么地方不对劲了,便一甩他的手,道:“以前是以前,以前我不懂事行了吧?如今我又喜欢你了,想跟你成亲了。”
南宫穆不可置信地看着她,这句他从七岁就等着盼着的话,如今被她轻易地说了出来,还有点置气的成分,不禁有些恼了:“你如今想跟我成亲,我还不想了!”说吧就要起身走人,刚走两步又回转身,拍了拍她的肩膀:“采箫,这里人生地不熟,你别出去乱晃,我先回郡主那边,明天来找你。”
简采箫一把跳了起了,像是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二话不说揪过南宫穆的头发:“不许走,不许走,你说什么?什么郡主?哪个郡主?”自从遭到定幽将军“无情”的拒绝之后,不可一世的简家小姐谈“郡主”色变,天下的郡主都来跟她抢人了不成?
南宫穆睨着她的手,轻轻捉住她的手腕,稍一用力,简采箫便龇着牙松了力道:“简采箫,男女有别,你也该长大了!郡主于我有救命之恩,你瞎想什么!我明天再来找你,别让我逮到你晚上出门乱晃!”说罢一晃,以极快的身手闪人。
话虽霸道,却是透着毫不隐藏的关心,简采箫一听心里舒坦了,便不追他,只一个纵身跳出房门,对着他的背影大叫:“南宫家的呆子,只懂得练剑的大傻瓜,还想惦记什么郡主!难得你简姐姐不嫌弃,你赶紧给我速去速回!”而此时南宫穆已跑出院门,听闻简采箫的声音,差点一个趔趄,这辈子就没在这女人面前挺起过胸膛。
最让他分神的是那句“还想惦记什么郡主”,要不是天已黑,怕和风与木一担心,他真想跑回去跟简采箫理论一番,连对白都想好了:“我什么时候跟你说我惦记什么郡主了?要惦记她也得喜欢她,我根本就不喜欢她。不对,我也不是根本就不喜欢。不对,我喜欢她不对,那我还喜欢木一呢!不对,喜欢木一跟喜欢她是不一样的”
武林百年难得一遇的剑痴南宫穆当下凌乱了,左手下意识抚了抚剑,这是和风带着木一逛遍了皇城每个角落,然后找了个据说“很犀利”的铸剑师为他特别打造的一柄剑。这剑自不是什么稀世珍宝,毕竟那两个丫头不懂武功,也不懂得选材料。饶是如此,南宫穆用得很顺手,用得很舒服。
等他一回去,就看见郡主与木一坐着她屋里。郡主坐在窗边吹笛子,他从来没见过她像别的小姐那样抚琴,只喜欢吹笛子,笛声有时悠扬,有时又透着淡淡的哀伤,像极了小时候经常去捉鱼的那条小溪里缓缓滑过小腿的流水,冬天时刺骨,夏天时冰凉。木一拿着一方翠绿色的帕子在刺绣,她总喜欢各种建筑,所以尽管天天刺绣,从未绣过任何花草树木,而是千篇一律的一叶雕窗。有时候南宫穆想,这两个女子坐一起,很容易让人误会了她们的关系,小姐不似小姐,丫鬟不像丫鬟,却都是有股浓浓的书卷气,令人舒心。此时两人都没有说话,显然很担心他,只沉浸在各自的思绪中。
笛声戛然而止,然后就听到少女特有的唧唧咋咋,两姑娘顿时满眼欢喜跑向他,南宫穆不禁有些不好意思,便向郡主微微失礼,忙解释了下午的情况。
原以为两人很快就会回房,南宫穆便要洗漱休息,谁知一向不过问私事的郡主却让木一烧水,自己起身亲手煮了一壶茶,然后招呼两人坐下,毫无离开的意思。
“南宫穆,紫书,咱们聊聊,”给两人各倒了一杯茶,和风悠悠开口,其余两人随感奇怪,也没做声,便坐下了。见两人颇有点局促,她兀自抿了口茶,看一眼窗外夜色深沉,然后别过脸盯着冒着热气的茶水,叹了口气:“原本,我们就应该是朋友,可是想想,有一天也许天各一方,但从来不知道彼此到底是谁。”其实她更想说,今日南宫穆的娘子都寻来了,这天各一方很快就要到来。
两人于是明白了郡主的意思,内心又是一阵莫名的伤感,便听到她又幽幽说话:“在进宫之前,我被母亲送往镖局,打算偷偷进入皇城,投靠父亲的故友,半道上镖局被劫了。那时我9岁,只记得母亲叮嘱的,无论如何得去皇城,于是真的走到了皇城。在实在找不到父亲的那个故人之后,我只好每天在皇宫偏门日日守着,那里有进进出出的太监,我想,至少我可以想办法去当个小宫女,混口饭吃。”夜凉如水的初冬时节,她端着的茶水很快凉了,眼睛里却升腾起雾气,仿佛那一个人蜷缩破庙的夜晚又回来了。
“后来我真的进宫了,后来的事你们也知道了,”她重新给自己倒上茶,两只手捂着杯子,片刻便恢复了淡然,“我在傅氏宗谱上是没有名字的,我的父亲从来没有娶过我的母亲,她是竟国人,两人从未成亲。从我出生起,记忆中不过是每日父亲派人去母亲的别院里接过我,送去夫子那边学习或者跟着他呆上一天,然后晚上又被母亲接走。所以,以后不管你们走到哪里,不用担心被我的身份连累凭添麻烦,我能够躲过当年朝廷的诛杀,主要原因也在这里。我的母亲硬要陪我的父亲,自己追到了刑场,所以她没有逃过,她从来也不想逃过。”她轻轻说着从未向外人道出的身世,不容两人有反应的时间,她又温和地看向木一:“紫书,你又是怎么回事进了供香阁的呢?”
她是何等通透,下等宫女都是穷人家丫头,而木一如果是穷人家孩子的话又怎么会读文识字?有些东西,不是后天学得来的,紫书那份温暖应该是打小便被良好家境培养出来的。
这个在皇宫里叫紫书的姑娘看了看郡主,便无奈地笑了:“我一直在等郡主问我呐我其实也不叫紫书,我的父亲是幽州府的书记官,我主动顶替了大姐参加选秀进了宫。”
南宫穆从来不懂宫里那些奇怪的规矩,顿时好奇地望向木一。“嗨,”她自嘲地摇摇头:“我被人掉包了,从秀女的名册里被人踢到了宫女的名册上,连名字也被人盗用了。”在场的其余两人呆了呆,和风突然一阵心疼:“那你以后还叫木一,什么时候想回家了,便回去吧。”木一感激地点头,而后又说:“我想留在丰国陪郡主。”
和风一手扶着她的肩:“但是记住,你只是陪着我,却不是我的丫鬟,你来去自由的。”
轮到南宫穆时,他有些愧疚,原本就不善言辞,以往解决问题的方案无外乎“打架”,此时有些坑坑巴巴,即便是油灯下,也能看见俊颜上浮上红晕。和风见状便扯扯他的袖子:“不着急的,你慢慢说。”
显然两人心里期待的是一个血雨腥风的江湖仇杀故事,木一甚至跑回屋里端来了瓜子和话梅,同时准备好手帕。
南宫穆看着她两正要嗑开的瓜子,无奈地将自己怎么进的郡主府一五一十讲了,他的人生,7岁以后便都是简采萧,说来也就那么简单,经历的最大打击不过是被拒婚以及年少时某一天,有一招剑式无论如何掌握不好。提到恋人的时候,他不时暗自瞟一眼郡主,确定她听故事听得很欢,内心淡淡有一丝失落。
听到他两的人生并没有自己那么苦大仇深,和风深深松了口气,此生牵挂已不多,她能受得了自己曾经悲伤甚至以后也可能惨淡的人生,却受不了南宫穆与木一经历惨痛。
人生短短几十载,能有几个在意的人,而他们又过得好,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