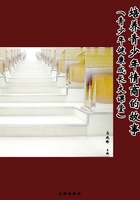(北千漠自言自语:刚下动车我对世间所有的女子有种深深地怜惜,所以我的笔下,女子面容各异,身份各异,性格各异,却无一都是真性情、敢爱敢恨的主。只是,有人敢表现出来,有人懂得隐忍。愿看文的各位,也要活得从容。有人在身旁时,努力爱他;他若不值,努力爱自己。)
尽管那天早上捡了根笛子落荒而逃,丰世子仍然一连十几夜回了中院歇息,具体为了什么,他自己说不清楚,可能从小习惯了中院,他这么认为。
梅雨将至,春种与洪汛的奏章每日纷至沓来,西州的茶山进入正式种茶季节,但是徐氏并未按王室诏书送来长子一脉,来的,是徐氏次子。丰世子接到奏报的瞬间,一声冷笑,心里莫名多了一重高兴。
淅淅沥沥的雨连绵下了三日,邺城防守重点转为防汛,丰世子事必躬亲,一抹鲜亮的蓝色,一顶褐色斗笠,一匹白色骏马,经常穿梭在各大城门之间,他的身后,是鲜衣怒马的贴身护卫。
第三日,雨开始下小了,到了傍晚,变成了点点滴滴的细雨。世子一身衣服全部湿了,贴在身上,风一吹,阵阵寒意。他拗不过汶泰和几个属下的请求,便先行回府,剩下的事情交给了汶泰。
当他一人骑着马回府时,世子府面前开阔的白虎大街上,一个女子撑着淡紫油纸伞,走走停停。她的长裙虽被拎起,厚底的锦缎绣花鞋却已全湿,细细的雨帘中,他看不清那女子的样子,但是凭直觉他认出了自己的世子妃。
一步策马,丰毕岑来到雨中发呆的世子妃面前,人未下马声已至:“傅和风!”
听到自己的名字被人唤起,世子妃猛然抬头,伞下是一张没来得及被吃惊掩盖的和颜悦色,“咦,毕岑,你全身湿透了!”
马上的人却有些怒意,道:“你一个人在外面?”
和风扯扯他的袍子,示意他下马,于是丰世子跳下来,世子妃踮起脚,撑着伞把他也盖住了。
“毕岑,你听啊,”她立住脚,吃力地举着伞,盖住比自己高出一大截的丰世子。
丰世子无奈立住,天地静默,雨点沙沙地,均匀地打在油纸伞上,像是柴门轻磕,又像是小鸟啄食。雨水打在伞上,又滑下,溅在地面,传来微弱的啪啪声。丰世子惊讶地看向身旁的人,他生长在这南隅大地,却从未如此安静地听过雨打油纸伞的声音,却是那般静谧的美好。
和风侧过头看向他,道:“咱们回去吧,得赶紧给你换身衣裳。”
丰毕岑“哦”了一声,走了几步,伸手,于她握伞的上方一寸之处,接过那伞,她便松了手,由着他举伞。
“呐,毕岑,你刚才是在担心我淋雨吗?”
“不是。”
“那你不是在担心我淋雨啰?”
“不是。”
“那你干嘛生气?”
“没有。”
“哦。”
“嗯。”
“要不我以后准备一身衣裳,让汶泰带着,湿了你便换了,别整日这么冻着。”
“好。”
伞下,两人逐渐走近世子府,白马踏着悠闲的步伐,哒哒地跟在主人身后。
莫夫人自小虽不是大家贵族小姐,但也是千般疼万般宠地长大,这厢初为人妇,却一连十几日没见世子过去,初时有些委屈,继而有些自怜自怨,慢慢生出了些幽恨。她这些情绪,既不敢对着世子发泄的,连人都不敢贸然去见;也不敢针对世子妃,只能自己日复一日,坐于房中,盯着院子里的竹子发呆,然后趁宫人不在身边的时候偷偷抹眼泪。她从西州带来的贴身丫头叫千伶,这姑娘不仅懂武,而且生性泼辣大胆,经过多次发现主子偷偷哭泣之后,千伶便自作主张,去了趟中院。
彼时,世子与世子妃刚进院,却见千伶跪于中院门口,木一立于身旁,无奈地为她撑了把伞。这两位姑娘在世子府中,算是规格待遇较高的,她二人一个站着,一个跪着,其他的宫人便只好垂首静静地陪着。
世子见状皱了皱眉,看向世子妃。
和风一看千伶跪在院中,心下便明白了几分,无声叹了口气,便拉拉世子的衣袖,道:“世子快去竹苑换下这衣裳吧,别着了风寒。”
世子没反应过来。诚然,他若能这么懂女人的话,当初不会隔三差五把凤止气哭。在国事问题上,他15岁初监国时,便展露锋芒,以至于三年内便把王城军权慢慢一一拿到手;但是在感情问题上,他向来迟钝。这么多天没去莫夫人那边,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公事繁忙,另一方面当然是由于心系凤止。不管有无夫妻之实,莫夫人在他心里,地位与世子妃其实无异。
见他一脸茫然,和风无奈摇摇头,对着仍然俯首跪着的千伶道:“千伶,你先回院让夫人给世子准备一身干净的衣裳。”
千伶闻言,不顾腿已经麻了,忙不迭地叩头,然后喜兹兹地小跑回去。
“莫夫人想你啦。”世子妃侧过头,稍稍靠近世子,轻轻说。
丰世子稍稍红了红脸,便被世子妃推了一把:“快过去,别磨蹭了,一会真要风寒了。”
他便一个转身,二话不说,大步走向后院。
见他的身影消失在雨中,和风微微一笑,嘱咐木一:“以后这种情况啊,你就直接打发她回去,等世子回来我再让你叫她过来,你别陪着站在雨里。”
木一不满地收着伞,见宫人已退去,劈头便责骂她:“自己的丈夫你倒是舍得,反倒不舍得我啦?”
“疼你多些嘛,来,脸红一个,”和风掩着帕子一笑,木一恨恨一跺脚,便真的脸红了。她无奈地叹了口气,出门时说:“瞧你你伶牙俐齿的,有本事别让世子欺负你!”
和风一愣,看她,而后摆摆手便让她下去了。
成亲以来,处境比和风更尴尬的,则是小王爷丰毕寒。
原本他的故事很简单。闲散王爷一个,一年半前在哥哥府门口遇到倾心的姑娘,打听了姑娘的出身,便央求自己的母后出面,让父王赐婚。当时的他,16岁多一些,说话办事总是随性而为,什么都打听清楚了,就是忘了自己在哪里遇到凤止。一个堂堂左辅小姐,怎么从哥哥府里跑出来了呢?他欣喜得缺根筋,却害苦自己,也害苦他人。当然,当时他的母后打听清楚了世子与凤止的关系;他的父王、他的哥哥以及他的未婚妻,谁都明白情况,只有他一个人,什么也不知道,欢天喜地迎娶娇娘。
成亲的当晚,他雀跃不已地用金秤钩起王妃遮盖在脸上的喜帕,那个瞬间,他呆了,脸色瞬间惨白。美人还是那个美人,只是那蔑视中带着怒气的眼神,生生逼得他退了两步。
凤止生在书香门第,不懂武功,但是,当她与心上人约定时,她便已经知道了如何保护自己。
眼前她深为憎恶的人,一袭大红喜服,头发高高竖起,狭长的眸子,白净的一张脸。掀开喜帕的一瞬间,他的神情由喜悦变成了疑惑,进而是莫名的害怕。
凤止自头上拔下一根凤钗,在自己脸上比划了一下,冷冷道:“小王爷,此话我只说一遍,你听好了。”
丰毕寒微皱着眉,下一刻掌携劲风,将簪子夺到手中。
凤止鄙视地看他一眼,继续说:“我不懂武功,你要是敢碰我,我也没办法反抗。但是,事后我一定划破自己的脸,你日日夜夜也看不住我的。当然,我也不会自杀。”说话间刺啦一声,却是用拢在袖中的金剪子,将自己的手背划破,血顿时汩汩流下。
丰毕寒吓了一跳,一把抓起她的手,想要帮她止血,却被她用尽全身力气推开,忍着剧痛,她从牙缝里挤出五个字:“滚,离我远点!”
惊魂甫定的丰毕寒皱了皱眉,约莫是明白他这王妃心有他人,便不动声色,转身飞奔召来御医。
自此,他从来不踏进王妃卧寝,也从来不问那人是谁。
三个月前,世子妃身边那个叫木一的姑娘在落日余晖中冲着他叫:“下次你若再问我的名字,我绝不理你。”
他心中轻轻一阵涟漪泛起,却为自己突然而来的糟糕生活而烦恼,他答:“本王记忆不好,若忘了,姑娘不理便是。”
他这的回答,木一夜夜于枕边想起,却不知道应该以怎样的心境面对。他们之间,不过三面之缘,若说有点什么,那太过牵强了,她只能幽幽一叹,然后日子照过。想起以前,被人莫名其妙从秀女的名册掉到了宫女的名册,她也只是惨淡一笑,轻轻跟自己说:“这下免得伺候年纪与父亲相仿的人了,挺好。”
和风到底也是琢磨出来了她的心情,多次提议带她去王爷府,算是登门道谢当日小王爷所赠的那些花。每次,木一都摇头,说话毫不客气:“要去郡主自己去。”
和风当然没有去,她怕遇上凤止,她没有勇气去面对那个女子,尽管,她并不认为自己伤害了她,这一段段纠葛当中,凤止无奈,她自己又何尝不是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