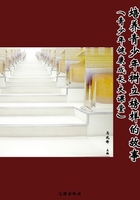“我是德国人,而且你们并不清楚我是谁,也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所以,我不能接受邀请。”
“德国人,弗兰肯人!”老人在表示敬意的同时,毫不掩饰对我的好奇,“我以前听过,据说西方的医生能让死人复活。今天,你用一个小瓶子便让我儿子活了过来,你能把生命从死神那里夺回来。现在,帕夏不在,我得告诉总管德伍特,把宫殿里最好的房间安排给你。假如你能治好德伍特的病,他对你会感激不尽的。”
“他有什么病?”
“胃病。德伍特的胃不好,光是他一个人的饭量,就足够五六个普通人的份儿了。”
“如果是这样,他并不需要我的治疗。只要控制饮食,减少饭量,他就能获得健康。况且,他并不想让我对他进行治疗。因为,刚才把我从宫殿里赶出来的就是德伍特。”
“把你赶出来?这绝不可能!”
“虽然我来这里是经总督的船长艾赫迈德的推荐,但是,刚刚我遭受了德伍特过分的羞辱,也是不争的事实。”
“你是艾赫迈德推荐来的?那就难怪了。一直以来,他对德伍特的态度都很不好,非常粗暴。所以德伍特对他异常的痛恨。假如是其他人推荐你来的,德伍特绝对不会对你如此不恭敬。既然如此,我就不去找他了。但是,我想把你留下来。因为,对于你的所作所为,我非常感激。请恕我冒昧,你能看看我的住处吗?如果你能喜欢,并作为客人住下来,则是我最大的荣幸,也会给我极大的快乐。”
从老人的语调中,我能感到,假如拒绝这个请求,那是对他的一种侮辱。与此同时,那个年轻人也对我说:“留下吧,先生!我现在依然头痛得厉害,假如我的伤势变得严重,还需要你的帮助。”老人的妻子也把自己的双手伸向了我。
“好吧,我住下。”我说,“也许,我的行李会由总管转交给你,希望这不会给你们招惹来麻烦。”
“麻烦?不,不会的!”老人不以为然,安慰我说,“我可不是一无所有,我是帕夏的马槛总管,名叫伊斯梅尔·本·查里利。现在,请随我一起去看看我的房子吧。”
说完,伊斯梅尔对抬担架的两个人说:“你们去找总管,把先生的东西从他那里拿回来!”
两人听到老人的嘱咐后,便离开了。
在穿过了很多扇门后,伊斯梅尔带着我来到了一个大房间。这间屋子刚好把着整个住宅的一个角,而且,它还有另一扇门,从这里可以去往刚才我穿越的院子。看到我喜欢这间屋子,伊斯梅尔很开心。他对我说,自己要去照顾儿子,让我自己随意。
最终,我还是住在了宫殿里,而且是一个胜过宫殿总管百倍的人的住处。
没过多久,伊斯梅尔就回来了。他还带了烟斗,并为我亲自点烟,以示对我的敬意。随后,那两个人把我其余的行李和两支枪也带回来了。其中一个人对我说:“先生,我们取行李的时候,把你在这里住下的消息告诉了德伍特。当听说你拥有可以重获生命的瓶子,医术也很高超后,他对自己刚才的无礼举动表示非常懊悔。他希望你能接受在这里接见他的请求。他病得很重,因为我们的医生诊断他的肚子迟早有一天会爆炸。所以他认为你是安拉派来的,是唯一能给予他帮助的人。”
“好吧,请转告他,他能来见我!”
对于那个黑人对待我的态度,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惩罚他,可是,也找不出什么借口拒绝他的请求。所以,我对自己说,针对于他的“症状”的谈话,也许会非常有趣。
我并没有等太久,德伍特很快就来了,当我看到他那张扭曲的脸时,忽然对他产生了一丝同情。
“请宽恕我,先生!”他哀求道,“如果我那时知道你是——”
“别说了!”我打断了他,“你没做什么需要我宽恕的事情。毕竟总督的船长也有错,他对你的态度的确不怎么礼貌。”
“先生,你对人实在是太仁慈了。我能坐下来吗?”
“当然,我正打算请你坐下来。”
德伍特正对着我和伊斯梅尔坐了下来。直到这时,我才真正注意到他身体的肥胖程度。他的呼吸好似鼓风一般,脸庞则像是一个鼓鼓囊囊装满了东西的口袋。他脸上的皮肤虽然是黑色的,但显现出一种近乎于血色的红润。这让人产生一种预感,他以后必定不是死于消化不良,就是由于血管迸裂而死。
看到我在上下打量他,德伍特叹气道:“肥胖总被人们看做是一种健康的象征,其实不是这样的。先生,我并不像你看到的那么健康。”
“我知道。一个人越来越胖时,就表明他与死亡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对于这一点,我们德国的医生都很清楚。”
“安拉保佑!先生,请你告诉我,我能活多久?”
“你什么时候吃的上一顿饭?”
“今天早上。”
“那么,你打算什么时候吃下一顿饭?”
“中午,半小时后。”
“你早上都吃了什么东西?”
“不多,只吃了半个羊脊背和一只鸡。”
“中午呢?你打算吃什么?”
“也不多,早上剩下的半个羊脊背,一只烤鸡和米饭,盛米饭的盆比我的头巾小一些。还有一条鱼和一盘牛奶小米粥。”
“如果是这样,我想你恐怕连今天晚上都活不到了。”
“噢,天啊!先生,你说的是真的吗?”
“是的,我说这话是非常认真的。你刚才所说的那些食物,我即使只吃其中的四分之一都会爆炸掉。”
“先生,你也许会是那样。但是,我和你不同,我的肚子几乎是你的六倍那么大!”
“哦,不,德伍特!难道你把我们的肚子当成了一个空的大桶吗?你不单单是身体肥胖,我听说你还吃出了毛病,是腹痛病,对吗?”
“对,我已经无法忍受肚子的疼痛了。”
“能告诉我疼痛的位置吗?”
他的手放在了胃的位置上,说:“这里。”
“疼起来是怎样的?像针刺一样的疼痛吗?”
“不是。那种疼痛我描述不出来,只是感觉肚子空空的。”
“原来是这样,我知道了!这种疼痛有规律吗?一般什么时候会疼?”
“有。每次疼痛都是在要吃饭之前出现的。只要一开始疼,我便会立刻吃饭。”
我尽力保持一副严肃的样子,努力不让自己笑出来。
“这种病很严重。”
“它会致命吗?”德伍特恐惧地问道。
“是的,除非尽早进行治疗。”
“先生,快告诉我,我的病你能治好吗?我愿意用黄金作为付给你的报酬!”
“只要弄清楚了你所患病症的名字和治疗的办法,医治起来并不困难。我可以免费为你进行治疗。”
“那这种病的名字是什么?”
“法国人把这种病叫做faim,英国人则叫做hunger[ 法语中的faim和英语中的hunger都是饥饿的意思。
],至于它在这里的名字,我想你完全没有必要知道。”
“你只要把治疗的方法告诉我就好。至于它的名字,即便告诉我,我也不懂是什么意思。”
“它的治疗方法,我倒是知道一种。”
“先生,快告诉我吧!帕夏的宫殿总管就是我,我有很多钱。重申一遍,我愿意付你黄金作为报偿!”
“我也再次声明,我不要报偿。即便你不付钱,我也能治好你的病。对于你的病症,这里医生的诊断是什么?”
“他们认为我的肠胃很虚弱,必须要控制饮食。”
“其实,你的肠胃非常结实,和他们的诊断情况刚好相反,这群傻瓜!你的这种病被我们那里的医生叫做大马猴胃或是河马胃。在治疗的过程中,不仅不能控制饮食,反而要放开了肚子吃东西。”
听了我的话,他很开心,脸上还散发出高兴的神采。他一边用胖乎乎的双手拍打自己的膝盖,一边欢呼:“噢,穆罕默德,噢,哈里发!我不仅可以吃、应该吃,甚至被命令吃东西!我的心和理智都不会抗拒这样一剂良方的。”
“这个方法能医治好你的病症,也是唯一的治疗方法。只不过,你必须按照正确的方式运用它。”
“那么,先生,我该怎么做?”
“当你感觉到肚子里空荡荡的时候,要立刻起身,冲着麦加方向做七个深鞠躬。做完之后,才能开始吃东西,直到那种感觉没有了,再停下来。”
“什么东西是我应该吃的?”
“一切美味的食物。如果你吃完东西后,觉得身心舒畅,这个时候,你要站起来,冲着麦加方向再做九个深鞠躬。这次做的时候,要让自己的头贴着地面。”
“我做得了这种动作吗?”
“一定要做到!”
“假如我做不到呢?”
“一定要这样做,不然,这种治疗就起不到效果了。你做的时候,可以用手辅助一下。只要双手能放在地面上,头自然也可以做到。现在,你可以先试一下。”
德伍特听从我的指示,站起来,尝试着做我刚才说的那种动作。他手脚着地,努力让自己的头碰触地毯的样子,看起来很滑稽。但是很奇怪,我对待这个场景时,竟然是一种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对于德伍特来说,这个动作的确很有难度。但是,他强迫自己做下去,甚至在失去平衡后,还不得不在地毯上打了个滚儿,不过,他立刻站起来继续完成动作。最终,他成功地完成了动作。
“我做到了,做到了!”德伍特开心地叫道,“不过,在家的时候,我只能私下里做。不然的话,我的尊严会因此而受到损害。先生,我还需要做什么?”
“要多做善事。”
“对什么人做善事呢?”
“患有眼病的那些人。在来这里的路上,我看到患有眼疾的大多都是孩子,他们的失明是由于眼部发炎造成的。还有一些苍蝇趴在盲童眼睛上,吃那些流出来的脓汁。”
“的确。”他说,“在路边向行人乞讨的这种孩子足有一百多个。”
“对于这样的人,先知们不是曾教导我们要进行救济吗?既然你那么有钱,假如我治好了你的病,你就找五十个盲童,每人给两个皮埃斯特,每三个月给一次。”
“好的,先生。我相信你的治疗方法,我会照做的。用不了多久,尼罗河沿岸的各国和别的地方都会知道你这位伟大的医生。”
德伍特拉着我的手,和我告别。在整个谈话过程中,马槛总管伊斯梅尔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保持着严肃的神情。此时,伊斯梅尔笑了,胡须也随着他的微笑抖动着。
“先生,除了是一名医术高超的医生,你还是一位好心人,而且幽默风趣。”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帮助了那些盲童。”
“为什么说我幽默风趣呢?”
“嗯,你告诉德伍特的治疗药方,是认真的吗?”
“什么药方?”
“就是你刚才——哦——请恕我无礼!你的学识和开出的药方,岂是我能明白的?朝着圣城麦加深鞠躬,无论是七次还是九次都是应该和必须的。我相信,一个医生既然用小瓶子就能挽救人的生命,他自然明白向麦加深鞠躬朝拜会产生的后果。亲爱的孩子,除了你没人能挽救他的生命。我的内心有一个沉重的压力,你能帮我解除吗?”
“能告诉我是怎样的压力吗?要知道,有很多你们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在外国人眼里都是可行的。”
“不过,压在我心头的这件事,也许你们外国人也无法做到。因为虽然你们也有马匹,却不是驾驭马的高手。这件事,恐怕只有能豁出性命的贝都因人才能解决。”
“这件事和马匹、骑术有关,对吗?”
“对,和一匹马有关,而且是一匹恶魔似的马。让我来告诉你,在麦加的另一面,帕夏有一个兄弟。他在几周前,把一匹纯种的巴卡拉种马送了过来。那是一匹灰白色的马,非常漂亮。巴卡拉种马,先生听说过吗?”
“听说过,是阿拉伯种马,而且性子堪属最烈。”
“那么,先生知道,灰白色的马在所有的马中是最难驾驭的吗?”
“听人们这样说过。不过我觉得,作为一名好的骑师,不管马匹是什么颜色,都应该能驯服它。”
“先生,千万别说这样的话!你是一位好医生,是一个德国人,一位学者。但是,你绝对不是一个好骑师。我作为帕夏的马槛总管,曾驯服过无数的马匹。在尼罗河周边国家的所有部落进行的骑术比赛中,我从来没有输过。可是,就在我不顾生命危险,刚刚骑上这匹灰白色的牡马的时候,却被它摔了下来。帕夏已经下达了命令,等他回来的时候,这匹马必须驯服,而且可以成为他的坐骑。可是现在,只有先把它拴好,才能给它装上马鞍。如果发现谁要骑上去,这匹马便会又踢又咬,根本无法靠近。刚才我儿子那个样子,就是被它摔伤的。我手下的马夫中,有好几个都是被它弄伤的。”
“你儿子是从马上摔下来的?那也就是说,他已经骑上去了。你刚才说,这匹马不是不让人靠近吗?你儿子是怎么骑上去的?”
“先把马用绳子拴好,把它弄倒在地上。接着,上好马鞍。等我儿子骑好后,再松开绳子。谁知道,马夫刚松开绳子跑到一旁,我儿子就被那匹马甩到了墙上。”
“现在,那匹马在哪儿?”
“马圈外的院子里。我们没人敢在这个时候接近它,把它牵回马圈,只能等着它自己回去了。
“能让我看看它吗?”
“当然可以,只是,你要保证不能靠它太近!”
“好的,我保证。”
“那跟我来吧!你马上就能看到它。你们的国家从来没有过这种马,以后也不会有!”
伊斯梅尔的话引发了我浓厚的兴趣。一匹纯正的巴卡拉牡马!驮着我云游各地的爱驹丽赫,就带有一部分这珍贵的血统。善良的伊斯梅尔肯定不知道,我曾驾驭过多少各种各样的骏马。这匹灰白色的牡马,我虽然尚未看到,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相信伊斯梅尔对待它的方式肯定不对。因为,只要用正确的方式对待马匹,即便是性子最烈的阿拉伯种马,也会像孩子那样乖乖听话的。这匹马也绝对不会成为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