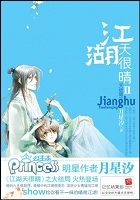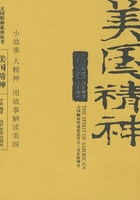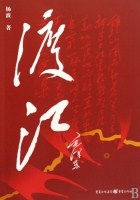轻叹了口气,季宇衡委婉的说:“泽,振作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能安慰的也只有这些了,只能说生命有时真的是很脆弱,所以该珍惜的都要好好珍惜。
任奕泽双手撑着额头,闭着眼没开口,只是轻轻的点了点头,样子看上去很是疲惫。
心太痛了,好像有人在一刀一刀的剜他一样,让他窒闷的喘不过气来。
季宇衡无奈的摇摇头,悄悄退出了总裁办公室,他知道,他需要独处,需要发。泄。
果然,季宇衡才刚走没多久,任奕泽的手就开始颤抖,甚至还有低低的呜咽声传来,光洁的办公桌上,一滴晶莹的泪珠掉了下来。
灯光下,这滴泪珠散发着璀璨的光芒,瞬间又好像失去了所有的光泽,如一滩死水般凝固了。
“祁馨菲,你如果不回来,以后就别想再见到我!我说的是真的,你自己看着办!”无情又痛苦的声音从任奕泽的口腔中逸出,一种凄入肺腑的悲哀,如沸腾的滚水翻涌而来,生生将他灼出泪来。
“如果你明天平安回来了,我马上就娶你,娶你做我的妻子,好吗?”声音瞬间又变得轻柔无比,甚至还有些无力,像是烟花在空中释放出了最后的光华,渐渐地弥散在空气里,直至完全消失。
他真的好后悔,后悔那天不应该回什么纽约,他应该在家里陪着她,好好的安慰她一下,也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该死,真该死!一切的一切,都是他的错,他为什么偏偏在那个时候选择回纽约呢?
猛然睁开眼,瞳中满是悲痛的火焰,犹如一只发怒的雄狮,拳手重重的砸向坚硬的墙壁,墙壁上的古董画似乎也微微颤抖了一下,紧接着还有骨头碎裂的声音。
鲜血如泉水般涌了出来,溅洒在了雪。白的墙壁上,形成了一幅诡异又妖娆的图案。
任奕泽不觉痛,一拳一拳的麻木捶击着,似要将坚硬的墙壁砸出一个窟窿来。
如果失去了她,他不知道以后的日子他该怎么去渡过,生活中的阳光消失了,陪伴他的只有阴沉的乌云和冷冽的寒风,他的生活也将随着她的离去而变得黯淡无光。
“祁馨菲,回来吧,我真的很需要你!”任奕泽近呼耳语的低喃,紧握的拳手很严重的开始颤抖,鲜血依然沽沽的流着,整只手臂已经显得有些苍白了。
心渐渐的沉下去,沉下去,一直沉到心底那汪冰澈如雪水的冰寒之中。
“泽,又有消息了,刚刚又……”
季宇衡急迫的声音响起,办公室的门也随之打开,季宇衡毫无预警的闯了进来,当锐利的黑瞳在瞧见任奕泽那流满鲜血的右手时,季宇衡发狂了。
“任奕泽,你疯了吗?”一声厉喝,几乎将总裁办公室给震塌了。
一听有消息了,任奕泽失魂的眼睛立即有了神采,跌跌撞撞的冲到季宇衡面前,竟低声下气的问:“是不是她有消息了?是不是?她得救了是吗?”飘出的声音含着浓重的鼻音,沙哑而低沉。
季宇衡原本还想大发雷霆,可是一见任奕泽这般模样,肚子里的气也只是化作轻浅的叹息,说:“不是,还没有她的消息,你应该去医院。”幽深的眼睛撇了一眼他满是鲜血的右手,季宇衡无奈的摇了摇头。
光亮的瞳仁瞬间又黯淡了下去,任奕泽无力的垂下手,如行尸走肉般耷拉着脑袋,陷在了沙发里,高大颀长的身躯此时竟显的那么渺小、颓丧,让季宇衡也不jin一阵纠心,轻叹口气,从裤兜里掏出手机,按了一按扭,很快,电话接通了。
“梁,来泽办公室,顺便带药箱来,他受伤了。”低沉的声音中隐含着无奈和心痛,看他的样子他是不会主动去医院了,那就只能请梁逸夫来这里了。
电话那头的梁逸夫沉默一下,才说:“好,我马上来。”
挂断电话后,季宇衡又看了一眼躺在沙发上的任奕泽,眉心纠结,又无力又心痛。
只一晚,他已经憔悴的不成人样了,笔挺的西装起了折皱,头发乱篷篷的,胡子也没剃,哪像从前那个意气风发的任奕泽啊!
女人啊!真是可以创造一个男人,也可以毁灭一个男人!这话说的一点也不假,他已经活生生的从任奕泽的身上看到了。
“泽,你应该休息一下,你要知道,你的责任不止她一个人,你还有公司,公司也需要你不是吗?”季宇衡残酷的说着言不由衷的话,虽然他并不想这么说,可是没有办法,如果不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他怕任奕泽真的会倒下。
任奕泽依然不语,只是眼神茫然的盯着天花板一动不动,手上的鲜血此时已经凝固了,血肉模糊中,还可以看着白白的骨头刺目的露在外面。
薄唇边突然露出一个苦笑,任奕泽僵硬的脸部肌肉终于动了动。
如果祁馨菲回来,他马上就投入工作,让他连续工作三天三夜他都不在乎,他如此对自己说着,可是……可是……接下去的他不敢想像,也不愿去想像,他只希望祁馨菲能够回来。
“你好好休息下吧,一有消息我会立刻通知你的。”季宇衡默默的说了一句,便在办公室里开始了他的工作,他实在不放心任奕泽,怕他等一下又会做出什么让人意想不到的举措来,至少,他得等梁逸夫来。
薄薄的阳光照在光洁的地板上,折射出亮白的光晕,四周寂静得仿佛世间再没有声音,好在梁逸夫很快就来了,宁静的气氛也不用维持多久。
梁逸夫一进门就看到一脸颓废的任奕泽如死尸般躺在沙发上,眉峰微微一皱,对上季宇衡那忧虑的眸光,只一瞬间,一切都已了然。
空难的事,他已经知道了,也知道任奕泽的女人在飞机上出事了,从他上次带那女人来看病,他就知道那女人对他意义非凡,今天一见,果然如此。
轻声的走到任奕泽身边,看了一下他的伤口,还有那布满血丝的双眼,默默的从药箱里拿出消毒水,抬眸,又看了他一眼,说:“会有些痛,忍着点。”
任奕泽一动不动,甚至当湛满消毒水的棉球碰触到他伤口时,眼睛都没眨一下,他的痛不在手上,而是心里,心能用什么药治好吗?可以不那么痛吗?
时间无情的匆匆而过,并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悲伤而停止转动,可怕的空难也在时间的流逝中渐渐的被人们所遣忘,回来的依然活着,回不来的也只能被人默默的悼念着。
一晃,五年过去了。
纽约任家别墅老太太一脸无奈的瞪着面无表情的任奕泽,昔日炯炯有神的双眼此时已是深深的凹陷,苍老的脸上更是没了当年的精干与神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