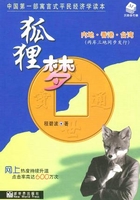她很怕人家说她身上有猪屎味,所以她洗头,洗澡,洗衣服,洗得很勤,家里的肥皂票总是不够用。后来她改用皂角洗头洗澡,把石碱砸开洗衣服。皂角养头发,她的一头短发越洗越黑,有一回罗想农在河边涮鞋,远远看到杨云沿着灌溉渠岸下班回来,夕阳照在她的头发上,亮灿灿的,跳跃着无数金光闪烁的点,衬得她那张脸既生动,又年轻。罗想农脑子里一下子跳出父亲那颗黑白斑驳、花里胡梢的脑袋,心里就感觉怪怪的。
罗家园现在有了一个无法克制的习惯:每天都要步行两公里到新建的种猪场转上一圈。他背着手,佝偻着腰,脑袋伸在前面一冲一冲的,脸吊出有一尺长,嘴唇紧闭,活像满世界的人都欠了他的大钱。他走出家门,先到场部宣传栏前面逗留一下,在印制粗糙的、五颜六色的传单中浏览一番,看看有没有关于批判他“走资本主义路线”的新的大小字报。这些东西,有些是农场造反派们捣鼓出来的,有些是青阳城里的红卫兵们行军下乡“点燃革命火种”的样本。要是找到了他的打上了红叉的名字,他会歪了脑袋读一遍,啧一下嘴,再走开。
然后,他顺着环绕场部的灌溉渠,走二里路左右,过水泥小桥,折往良种试验田。灌溉渠是大跃进那年他亲自带着民工们修起来的,宽广,笔直,渠岸遍栽杨柳和洋槐。实际上,农场地处江边,水资源丰富,仅仅为了灌溉农田,用不着修这么气派的一条人工渠道。可是大跃进年头人人都要大放卫星,作为农业局长,他手里必须要有一个示范工程。因为修这条渠,那年的秋粮无暇收割入仓,食堂里的存粮吃得一干二净,隔年春天,渠岸上的新发出来的嫩洋槐叶都被人捋尽了,吃光了,树皮也剥光,树死得七零八落,现在长在渠岸上的钻天杨,是后来补种上的。
良种试验田在灌溉渠外,乔六月下放到农场之前还是一片芦苇杂生的江滩地,乔六月来了之后自告奋勇开垦出来用于水稻育种。他带了几个人,翻地,斩断芦根,挖排水沟,晒田,苦干了两年,如今的试验田成了农场最肥沃的一块土地,随便抓把土都能够捏得出油。试验田秋播小麦,夏插稻秧,长什么什么得劲。时常有四乡八邻的生产队长转悠到田边,观察乔六月怎么下种,怎么追肥,有时候也开口讨要种子,但是农场禁止良种外流,队长们喜欢紧了,风高月黑夜会派人下手来偷,白天侦察好了地块,夜里拿个麻袋来,剪上百十来穗装回去,来年那个队里也就有了芦席大小的一块种子田。这样,庄稼成熟的季节,良种田要搭窝棚看夜,就好像果园和瓜地的防贼措施一样。
乔六月有点于心不忍,他认为种子培育出来就是为全人类用的,别说附近的公社生产队,就是非洲亚洲的国家有人要,那也应该给。但是他又说,良种培育其实是个漫长的过程,队长们把种子偷回去,不会种,两年一过就要变异,可惜了。
这么说起来,防偷又有了必要,否则乔六月将永远看不到他的最终培育成果。
罗家园到了试验田边,就小心起来,先踮脚四望,确信视线里没有乔六月的影子,才哈了腰,借庄稼和树木的掩护,贴着田边小步快走,往杨云的种猪场。
种猪场和良种田靠得这么近,干活儿干腻了,抬脚就可以串个门。谁能够看得到?谁也看不到,这地方偏着哪,是农场的“西伯利亚”。这个狗日的袁大头!
有两次罗家园在田边撞上了农场现任革委会副主任王六指,老家伙头上扣顶破草帽,带着饵食和鱼钩蹲在稻田边钓黄鳝。罗家园当农业局长的时候,王六指是他的下属,江边良种场的党委书记。文革运动一起来,袁大头造了王六指的反,一度有传言说王六指的第六根指头里藏着美蒋特务的微型发报机,当然后来证明是不可能的事。王六指曾经被斗得断了两根肋骨,一只眼睛差点瞎掉,现在眼仁上长出了一层白白的翳,抬眼看人时眼珠不动,像假的一样。
王六指下了台,当了副手,落得不管事,有会去听听,没会就拎根钓鱼杆四处跑,钓到小鱼后拿给食堂大师傅帮忙拿油一炸,端回家就老酒。据说他家里还时常有女人,他对外界说女人们是来帮他洗被子的,补衣服的,缝鞋子的。究竟是做什么的,看在老单身汉的面子上,大家都睁眼闭眼不追究。
王六指看见罗家园贴着田边走过来,起身招呼他:“晚上过来喝两口?有黄鳝下酒。”他指指游在铅皮桶里的几条小手指头细的鳝鱼。
罗家园绷着脸,摇摇头。他对人很少有笑容,这是从前当局长的习惯。
王六指看看他的脸色,哈哈地笑起来:“心事太重会折寿的!世上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啊?吃点儿喝点儿比什么都好!”
罗家园心里腾起恼火,他觉得王六指看穿了他心里想的东西。这老家伙表面糊涂,肚子里猴精。
罗家园冷冷地说:“你还是管好自己,别弄出民愤。”
王六指就骂他:“跟老哥们都不说心里话,没劲!”
罗家园头也不回地往前走。
种猪场是开春之后才移址重建过来的。工程很简单:地平整好了之后,拉来几船砖头和水泥,农场竹园里砍来毛竹,搭上江边割回来的芦苇,地基、屋梁、墙、顶全都有了。猪不是人,它们对居住场所不讲究,日晒不着雨淋不着已经是幸福。
杨云穿着齐膝高的胶靴,胳膊上套着回纺布的袖套,腰里系一条黑色橡胶围裙,拿一把竹扫帚哗啦哗啦地清扫猪圈。她的脸色红朴朴的,乌黑的头发被汗水浸湿,低头时,就一络络地粘在脑门和脸颊上。因为手脏,她会时不时地扭头在肩膀上蹭一蹭,把遮住眼睛的发丝蹭开,动作很自然,带点孩子气。她把猪粪扫到墙角的一个拱洞口,再从洞口推出去,让粪便进入蓄粪池。猪粪是宝贝,农场的果园菜地抢猪粪抢得要打架。扫过的地面她还嫌不干净,还要拿水冲一遍。相比起来,她对自家的家务事倒没有这么认真。猪圈有几头半大不小的猪,被杨云的竹扫帚驱赶得窜来窜去,猪蹄子在水泥地面上敲出咚咚的声音。猪是白猪,身条儿很长,一望而知是洋种,长足了总要有三四百斤重。
杨云明明是兽医,现在却要兼任饲养员,跟种猪场的农工们干一样的活儿,粪水潲水沾得满手满身,罗家园很心疼。他自责是自己的身份连累了她。转念一想,她明明可以不来,却偏要跟着他来,什么动机呢?跟他罗家园有没有关系呢?心里又涌上愤怒。
罗家园承认,他的心情是矛盾的,他舍不得杨云,又怨恨杨云,偷偷地跑来监视她,盯她的梢,如此的阴暗和卑俗,他的堕落已经连他自己都不耻。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忍不住地要跑过来,隔着老远的距离,遥遥凝望,悲欣交集。
有一天,杨云忽然问了罗想农一句话:“你看了托尔斯泰的《复活》了?”
时间是在晚上,罗想农在头顶十五支光的灯泡下忙着写他高中一年级的作业:一篇批判刘少奇是叛徒和工贼的文章。这样的文章不难写,报纸上连篇累牍都是现成的内容,拣其中的一段摘抄,加个开头和结尾,凑够两张作文纸,差不多能交差。全班同学都是这么干的——一个乡村中学生跟刘少奇哪儿搭得上边呢?
杨云手扶着门框,头微微地歪斜,悠闲而恣意。她的面孔在昏暗的光线中变得柔和,突出了额头、鼻子和脸颊,其余尖锐的部分统统消解,隐入黑暗。她脸上甚至浮动着笑意,笑吟吟的,小女孩子一样娇嫩的神情。
罗想农抬头,钢笔横在右手的虎口上,片刻间竟然呆住。
从来没有见过母亲这样跟他说话,这样的羞涩,甜蜜,温柔。
他拼命调动自己大脑里的细胞,回忆他在乔六月的实验室里读过的所有的小说。是的,他读过《复活》,一本竖排版的纸页发黄的书。可是他读得非常马虎,匆忙地翻过去,因为书里的内容太深奥,有关宗教精神,道德拷问,大段的心理描写,他不能完全明白。书里的那个贵族青年叫什么?聂赫留道夫吧?他在法庭上偶然重见了家中的女奴玛丝洛娃,发现一切罪恶皆因他而起。然后呢?然后呢?
他心中忐忑,生怕杨云要跟他讨论书中的内容,而他结结巴巴说不利索,读了等于没读。可是在他千转百绕打着腹稿准备应答时,再一瞥眼,杨云已经不见了,留着一个空荡荡的门框,还有屋子里若有若无的“蜂花牌”香肥皂的气味。
第二天一放学,罗想农直奔乔六月的种子室,轻车熟路地找到了被藏在一盒纸制标签下面的小说《复活》。他连着读了好几天,读得费力而且辛苦。竖排版的繁体字让他头昏脑胀,书中的阴郁沉闷也令他呼吸不爽。他读着,心里想的是,如果杨云再跟他提到这本书,他如何回答才会让她惊喜。
杨云却仿佛忘记了有过那次半截子提问,她依然是早出晚归,灯光下忙碌着一家人的琐事,补衣,纳鞋,把罗卫星嫌短的裤子接出来一段,在容易脏的被头上加缝一条便于拆洗的毛巾。她进门出门,忙里忙外,每一个转身都带起一股轻微的旋风,在屋里激荡起令人心惊的气流。因为全神贯注于手中的家务,她似乎无暇跟屋里的三个男人说话,她把他们晾在一边,不理不睬,任凭他们澎湃的感情自生自灭。
但是罗想农一点儿都不伤心,因为他明白了他的读书行动被母亲知晓了,并且隐晦地肯定了。她问他:“你读过了托尔斯泰的《复活》吗?”这是一个暗号,说明他们之间的暗道已经打通,他们像向日葵的花盘一样,在某一个时刻,同时朝向了某一个方向,享受同样一种快乐。
想到他读过的每一本书,可能都残留着母亲的指纹,她呼吸的气息,她目光的余温,罗想农的心里就会激动。
蚕豆刚刚开花的时候,杨云把一只刚出生的小猪崽装在她的袖套里带回家。她蹲在家门口,轻手轻脚从袖套里掏出那只小猪时,罗想农看见,小东西耷耳闭眼,半死不活,瘦得还不如一只猫咪大,红不拉叽的皮肤上又是粘液又是猪屎,看着很是恶心。
杨云头也不回地吩咐:“弄盆水来,我给它洗个澡。”
没有指定对象。但是罗想农知道,这样的指令一般都是对他发布的。
他奔回屋里抄家伙,却拿不准应该拿脸盆还是拿脚盆。想想是给一只猪洗澡,脸盆脚盆都不合适,转了一圈,把床底下一个装杂物的小瓦缸腾出来,舀了半缸水,拖到杨云手边上。
杨云不满意:“做事动作这么慢!”探手一试水温,马上皱起眉:“用不用脑子啊?天还凉着呢。”
罗想农冲回屋里拿热水瓶,往小瓦缸里倒进多半瓶开水。
杨云支愣起两条胳膊,示意罗想农帮她把衣袖往上挽,然后一只手托着猪崽,慢慢地浸到温水中,另一只手撩水往它身上浇,用巴掌轻轻擦去那些污秽。小东西不知道是快活还是惊慌,闭着眼睛,细声细气地哼哼着。
瓦缸里的水浑浊起来,泥污和粪便沉下去,一些草屑浮在水面上。
“别抱怨了,”杨云对小猪崽说话,“是你妈不要你,不是我闲得没事带你回家玩。你看看,洗个澡多舒服!来,把嘴巴张开,让我掏掏你的舌头……”
洗完,擦干,放在一个旧棉花垫子上,罗想农才发现这是一只有残疾的猪崽,四条腿不知道怎么只长出三条,因此它没法站起身,勉强抓着它起来,手一松,它身子一歪,又软不溜丢地倒下去。
杨云端详着模样怪异而丑陋的小猪,自言自语道:“可能是遗传有毛病。”
之前她异想天开要培育一种专为国家出口用的“瘦肉型”的猪,就从附近村里弄来一只瘦骨伶仃的本地黑母猪,跟场里饲养了好几年的一只从东欧引进的大洋猪做了交配。不知道是不是洋猪跟当地土猪的基因差距太大,诞下的八只杂种猪,两只是死胎,一只就是眼前的这个“三腿怪”。
三条腿的猪崽没法爬到母猪怀里吃奶,杨云把它弄回来人工喂养。是她胡乱试验造下的孽,她要承担一份欠疚和责任。不管怎么样,眼前这个肉团团好歹是条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