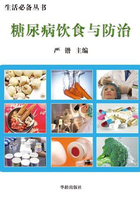我点点头,她又轻盈地出去了。在她进屋时,我仔细端详了一下,像她——不,是她!我激动得心里怦怦跳。我们县中学当年的两千多名学生,文化革命后几乎都回了家。我每次下乡深入生活,都会碰上几个老同学,但在这里碰上鹿荣,还是太意外了!
那场球赛刚结束,同学们就把我们全抬起来了,游了大半个校园。我们几个队员都激动得哭了。不大会儿,我们在学校澡堂,痛痛快快洗起澡来。鹿荣累得快走不动了,一瘸一拐走在后头。进了浴室后,她昏昏沉沉开错了喷头,冷水一下子浇了全身。当时,她还大汗淋漓,被冷水一浇,惊得尖叫一声,就昏倒地上了。
后来,鹿荣腰部瘫痪了。先在县医院治疗,效果不大,又转到二百里外的专区医院。高老师里外张罗,由学校出钱为她看病。我们几个姑娘去看过两次,她仍不能动弹,不仅腰部坏了,而且得了严重的妇科病。我们在她床前哭,她却笑着安慰我们:“别哭啦,小妹妹们!我肯定会好的。”
当时,她主要担心不能参加高考。恰好不久,“文化革命”开始了,高考停止,她也就安心养病了。而我们因为醉心于“文化革命”,此后又是串联,又是打派仗,接着知青下放,再没机会去看她。也就不知她后来的情况。只隐约听说,她后来成了瘫子。前几年,省里下放来的那一百零四个右派全都平反了,鹿荣随母亲又回省城去了。她怎么还在这片密林里,过着隐居样的生活呢?她母亲呢?她的身体什么时候恢复的?她什么时候出的嫁,男人什么时候死的?现在,为什么又对一个陌生的“男人”这样感兴趣……
这一切都像谜一样,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和关切。我想立刻和她相认,互相倾吐一下别后十七年的经历。但我又担心把她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这会儿,她正情意绵绵,陶醉在对异性的向往中。她几乎忙得脚不沾地,又是殷勤留宿,又是精心做饭,又是张罗洗澡水,她正通过一个女人所能做到的一切,表现出她的柔情。她也许以为,自己正一步步把我这个英俊的“小伙子”变成她的俘虏呢。她正在做着一个美好的梦!我一旦暴露了身份,她会不会羞得无地自容呢?啊,会的,肯定会的。我实在不大忍心了!
不知为什么,我竟一点儿没觉得她的痴想有什么邪恶之处。这也许是因为我们少女时代的关系太密切了吧,她曾经给我留下过那么美好的记忆;也许,分别十七年来她的谜一样的遭遇,使我有一种预感,她生活中肯定有过巨大的不幸和缺憾,谁知道呢?反正我同情她,尽管我还没有理解她。
我刚吃完饭,她又进来了,依然是羞怯怯的:“你……去洗澡吧,我烧好水了。”
的确,我该洗个澡了。在林间穿行七天七夜,浑身脏透了。我感激地注视了她一眼,立刻起身去了,心里有点儿慌慌的。现在轮到我心虚了。我真怕她在这时认出我来。可是,又能瞒多久呢?
小木屋东山头,有半间厨屋,也是用圆木扎起来的,周围是篱笆泥墙。厨屋里亮着一盏油灯,由于水雾蒸腾,显得朦胧不清。靠锅台的地上放一只大木盆,里头盛了大半盆清水,我伸手试了试,热乎乎的,正好用。我伸头往外看看,急忙关上门,把衣服都脱下来,放到一堆木柴片上。我几乎是手忙脚乱地跳进木盆的。真舒服呀!盆里放好了一条毛巾,浸泡得软软的,我拿起来尽情地在身上撩水、擦洗,灰尘一层层掉下来,我周身像脱了一副枷,顿时感到轻松了。
我躺在大木盆里,又浸泡了一会儿,舒服是舒服极了,可是不能老洗。我站起身,擦干净水,伸手拿过衣服,太脏了。刚洗过澡,真不想再把脏衣服穿在身上,可我又没带替换衣服,怎么办呢?我犹豫了一下,朝外喊起来:“喂——!”我不想喊她大嫂了,我想喊“鹿荣姐”,又觉得这样太突然,就“喂”了一声,“你有干净衣服让我换换吗?”
“有——啊,我给你拿来了。”她就站在院子里,似乎早在等待我的呼唤了。几声胆怯的脚步响,停住了。我的心也像被她踩住,不动了。“笃笃。”她在轻轻敲门。“进来吧!”
门被慢慢推开,她抱着几件衣服,悄悄进来了,面孔通红,神色慌乱,一副窘迫的样子。我赤裸裸地站在水盆里,女性的一切特点都暴露无遗。她抬起头,从上到下打量了我一眼,猝然惊慌地“哦”了一声,又看了我一眼,胡乱把衣服往我怀里一塞,转身逃走了。
我接过衣服,心怦怦跳,一时愣住了。我确信,刚才即使是一个真正的小伙子这样赤身裸体地站在她面前,她也不会这般惊慌失措!在她回首一瞥的刹那间,我从她的眼神里,不仅看到了惊慌和羞愧,而且看到了一丝儿哀怨和深深的失望!
我心里乱糟糟的,飞快地盘算着下一步该怎么办?事情明摆着,我不能再隐瞒下去了,我必须承认自己的女性身份,而且应该立刻和她相认。我已经残酷地欺骗了她,不能再欺骗下去了。我匆匆穿好衣服,是一身中年男人的肥大裤褂,穿在身上真是不伦不类,可我顾不上挑剔了。
小黑狗卧在一垛柴草上,在黑暗中看见我,亲昵地“叽叽”了几声,又重新躺好了。不知什么时候,月亮已经隐入云层,到处一片漆黑,我仿佛置身在一片原始大森林里。我站在小木屋门口,深深吸了几口清凉的空气,使自己的情绪镇定一些。我大步跨进门槛,不小心碰了一下厚重的门板,发出“咣”一声响。
她正站在里间,背对我翻腾一个木箱,灯光照出她颀长的身体,头发有些儿散乱。听到门响,她没有扭头,依旧翻检着什么。我猜得到,她已经没有勇气看我了,她正处在痛苦和羞愧的深渊里。她的肩膀在微微抖动,她哭了吗?
我惶恐地站在当门,张了几张嘴,终于轻轻喊了一声:“鹿荣——鹿荣姐!是我呀……”
她浑身一颤,缓缓回过身来,紧紧咬住右边的嘴角,直愣愣地盯住我,茫然了。
我冲上去一步,张开双手,急切而冲动地喊道:“鹿荣姐!你——真的认不出我啦?”
她愕然把眼睛睁大了,也往前凑了一步,又是一步,歪起头仔细打量我。我看到,她两眼闪着泪花,胸脯剧烈地起伏着。猛地,她抬手擦擦泪,把身子扑向我:“你……你是‘假小子’?”
“假小子”是我在学校时的外号,就是说,她终于认出我来了!我跨过一步,双手抱住她:“鹿荣姐,是我是我,我是‘假小子’呀!”
她一下扑到我身上,紧紧地搂住我的脖子,刚伏下头,又立刻抬起来,用一只拳头在我肩上乱捶:“‘假小子’、‘假小子’!你这个死丫头,真会坑人!”说完,又立刻害羞地把头伏到我肩上,一下接一下摇晃起来。我简直要被她摇散了!我也紧紧抱住她,心里激动得厉害。过去在学校时,她素来像个大姐姐一样照顾着我,感情密切得像亲姐妹,事隔十七年,在这样一个地方重逢,真是太让人高兴啦!
不知过了多大一会儿,我们终于都平静下来,两人牵着手坐到里间的床沿上。她偏起头,又仔细看了我一阵:“你不是当了作家吗?跑这里干啥来啦?”
我笑了笑,她倒知道我的情况。于是我又简单地说了一些,并向她介绍了这次深入黄河故道来的目的、经历,好叫了一阵子苦。她佩服得要命,抓住我的手夸赞:“你真行!干什么还是那股傻劲。我还真以为……你是个打猎的呢!格格……”她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但已经没有忸怩之态了。我也笑了。笑得非常开心。我们之间很快像当年那样无拘无束了。
“哎——你出来到处跑,孩子由谁照看呢?”她很认真地问我。
我笑起来:“我还没结婚呢!哪来的孩子?”
“怎么?”她一下子把眼瞪得溜圆,“你也……没有对象?”
“嘻嘻,有,怎么没有?我们都谈了十年啦!”
“啊哟——!谈了十年?比抗日战争还长啦!——咋不结婚?你想把他扔了?”
“哪能呢?我挺喜欢他,憨不拉叽的!”
“不用说,他也很……爱你喽?”
“爱!爱得发疯,傻家伙。”
“……”
“我这趟来,他就不同意,又是怕我出事,又是怕我受罪,婆婆妈妈的……那天我临来时,他一直搭车送我到黄河故道,眼看着我钻进密林,还恋恋不舍地站在一片野地里,好像在后悔把一条鱼儿放归了大海。我避在一棵大树后头偷看了好一阵,他还在那儿站着,呆呆傻傻的,真是个情种!我又好气又好笑,弓腰又钻出林子,他以为我后悔了,高兴得手舞足蹈,奔上来迎接我。我举起枪来,冲他头顶上‘砰’放了一枪。他愣了愣,站住了,气得狠狠跺了一脚,转身就走。我在树林子边上,开心地大笑起来,可他一直没再回头,趔趔趄趄地走了。傻家伙,真是气人!”
我只顾滔滔不绝地述说,猛然发现鹿荣又咬起了右嘴角,脸色惨白,一双大眼里注满了亮晶晶的泪水,头也低垂着。我吃了一惊,忙抓住她的肩:“鹿荣姐!你怎么啦?哪儿不舒服吗?”
“不、不……”她惊醒了似的,抬起头向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你真幸福!”眼皮儿一扑闪,滚出两串泪来,又立刻扭转头抹去,掩饰地说:“天有半夜了,睡吧,咱们睡吧。”
她默默地收拾着床铺,放下蚊帐。我呆呆地站在一旁,心里直后悔,肯定是我的话触痛了她的心事,我不该说自己说得那么多。鹿荣姐好像看出了我的意思,故意冲我笑了笑,拿起先前她从柜子里翻出来的几件衣服,打趣说:“这是我的衣服,明天早晨换上,看你穿得像个老头子,被人瞧见了,不笑掉牙才怪。”
我没有笑,我笑不出来了。我急切想知道她这些年是怎么生活过来的,不然,这一夜也不能入睡。
我们睡下了,躺在一头。在我的一再要求下,鹿荣姐叹一口气:“嗨,说就说说吧,反正不怕你笑话。不说呢,心里也闷得慌……从哪儿说起呢?我嘴笨得要命……”
“从头呗!”
“死丫头!你可别把我写进小说!”
“行喽!”
08
“那年我瘫倒住院以后,开始是学校出钱为我看病。后来乱得厉害了,校长、主任和老师都被揪出来批斗,没有人能过问我的事了。有一天,高老师来了。他说是偷跑出来的,学校公款已经被红卫兵控制。他带来五十块钱,是他当月的工资,要给我留下看病。当时,我母亲在这里护理我,她自己是当教师的,当然知道教师的生活多么困难,坚决不要。可高老师还是执意放下了。临走时,他紧紧握住我母亲的手,眼里闪着泪花,好半天才说:‘真对不起,我没能把你的孩子带好……那场球赛,我本该制止鹿荣上场的。她的瘫痪,我有很大责任,真对不起!’可是,这能怪他吗?我母亲一句抱怨的话也没有说,反倒安慰了他几句。高老师又摸着我的头,深情地说:‘鹿荣,安心养病,等治好病,乱过这一阵去,我亲自去省城找我的同学,保送也要保送你进省体育学院。好好看病吧,如果有可能,我还会来看你……’
“高老师走了以后,再没有来过。后来听说,因为他家庭出身地主,又说了一些对‘文化革命’不满的话,被打成牛鬼蛇神,折磨得厉害,他割断静脉自杀了。”
高老师自杀的事我早就知道。鹿荣说到这里,哭起来,我也流下了泪。他为培养我们这些孩子,花费了多少心血呀。
“后来呢?”我小声问,感到鹿荣的手在抖动。她扯出枕巾擦泪,又说起来。
“后来,生活就困难了。我母亲只有四十多块钱工资,平时供我们母女俩生活还很艰苦,现在还要住院看病,就差得更多了。那时,我还在床上瘫着,不能出院。父亲头年死了以后,母亲把我看成命根子。她不能眼看着女儿这样完了,倾家荡产也要为我治病。她不断回去变卖家产,可我们家并没有多少东西,没撑几个月,箱箱柜柜,包括父亲留下的衣服,都卖光了,钱还是不够用。白天,母亲强装笑脸安慰我,晚上就暗自垂泪。看着母亲作难,我哭了,对母亲说:‘我不看病了,咱们回去吧!’母亲不同意。过了几天,她又去操办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