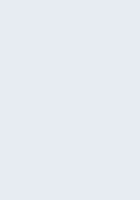快乐幸福的日子总是像流水一般逝去匆匆,短暂的岁月中消耗了母亲所有的生命力。在我八岁那一年,她走了,去了一个我完全陌生的世界,她的离逝带走了我美好的童年。
来自浔阳的噩耗加速了母亲的病体衰弱,使得母亲越来越接近死亡。向夫人自刎了,在得到檀爷爷的噩耗之后,毅然决然地结束自己的生命。父亲派去接她的使者仅仅带回一封沾染上母亲鲜血的信。
她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爱我的女人。深秋时节,落叶纷纷,枯黄的落叶在风中悄悄旋舞,舞出属于母亲的哀乐,盘旋着落地。母亲的离世好像同时带走了尘世万物的生命气息。
她去世的那一天,我永远都记得。母亲静静躺在父亲的怀抱里,她蜡黄的脸色中带有丝丝苍白,如惨灰般的颜色,宣示母亲失去了生命的迹象。她曾丰满柔润的鹅蛋脸庞已经变得干涩瘪瘦,她曾经悄绽樱颗的双唇已经毫无血色并且干裂,她唯一没有变的那双美眸已经永远阖上,再也无法呈现生命的光彩。
母亲纤细柔弱的身躯像一片轻盈的羽毛,似乎随时都会飘走,而这副美妙身躯里的灵魂已然飘走。
任谁看到现在的母亲,都不会想到,曾几何时,她是建康城中的绝代佳人。
母亲再也无法用那双美丽的眼眸温柔地注视我,她再也不会用自己洁白纤秀的柔荑抚摸我的脸颊,在我哭鼻子时,我再也无法寻求到那样温暖的怀抱。我知道,这种认知无时无刻不在凌迟这我的心。
父亲始终是以那样一种不变的姿态怀抱着母亲,似乎他仍在拒绝接受这个现实,似乎只要他一直这样母亲就能回来。我不想在这种时候去提醒他,因为我如此清晰地体会到什么叫“崩溃”。
伴随着母亲的离逝,父亲的灵魂已被这个悲痛的事实抽走了。母亲早已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并且是最被需要的一部分。
母亲走了,父亲变了,哥哥也变了,父亲变得苍老,而哥哥变得成熟。
我还是那个我,只是我没有母亲了。
为母亲举行丧礼的那天,我们一向宁静的家里突然多出了许多的陌生人,他们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刚刚得知自己居然还有许多的亲戚,可好像我们也并不亲近。
原来在母亲罹患疾病后,也就是我出生后,我们的家里就再也没有了客人,也不常与外来往了,因为父亲要让母亲安心养病。这是哥哥告诉我的。
母亲去世后父亲就没再同我说过话,事实上,他已经不说话了。
父亲如同石雕般,没有表情,没有语言,没有动作,再一次地成为我生命中的陌生人。
母亲的丧礼由哥哥一手办,父亲和我没有帮上一点忙,哥哥已经变得越来越能干了。因为父亲与母亲都出生望族,来的人特别多。母亲的灵柩停放在正厅,那些前来吊唁的所谓“亲朋”们都去往母亲的灵堂前上香。
我看见了彭城王也存在于人群之中,如他那般的人物大约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轻易吸引别人的注目。哪怕他如今同父亲一样,显得那样死气沉沉,了无生气。
那双我记忆中神采飞扬的眼眸如今晦暗呆滞,紧紧盯着母亲的灵柩。我不知道他是在为母亲的死亡痛苦,还是在为他自己已然黯淡的将来悲伤。
刘允和刘肱竟然也来了,他们以及他们的父亲彭城王现在于我而言不啻是仇人。如果不是他们,檀爷爷不会遇害,向夫人不会自刎,母亲不会悲郁而终,父亲更不会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如果不是他们,我们一家人现在会团团圆圆地在一起,幸福又美满。檀爷爷还会像以前一样高高地举起我哈哈大笑。我想念他,想念那宽厚的怀抱,想念那爽朗的笑声,想念那个我从未谋面的睿智夫人。
然而,是谁摧毁掉了这一切?
是谁毁掉了这本应属于我们的唾手可得的幸福?是谁让我们饱受这天人永隔的绝对痛苦?
是谁让我在那一个个无法入眠的夜晚绝望哭泣?是谁让年幼的我在一次次的噩梦中惊醒?
究竟,是谁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这一切悲剧的罪魁祸首,这所有不幸的始作俑者,我发誓,永远。
我愤恨地看着这些人,他们就像是刽子手,可以在悲剧发生之时充当冷静的证人,却在杀完人之后却故作哀痛地来为死者追悼。
为什么他们就不能从我的生命中完全消失我真想把这些人赶出属于母亲的圣殿,可同样清楚的声音在告知我,我不能。
刘允的视线一直在追随着在屋外忙碌的哥哥,他的狂妄之气敛去了大半,他曾傲然于世的眼神居然也能变得那样复杂,我完全看不懂。
刘肱仍然是那一副波澜不惊的模样,安静内敛。我看见他就厌恶得不行,尤其他那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更是令我气愤不已。
他凭什么可以在我母亲的葬礼上这样无所无谓,他竟然连一点点的悲痛样子都不能做出来吗?还是他根本就是存心来惹恼我!
我气得胸膛一起一伏,眼泪往下直掉。狠狠地擦了一把泪,我终于忍无可忍,觉得还是眼不见为净,抬起脚我便往灵堂外跑去。经过刘肱的身边,却觉得衣袖霍然一紧。
我恼怒地回过头瞪向他,他苍白的面庞登时微红,嗫嚅着,“你…别哭了,我…我…”他的气息紊乱起来,嘴角翕动了几下,终是没再说出话来,却依旧拉着我的素服衣袖。
我猛地把袖子一甩,恨恨地对他道:“别这么吞吞吐吐的!你有事就直说,谁许你同我拉拉扯扯的,你又算是我的什么人”
他低着头没有回答,我看到他那副模样就来气,回转身子准备离开。有个软软绵绵的东西突然塞进我的手里,我低头一瞧,竟是一方细致白绢,上面绣有几朵墨梅,一缕独特的幽香突地钻入我的鼻端。
这敢情是让我擦泪用的不成?我简直没被气死!我愤愤地转过头望向他,他也正用一种悲哀而同情的眼神望着我。我何时居然要落魄到接受他的怜悯我愤怒至极,把那手绢往地上狠狠一丢,再也懒得去理会他,转身就跑出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