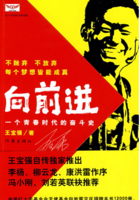“你还真长能耐了,还敢酗酒了是吧!”紫苏在我的卧室里走来走去,帮着开窗换气,整理杂物,把整个被子掀起来清理床铺,差点儿打到天花板上的吊灯上。
我坐在扶手椅里抱着玉儿,帮她编辫子,她的头发细而柔软,我无论怎样摸都摸不够。宿醉带来的痛苦远没有消散,头痛加恶心,程度恶劣到足够让我摔烂手边所有的东西,外加上羞耻感,这个可能需要三天以上才能完全消失。
“玉儿,你小姨满身酒气,你都不嫌臭吗?还不离她远点。”紫苏不以为然地说着。
玉儿吃吃笑着,抱住我的脖子不放手。
“紫苏,侯远的婚礼什么时候?”我突然想起这件事。
“下个月,怎么?”
“你要去参加吗?”
“还没想好。”她简单地回答,不看我,手中继续忙碌着。
“他现在仍然做海员?”我问。
“嗯,不然还能做什么?你以为他为什么那么久还都没有结婚,现在有几个女孩子愿意嫁人之后,一年半载都见不到老公的?”
进入社会后,人们为了独立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这些代价又对个人的生活产生了怎样不可估量的影响,这真的是每个成年人需要面对的话题。
“心屿,过几天一起吃饭吧!叫上LJ。”
“干吗非得叫上他,他看起来好像很忙。”我说。
“你也给我干脆一点好不好?拖了这么长时间你不嫌烦我都嫌烦。要么重新在一起要么分手,就不能快刀斩乱麻?”
我想起LJ姑姑说的话。
“对了,你喝醉谁送你回来的?”
是啊,我茫然地回忆,除了知道夏海送我回来,别的一概记不清楚了。
“夏海送我回来的。”
“谁?”有点嫌恶地问。
“夏海。”我有点心虚,轻声说。
“他还真是无孔不入啊!藤木澈是不是留下什么遗产了?不然他干嘛这么不遗余力的。”紫苏将杯子碟子摔得叮当山响。
“你能温柔点儿对待我的东西吗?哪来那么大火气啊你?”我有点儿啼笑皆非,“紫苏,你是不是心里有点儿反日情结,不会啊!我记得你小时候一直缠着外公给你说日文。”
“我又不是对他是哪国人有意见,他就是火星人跟我也没关系好不好?我就是不满意他干嘛一天到晚跟着你。”紫苏说。
“他小时候就一天到晚黏着我。”我突然觉得很好笑。“糟了,今天星期几?玉儿,告诉小姨今天星期几?”我突然间想起一件重要的事。
“星期五啊!对了,你今天不用上班吗?”紫苏说。
“当然用啊!不然谁给我发工资啊?”
我放下玉儿,从扶手椅里一跃而起,走去洗手间洗漱。
“你们怎么回事?我以为今天是周末咧!全体到我这儿报道是要怎样啊?”我朝她们喊道,嘴里不停地喷着牙膏沫。
“玉儿今天要去打预防针,所以我请假带她。”
“有什么事回来再说!我这个月的不光没有全勤奖,搞不好年底的奖金都危险了。”我奋力甩开拖鞋,穿上大衣,扬长而去。
夏海穿着大红色的篮球服,在学校室外篮球场上带球飞奔,两队正在对抗,气温不足零度,赛场上的每个男孩子都大汗淋漓的,周围有一小群低年级的女孩子在欢呼尖叫。
大学的校园,久违的熟悉感觉。
我站的远远的,视线落在夏海的身上,他露出很认真的神情来,不时对观众和队友笑笑,人群中就爆发出一阵被压抑的哄笑声。我好奇地看看那些年轻的女孩子们,想起自己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便觉得十分荒唐,那些流逝掉的时间,总该有个去处吧!
属于我的时空正在以我不知道的某种规律迅速地消失掉,我只是看着,根本无能为力。
休息时间,他看见球场外面的我,迅速地跑过来,笑着,微微喘着,用手背去抹掉额头上的汗珠。
有那么一刻,我突然产生了奇异的感受,四周的一切突然开始变形融化,我的世界突然变得白茫茫一片,只剩下我,还有夏海。这是什么?幻觉还是回忆?
“心屿。”他叫我的名字。
我迅速回过神来。
“嗯。”我点点头。
他微笑着,用手拨开我眼前的头发,我下意识地稍稍避开。
“头还疼吗?昨晚你一直嚷着头疼。”
我吗?什么时候?昨晚?我的脸上有些发烫。
“没事了,谢谢你送我回家。”我说。
“愿意等我一下吗?结束后可以一起吃饭。”夏海用手肘指了指球场方向,我顺着他的方向瞥了一眼,发现我们正成为别人视线的焦点。
他拍拍我的肩膀,不等我回答就跑回队友身边,我找个地方坐下来,故意不去理睬别人的目光。
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有没有说些不该说的话呢?
“你说什么?那个西方建筑史的讨论课,不是今天?”我急急地问。
“嗯,”夏海竭力忍住不笑出来,“我是说下个周五,不是这个周五。”
“不是这个周五?”我喃喃重复着,在脑中搜索记忆,明明就是这个周五啊!
“那我走了。”我掉头便走,夏海一把拉住我。
“你上哪儿去?”
“不是下周五吗?那下周五我再来。”我有些慌张。
夏海用一只手捂住嘴巴,故意看着别的方向。
“这件事有这么好笑?”我有些懊恼地问。
“不是,只是你的样子,非常可爱。”他这样说。
我保证,记错约会时间,决不是我众多缺点当中的一个,也许是昨天喝了太多酒,以至于产生了幻觉也不一定。
我看着夏海,他双手插在外套的口袋里,脸上挂着无比愉悦的表情,夕阳的余晖从他身后倾泻而下;这个刚刚和队友打赢一场篮球比赛的男孩子,浑身上下散发出运动后特有的气息,就连宿醉未消的我都被感染到。我在那一刻终于对于整件事有了真实感,他再也不是那个只存在于我记忆中的一直在奔跑着的藤木夏海,他站在离我不足一米远的我的面前,鲜活而又生动,我的心中第一次涌出一种对现实生活的感激来。
我喜欢跟他待在一起。这是真的。
我们并肩走在湖边的碎石小路上,说笑着,他突然间伸出一只手臂抱住我的肩膀,用力将我整个人拉离地面,然后再迅速放下来,我被吓得惊叫一声,脚底踉跄了一下。
“干吗?”我说,心脏砰砰地跳。
“没什么,就是很想这样做。”他调皮地笑,再次伸出手臂,把刚刚的动作重新做了一遍。
“别闹了,听到没?我真的会揍你哦!”我喊着。
“我见到你总是很高兴。你见到我不高兴吗?”夏海问。
“不高兴。”我故意说。
他装作严肃的样子,结果还是笑出来,我也跟着笑出来。然后,他很自然的牵起我的手,走完这条长长的路,一直没有放开。
离开的时候,看着后视镜中夏海渐渐消失的身影,鼻子一酸,眼泪就滚落下来。想起考上大学的那一年,母亲和藤木澈送我去外地的学校。分别的那一天,我随着军训的队伍渐行渐远,回头看去,藤木澈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在我视线所及,并不见有泪水掉下来,只是,他的鼻翼翕动了一下。
他让我想起他的父亲。
不,他们在外型上并没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只是,某一刻的神态,确实出奇地像。
人和人之间建立起深厚感情,也不是那么不可思议与困难的事,时间累积,水到渠成。不管这份感情有多复杂,感激和牵挂,甚至仇恨与愤怒。只是,想消解这份情感,却成了世界上最难做到的事情之一。
有的人因为伤得太重,再也不愿意去与任何人建立起任何关系,乍看起来这理由很荒谬,但是我却可以充分理解。
为了保护自己,做再多也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