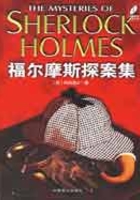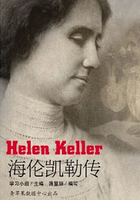秋庄稼在晨风里喧响,曙光从林梢透出。当云霞溢满天空时,太阳滴滴溜溜从灰蒙蒙的田野上慢慢升起来。
我把谱好的曲子拿给鲁新华看。他不懂五线谱,我只能低声哼给他听。
他说,这不是《北京的金山上》吗?
他的话让我泄气。这是我创作的第一首乐曲,经他这么一说,再读一下谱子,真的很像。我的灵机动了一下,不如干脆找几个女同学伴唱《北京的金山上》。
我给你加上笛子咋样?
鲁新华的笛子吹得不错,从前他在宣传队吹笛子。虽然用笛子给提琴伴奏有点不伦不类,可说不定也很好玩。
得给它起个名字吧?
我心里已经给它起好了名字,叫《想望北京》吧。
他看看我的脸,是不是因为张丽娅在北京啊?
你胡扯什么呀?张丽娅跟我有什么关系?
还嘴硬?那时候星期日张丽娅从家里回学校,你经常到北河渡口去接她,你以为我不知道?
我没否认,也没承认。也许张丽娅今生今世和我再没什么关系。她和我的距离越来越远,像两颗飞向不同方向的流星,不知还有没有相聚的机会。
现在鲁新华已经不只是一个往日的同学,他身上带着张丽娅的影子,常常不经意间透露出张丽娅的消息。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我脑子里会突然冒出一些想象,眼前闪现出一座村庄,一条村路,场院里的碾盘和草垛……张丽娅已经展翅高飞,她把这幅图画留在了家乡。只要我把提琴托起来,琴弓举起来,这幅图画就在我眼前浮动。
“你拉琴很投入。尽管你拉得很幼稚,很粗糙,我还是被你感动了。你身子随着琴弓摇动,脸上的表情很动人。我想给你指导,可不忍心让你停下来。看着你那全身心投入的样子,听着你的琴声,我觉得这一生什么磨难都算不了什么,为你做什么都值得。
“直到晌午,你娘把饭摆到桌上,你才想起问:我爸呢?
“你娘说,吃饭吧。下午你不是还得早点回学校吗?
“你看看叶子,看看我。妈,我爸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我把他留下的信拿给你。你默默看完,抬起头说,他没说到哪儿去了?
“孩儿,别替他操心!你爸这个浑货现在会种菜,会养鱼,在外边饿不住。
“他也没来信?
“该来信的时候就来了。你只管好好学习,别管他。
“你父亲像我一样任性,像我一样要面子。我带叶子入学的时候他远远跟在后面,给叶子买文具盒,给她买冰棍,像亲生父亲一样。他说,我这个父亲已经影响了安,不能再影响叶子。为了孩子,我们还是离婚吧。当初是我提出和他结婚,现在我不能随便答应离婚。第二天你爸就留下这封信走了。你娘坚持要继续留在这儿,她说她走了怕叶子吃不好饭。我猜想她是要证明你爸出走跟她没什么关系。”
我把提琴收进盒里,转过身瞪着母亲:想怎么样随你们便,我压根儿不想上什么大学!现在把叶子也扯进来。我看不如全都下乡种地,你们就省心了!
“你口气凶狠,眼神可怕,我真的被你吓住了。要不是你娘拦着,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安!别说这些不争气话!你爸你妈不都是为你好?”
我说的是真心话。大学在我心里已经没什么意义!我宁肯到乡下种地,也不愿为上这样的狗屁大学去费力!我瞧不起它。我鄙视它。
我提上琴往外走。跨过门槛,我回过头说,你们真自私!想把我和叶子推上绝路!
“我追出来,一手拉着你,一手把粮票和钱往你手里塞。你在大街上和我撕扯,把东西扔到地上,我把它捡起来,硬塞在你手里。你一手提琴,一手攥着那卷东西,满脸屈辱、愤怒。
“看着你离去的身影,一种歉意在我心里翻腾。你的话触动了我,让我愧疚不安。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你说得不错,一家人守在乡下种地,也许就不会有这么多烦恼。如果我没出生在那样的家庭,没受过那样的教育,像大多数女人一样听天由命地活着,也许一家人会过得更安稳,孩子也会少受些折磨吧?”
父亲给我写了信,还寄了钱。我无法评价他的行为,是勇敢,还是怯懦?是牺牲,还是逃跑?是爱,还是伤害?在我拉琴的时候,我会想起他,想象他的生活,想象自己如父亲一样,在偏远的山乡,守着一片池塘,披着簔笠,蹲在细雨中,抽着烟,看着鱼苗在水面上倏倏来往。
寒假的时候我和鲁新华没回家。学校组织了宣传队,跟随宣传队演出比回家快乐多了。每场演出我都和鲁新华合奏《想望北京》。四个女同学组成的小合唱为这首乐曲伴唱。当她们唱“多么温暖,多么慈祥……”的时候,我为这歌声感动,感觉到一种深情在我周身流动。我在琴弓上投入了全部的情感,把我的乐曲献给我的张丽娅(她在我心中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符号,一个影子,一份失落的寄托),献给我的父亲(一个遥远世界的想象),献给我的两个母亲(两种不同的母爱),献给我自己(一个自我陶醉的人对自己内心的想念)。如果有一座金色的山,放射着光芒……如果有一轮金色的太阳,照耀着宽广无边的天空……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的心儿照亮!
娘来看我,给我带了锅贴和豆包馍。
在县城演出的时候,我看见母亲的身影。演出结束后,她站在人群后默默看着我,没走过来和我打招呼。
“其实我天天都在想你,挂念你。为了不给你惹麻烦,我不能随便去看你,你演出的时候我也不想在同学们面前露面。你不知道,每个星期天,我都提一包点心走八里路到魏老师家去。他是你爸的姨夫,你们学校的教导主任。从他那儿我详细打听你在学校的情况,把你每次考试的成绩记下来。
“一年时间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转眼麦田黄了梢,大路上出现了城里下乡收麦的队伍。高考又要来了。我的心绷得更紧,你娘往魏姨夫家跑得更多。每次到他家去,她都会动了心思给他捎礼物。你娘拜托他,请他操心你的毕业鉴定,留心你的档案,希望不要像去年那样,在政审这一关出错儿。今年的高考就指望魏姨夫了。”
从二月到六月,我只回了一趟家。虽然我对功课不感兴趣,可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借口——高考复习开始了。其实那些课本我连翻也懒得翻。我冷眼看着班里的同学起早睡晚,梦里还在念念有词地背东西,只觉得可怜可笑。我不知道天底下还有什么比高考复习更让人腻歪、更摧残人了。早已熟悉的东西被强制着一遍一遍复习,嚼得没有味道的剩饭被强迫着反反复复咀嚼,嚼烂到让人恶心,呕吐。
就在高考复习最紧张的时刻,有一天老师突然在课堂上说,今天不复习了,大家学篇社论吧。
他把报纸交给班干部,班干部开始给大家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读报虽然枯燥,比复习轻松多了。更叫人高兴的是,读完这篇文章,我们就不再上课,大家可以在教室里大声喧哗。各年级的课程都停下来。白天讨论,晚自习也讨论,讨论完写决心书,贴在教室后墙上,然后抄在大红纸上,贴到校园里。老师集中到会议室学习。他们脸上现出不同寻常的亮光,人人都显得亢奋、热烈。教室里的奴隶们从钟声里解放出来,校园里弥漫着过年、过节的喜庆气氛。女孩儿们尤其显得轻松快活,她们又笑又唱,叽叽喳喳到处招摇。男孩儿们脸上现出好斗的红云,每天沉浸在演讲和辩论的激情里。大家一团一伙到街上去游行,喊口号。
我喜欢刷标语,刷标语特别过瘾。到伙房去打一桶面糊,把笤帚插进去,搅和一下,看哪面墙招眼,刷上面糊,把整张大纸糊上去。大刷子在墨桶里使劲一蘸,就墙写上:谁……就砸烂他的狗头!不但能随意使用食堂的面粉,不必掏钱掏粮票,还能毫不吝惜地挟着整捆的纸,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每个字撑满天地,写它半个桌面大,气势恢宏,震撼人心,充分满足发疯、挥霍的快感。
迫在眉睫的高考变得遥远了。那些开惯夜车的用功的同学一时感到茫然。就像短跑运动员听到“各就位”的口令站到了起跑线上,正在活动腿脚,准备蹲下,忽然找不到裁判了,不知道这场比赛还要不要进行。
傍晚时分,学校门口小饭店里的女人来找我。她带我穿过她的店房。走进院子,看见娘在院里等我。她把我拉近她身边,好像久别重逢似的,凑近我的脸,疼爱地看着我。
安,学校成立红卫兵了?
成立了。
出去破四旧了?
出去了。
你没参加吧?
我在宣传队排节目,没顾上。
孩儿,你可千万别跟着瞎哄哄!扒牌坊,推石碑,砸人家房上的兽头。
娘,这都是四旧啊!
管他四舅还是五舅,这都是犯忌讳的事!既是停了课,你不如跟我回家吧。
停课又不是放假,我们宣传队忙着呢。
给我好好听着!打人,抄家,砸东西,这些事不准干!祸害人的事,不能干!
黑影里走出一个人。原来母亲一直站在屋檐下。在昏暗的暮色里,她显得很憔悴。瞬间的感觉让我觉得母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你叫了一声妈,走过来拉住我的手。那一刻眼泪在我眼窝里打转。你不在县城,不知道城里的运动搞成了什么样子。我不想告诉你,让你分心。我双手握着你的手,用力揉搓着。安,你娘的话你要记住了。
“你点点头,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妈,你没事吧?
“我凑近你的脸,看着你的眼睛,你爸给你写信没?
“写了。
“他还好吧?
“你不用担心他,妈!
“安,运动来了,我最不放心你,也不放心你爸。你在学校里一定要少参加活动,少惹事儿。”
第二天,红卫兵战斗队揪出一群牛鬼蛇神,把他们押到街上去游街示众。我没去。不是我记住了娘的教诲,是我觉得这群老头子、老婆子、男男女女很晦气,一个个垂头丧气,像落水狗、落汤鸡,灰溜溜的惹人讨厌,看着不舒服,不如躲在宿舍后面拉琴。那是一个偏僻角落,红卫兵出去后,这儿很安静。我有很好的借口不去参加活动,我在为宣传队排节目。
鲁新华从墙角那儿转过来,手里抖着一张报纸。
知道吗?高考停了。
什么意思?
就是说大学停办了,不招生了。他指着报纸上的文章让我看。
读完那段最高指示,我激动地拍一下手掌。万岁——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咱们上不了大学了。肖长安。
让那些狗屁大学下地狱吧!
可是,可是……
鲁新华那丧气的样子让我觉得很好笑。“可是”什么呀?伙计,咱们再不用受高考的苦!再不用受高考的污辱、捉弄了!该死的高考!把它扫进历史的垃圾箱!把它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我知道这对母亲是很大的打击,可我还是禁不住跳脚欢呼。这是那个夏天我听到的最鼓舞人心的消息,是伟大领袖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最激动人心的决定!此后几天我都沉浸在轻松、兴奋的心情里,脑子里不断响着一句歌词:雪山点头笑咧彩云把路开——混蛋高考停咧奴隶站起来——
我和鲁新华坐在栏杆上,两腿在空中荡悠,望着楼下乱哄哄的人群。一队红卫兵押着校长、副校长从操场上走过去。
咱们是不是也组织个战斗队?
好啊!咱们到北京、上海串联去!
把县中转过来的同学拉到一起,回县城造反。
我转头看着他,我知道他想干什么。
找曹龟孙算账!问问他,凭什么不让咱们上大学?
找曹校长一个人能算清这笔账吗?表格是自己填的,鉴定是团支部、班干部、班主任写的。你知道究竟是谁在毕业档案里装进了那些玩艺儿,让咱们进不了大学?
那就把团委书记、班主任一起揪出来!
这家伙的计划很诱人。如果说小学老师没给我留下太恶劣的印象,从初中到高中,老师、校长在我的记忆里没一个好东西,全都是法西斯!我的班主任看起来那么和善,有教养,我一直很崇拜她,很喜欢她,可毕业时我才知道她对我一点也不客气。既不看母亲的面子,也不念我学习那么努力,对她那么尊敬。如果她手下留情,替我减去些重料,把那些致命的东西弄得含糊点,给我写个好鉴定,也许我就不至于落榜。她使我一想起老师就感到恐惧。老师捏住我们的命运,不光每学期给我打操行等级,下评语,还负责我的毕业鉴定和档案,老师们的目光让我提心吊胆,我不知道他们那琢磨不透的眼神背后藏着什么玄机,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会怎样摆布我。为了表示认真、负责,这些老师在我们的操行品德、政治表现、社会关系里仔细扒拉,不挑出点毛病好像就便宜了我们。我怀疑母亲对我的严厉、苛刻与她的教师职业有关。在三年高中时间里,我一直生活在母亲精心编织的网里。所有的老师都是她的眼线。哪次考试有什么失误,哪次课堂没用心听讲,哪次活动和同学闹了矛盾,消息会随时传到母亲耳朵里,立刻反应在她脸上。
组织个战斗队,拉到县城,杀回母校,把那些法西斯老师揪出来修理修理,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看看他们的狼狈相,那是多么痛快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