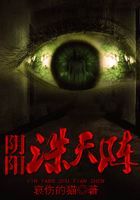“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她叹了一声,换了一种声调,文昌,现在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春如了。我虽然生了长安,可没养育过他,不懂得做母亲的心情。现在怀孕了才知道,一个女人是很容易改变的。为了孩子,我变得自私了,软弱了。白果树,是这个村子的象征,风风雨雨在山坡上长了不知多少年。我们这些不肖子孙,说砍就把它给砍了,填进小高炉里烧掉了。邹凡去阻挡,我拉住他的手,不让他出去。他挣脱我的手,大声喊叫着和砍树的工作队争吵。我躲在教室里,看着他们把他带走,连一句硬朗话也没说。邹凡他不知道他是谁。一个乡村小学教师,犯过错误,差点当了反革命,连自己都保不住,还想去保护那棵树?现在我明白了,我们这些芸芸众生不过是尘沙、蠓虫,不要说改变世界,就是对自己的命运也无能为力。”
一弯月亮偏过头顶。一阵风过,细沙腾起,齿缝间感到龇牙,脸上也感到涩疼。他把她的手拉过去,在手掌里摩挲,“小如……”他十分惋惜地看着她,想对她说,你怎么会变成这样了?
“她向四周看了看,把手抽出去。
“我也向四周看了看,把想说的话咽回去。”
“第二天我参加了出钢仪式。马武镇全乡群众打着红旗,敲着锣鼓,聚集到工地上。在一片鞭炮声里,几十座小高炉同时打开出钢口,橘红色的钢水从炉子里流出来,人群爆发出阵阵欢呼。‘赶上英国用得了十五年吗?我看用不了。’我想起伟大领袖这鼓舞人心的话,感觉到春如离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远,她真的不是师范学校那个小女生了。
“报喜队伍走后,我对乡党委刘书记说,大办钢铁取得了辉煌战果,从明天起,我看是不是把工作转移到春耕生产上来?
“他看着我的脸,好像听不懂我的话。大办钢铁的现场会……”
这位刘书记不知道我父亲内心的变化,他不知道他往往在关键时刻脑子出问题。一个女人影响了他的情绪,使他不再被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神话感动,他亲眼看到了那些神话是用农民家里的锄头、镰刀、门搭吊、甚至牲口脖子上的转环和他们烧饭的铁锅编织出来的。炉子里流出来的红红的东西,过一会儿冷下来,就会变成一坨废渣,报喜之后放进展览馆里去。
“季节不等人,让劳动力都回去,参加春耕生产吧。
“刘书记用疑惑的目光瞧着我。我掉转头,看着山坡下的农田。这不刚下过一场雨,趁墒情,赶快把早秋庄稼种上。你不用担心,我会给县委写报告。”
临走时,他说,“让邹凡也回学校吧。辩论他几场,好好教育教育就行了。”
“在乡政府,我见到了邹凡。他肩上挑着粪桶,头上戴着草帽,脸上没什么表情。
“你就要做父亲了,往后别那么冲动,好好照顾自己的老婆、孩子。
“他嘴角动了动,眼睛看着地面说,我的老婆、孩子我自己会操心。
“我苦笑了一下。
“我在马武镇待了两天,把这里大跃进、大炼钢铁的情况写了一份报告,让乡政府通讯员送回县城,又到各村去转了两天,看看春耕生产的进展。”
从马武镇到县城,是一条晴通雨阻的沙土路。行人车辆很少,大路显得很幽静。路两边的小树在风里摇摆,车轮带起的沙子打在裤脚上,发出嚓嚓的细响。田野从眼前掠过,村庄的影子在远处晃动。电线杆上的电线在风里呜呜嗡响。
“一路上,我的心情很灰暗,心底有一片阴影晃来晃去。因为什么?我自己说不清楚。
“一进县城,看到拦街飘动的大红横幅,‘热烈庆祝我县跑步进入社会主义’,一拨一拨报喜的队伍敲锣打鼓从大街走过,整座县城像过节一样热闹。街道上的老太太和小孩子都在忙着大搬家,打苍蝇,灭蚊子,熏老鼠,捉麻雀……大街小巷像白果树一样,家家户户大门敞开,院里空空落落,院子与院子之间的墙拆掉了,整座县城连成一片,人们想从哪儿走就从哪儿走,想进哪家就进哪家。
“推着自行车走过大街,我觉得自己像一只掉队的孤雁,心里禁不住一阵恐慌。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才下乡七八天,人就落伍了?
“我把自行车推到单位。单位像马武镇乡政府一样空空荡荡,只有通讯员小鲁一个人坐在电话机旁。他的样子让我觉得怪怪的。本来是个机灵、乖巧的小鬼,看见我却不像从前那样亲热,脸上的神气懒洋洋的,眼神里露出一丝冷淡。我把自行车扎靠在走廊柱子上。看我自己动手解行李,他坐在那儿没过来帮忙。
“机关里的人呢?
“都去大炼钢铁放卫星了。
“像白果树的老奶奶一样,他说了两遍我才听清楚。”
在他转身向外走的时候,一个软软的、丝丝缕缕的东西从他心底爬上来。说不清它的形状。说不清它的滋味,却能清楚地感觉到它像云雾一样在胸口弥漫,慢慢地包裹了他的心脏,让他的呼吸没法畅通。
据父亲说那瞬间的奇怪感觉几十年后他还记得清清楚楚。那算不算一种预感?
“虽然并不后悔,可回到县城之后,我觉得在马武镇写的报告有点性急了,与县城的革命形势不太适合,也许应该再等等。”
县城大炼钢铁的工地比白果树更壮观,场面更激动人心。白果树没有电,县城有电,人们不必拉风箱。鼓风机在小高炉边呜呜叫,电灯泡大白天在临时扯起的线杆上亮着。一走近炼钢炉,人就融进了噪音,耳边一片轰鸣,很快失去了意识,忘记了时间,不知道白天和夜晚。
“两天后,我明白了自己的处境,我只能每天忐忑不安地干活,等待倒霉时刻到来。”
“我的辩论会是在大炼钢铁工地上开的。会场就在工地边的土坡上。那儿是一片乱坟岗,树木砍光了,草丛里裸露着树茬子。鼓风机响着,人们手里拿着各自的工具。电灯泡白亮刺眼,把岗下的田野照得一片漆黑。
“尽管开会前没人和我谈话,点到我的名字,让我站出来,我一点也没感到意外。
“辩论会在工地上开,又选在后半夜,我感到很幸运。在马达的轰鸣声里干了三天三夜,精神本来就很疲惫,视觉、听觉都已麻木,垂头丧气的样子不用装也很真实,尖锐难听的话也不再能刺激我。挨批斗的人不会觉得受不了,当然也不会想到自杀。
“马文昌,你为什么反对三面红旗?”
这问题很棘手。他不能说没反对,那等于推翻了开会的合理性,否定了自己的罪行。他写的报告是反对三面红旗的铁证,白纸黑字,不容否认。否认罪行只会激起人们更大的义愤,会场上会爆发出激烈的口号声,人们会围上来推搡你,质问你,为什么不老实?!他也不能承认真的反对了。如果承认,接下来就是“为什么要反对?”这个问题更难回答。幸亏这样的辩论会父亲主持过,会前怎样武装骨干,如何动员积极分子,会场上如何不让批斗对象有反口的余地,这一整套逻辑他还算清楚,虽然做不到临危不乱,起码还知道其中的套路。
他弯下腰,低下头,做出十分沉痛的样子,用尽量诚恳的声调说,“我愿意接受同志们的批评。”
你说说,你为什么反对大炼钢铁?反对总路线,大跃进?
他再一次诚恳地说,“我愿意接受同志们的批评。”
当别人慷慨激昂地发言时,他在心里跟自己辩论: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你是鸡毛,还是我是鸡毛?谁是马克思主义者?你是,还是我是?他脑子里跳出不久前刚刚传达过的伟大领袖的批语,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就……临到什么呢?临到什么就什么?那会儿他的概念出现了混乱,心情也很沮丧,可他一点也没觉得冤枉。往辩论会上一站,在一片斥责声中,人就会觉得自己真的有问题,应该认真检讨。“是的。我的确就是伟大领袖批评的那种人,读什么什么时是什么什么,在伟大的革命运动面前就迷失了什么,丧失了什么,变成了什么。”
这样的辩论会给人的启示是,一个人不可能总站在台上。这会儿你主持会议,喊着口号斗争别人,待会儿可能就会被点名站出来挨斗。当你主持大会时,你口才出众,激情饱满,趾高气扬;当你做了对象,你就会变得灰溜溜的,自卑、笨拙、狼狈、愚蠢,脸皮的颜色也会显出挨斗的倒霉相。那时候,你只能像个死皮赖脸的沙袋提溜在那儿,任别人练习拳脚。
辩论会由专区工作组主持。起初父亲还算沉着,可刘英阿姨的出现打乱了他的阵脚,搅乱了他的方寸。
“我知道自从回到县城知道了春如的消息,她就一直记恨我,可我没想到她会在这时候站出来。”他不知道一个女人生了气会做出什么事来。
刘英阿姨伸出一只手,架平了胳膊,食指直指父亲的脑门,用异常理性的口吻,不高不低的声调,不快不慢的语速,声色俱厉地质问他:
“马文昌,你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现在是不是该把画皮剥开,现一现原形啊?看看你丑恶的历史,再看看你今天的丑恶言行!1945年,你是不是给日本人当过向导?参加革命的时候,你是不是当过逃兵,私自从陕北逃回来,在旗杆寨土地庙里和你的情人约会,差点被民团抓住?在朝鲜战场,你为什么让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美国鬼子?你这个肃反领导小组组长,为什么要包庇反革命分子?帮他平反,亲自给他送平反文件?……你反对大跃进,反对大炼钢铁,反对三面红旗,露出了你的反动本质!”
在此起彼伏的口号声里,父亲惊奇地看着刘英阿姨的脸,她的每一句话都像炮弹一样在他心上开花,打得他无法招架。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灰白,人也一下子矮了下去。
“辩论会后我被小鲁带回机关,交给老邢。他是县委的司务长,现在负责我们辩论对象的劳动改造。
“我看着老邢的脸。如果他让我去扫厕所,我一定会像邹凡那样一丝不苟,把厕所打扫干净,撒上六六粉,让进去的人都感到舒适。如果让我出垃圾、倒恶水,劈柴,拉菜……我也会一丝不苟地把它干好。我们这代人是认真的一代,干什么都会兢兢业业。”
老邢抽了一口烟,很大度地看着他。老马,你去捉麻雀吧。咱们机关这个月除四害任务还没完成,二十五号以前必须完成一百五十只。这任务就交给你吧。
“这有点出乎我的预料。我想过很多劳动改造的方式,却没想过去捉麻雀。然而现在老邢代表组织,我没资格跟组织讨价还价。捉麻雀成为我赎罪的机会。
“我能回家拿点换洗衣服吗?
“老邢用奇怪的目光看着我。回家……难道你不知道……”
父亲确实不知道。在这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日子里,人们的生活“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可以用瞬息万变来形容。他不知道全城已经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全城的房子都进行了统一规划。老年人进了敬老院,青壮年进了民兵营,孩子们进了共产主义幼儿园。干部编连队,男女分开,各住各的营房。
“你家的房子不知道分给哪个部门了,你还回什么家?老邢关心地说,到县直机关民兵营的保管室去看看吧,说不定你的东西在那儿保管着呢。
“我心里起了一阵恐慌。衣服倒无所谓,我的书呢?我的书到了别人手里,他们还会完完整整还给我吗?《联共(布)党史》、《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进一步退两步》……这些书是我多年积攒下的家当,它们比任何东西都宝贵。”
父亲把他那些小书和小册子看得很重。多少年后我看到其中的一本,从字里行间红蓝铅笔圈点的重点、警句,书页上小字批写的心得,都能看出他读这些书时的激动心情。对于父亲,毋宁说这些书就是他的空气、阳光和水。没有了它们,往后叫他怎么活?
“可是,当时我什么也没说。首先我得去捉麻雀。”这一百五十只麻雀是他的希望,是他改造思想、改正错误的机会。有了麻雀,书会有的,工作也会有的。
“尽管老邢说县城已经实现公社化,公社社员已经集体化,我还是想去看看刘英,看看孩子。她到大会上来批斗我,揭发我,让我更痛心地感觉到这些年对不起她。既然不爱她,当初就不应该和她结婚。现在我犯了错误,更不能牵连她母女。”
“刘英被抽调到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了。我去找她,她正坐在门口桌子边,验收各单位上交的除四害战果。
“大门口排着长队,上交战果的人手里掂着鼓鼓囊囊的纸包、草袋。
“刘英手里拿着一把镊子,垂着头,专心致志地点验桌上那堆黑黑的小东西。”
那些小东西伸着毛茸茸的细腿,鼓着圆圆的小脑袋,黑色的小圆头里混杂着一两个像蜻蜓眼睛似的小红头。
“刘英细心地数着,数完一堆,用清脆响亮地声音喊,新民街三选区,苍蝇八百七十二只。桌子另一头的女孩认认真真把它登记在本子上。
“她太忙了,我站在那儿老半天她才抬头看见我。她脸上的表情和我的想象差不多。她只瞥了我一眼,就又低下头去忙她的工作。
“我一直站在那儿,她一直忙。
“我说,我想看看卓娅。
“她在县直公社幼儿园。她头也没抬,手也没停。
“我干咳了两声,咧了一下嘴角。看着她俯在桌上的侧影,心里涌上一股热流,嘴唇嚅动了几下,转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