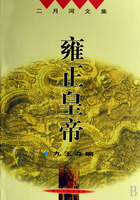风日晴和,一弯小河从天边蜿蜒而来。两个女兵在河边树林中边走边谈。年轻的女战士满脸通红,打着手势,眼睛灼灼发光。当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讲她的家庭和亲人时,她被自己的语言激动,深切地体验到革命的快乐,周身焕发出青春活力,激情在她血管里奔涌。文工团长停下脚步,对这位入伍不久的新战士流露出赞赏的目光。这目光使她兴奋、自信,她的口才显得更出色,思路也更清晰、流畅。也许她并没意识到,她的思想,就是在她的话语中升华出来。她对家庭、亲人的看法,也就在这样的叙说中被加工完成,变成一种信念。
“从于大姐脸上的表情,我看出她对我的谈话很满意。她站下来望着我,凑近我的脸,看着我的眼睛。小曾,你看——大老方——咱们政委,这个人——咋样?
“老方?他人很好啊!又朴实又有水平。
“于珍冲我笑了一下……要是让你跟他谈对象,你有意见吗?
“其实,和于珍一起走下小路时,我已经意识到她想跟我说什么。我憨憨地朝她笑了笑,显出意外的样子。
“大老方?——他还没成家?
“他家里有媳妇,是父母包办,参加革命后就断绝了关系。”
那瞬间她想到了“二壮参军”。方德胜编这个节目时,是不是想过,秀花热情送丈夫参军,二壮参军后会抛弃她?在那个年月,这种事很平常。要把妇女从封建婚姻中解放出来,参加革命的丈夫就必须首先解放自己,和她们离婚。这个革命道理本来正是父亲和母亲所追求的。可不知为什么,听说大老方和自己妻子脱离了关系,她当时就想到了秀花。在那一刻,她才明白自己为什么讨厌这个角色。这个善良的女人为了送丈夫参军,满腔热情,费尽周折。她把丈夫送去革命,自己留在家里,辛勤劳作,侍奉公婆;含辛茹苦,养育孩子;忍受孤苦,盼望革命成功。然而,革命胜利了,她日夜盼望的丈夫只用“父母包办”四个字就轻易地把她甩了,像甩掉行军路上穿破的草鞋。
“这就是女人。这就是革命。”
母亲发出这样的感叹时,她是不是想到了我娘?她在兴隆铺住了一年,在那间密室里生下我,娘和她朝夕相伴,每天给她做吃端喝,为她倒尿罐洗片。她亲眼看到她怎样支撑着父亲的家,尽她的力量保护着马家的一切。然而她会不会因为我娘的勤劳善良而心软,放弃自己的爱情?放弃革命?
“我看着于大姐的眼睛,这是组织的意见?
“她咧嘴笑了一下。
“是老方的意思?
“她又咧嘴笑了一下。
“我有点自责,我不知道自己哪点没做好,怎么会让那么好的一个同志对我产生这样想法?
“我很感激老方,很尊敬老方……可是,我有对象了。
“我想说我结过婚了,不知为什么,话到嘴边说不出口。
“于大姐的眼睛在镜片下闪光,我脸上有点发烧。可我觉得应该趁机会把话说出来。
“小时候家里给我订过亲,是县城一个资本家的儿子。……为了争取婚姻自由,我从家里逃出来。……他是我二哥的同学,家里给他包办了婚姻,为了自由解放,他背叛家庭,投奔解放区,参加了八路军。
“于珍的眼睛在镜片下闪闪发光,脸上露出惊奇和赞赏。
“我没跟她说我和马昌在西安同居,也没跟她说兴隆铺寄养着我的孩子。我知道这样做是对组织不忠诚,可我不是有意隐瞒,只是不好意思。
“于珍站在那儿看着我,她一定能从我脸上看到我是多么爱文昌,说起他的时候,我声音有点喑哑,鼻子发齉,眼角发红。
“她轻轻点了点头。
“于珍走后,我一个人坐在河岸上看着沙滩、河水,看着芦苇在风里摇动,看着对面山头上的云彩。参加革命几个月,这是我头一次想念二哥,想念文昌,想念孩子。离开兴隆铺那天晚上,走出马家堂屋,我连头也没敢回,我怕一回头就再也没勇气走出去。我不敢想文昌,不敢想孩子,想起他们,像做梦往深渊里掉那样,整个心忽忽悠悠往上飘,天旋地转,头脑发晕,胸口发堵,左肋隐隐作疼。我只好把我的魔咒祭出来,心里念着forget!forget!forget!”
“解放七棵树之后,文工团在街上演了一场,沿街贴了一些标语。等我们找驻处时,镇子里已经找不到落脚地方,牛屋马棚都住满战士,一些连队在打谷场上露营。天黑了,成群乌鸦在树上盘旋、鸹叫。我忽然想起,来的时候,山洼里不是有座祠堂吗?同志们一听,就跟我跑下去。
“祠堂在镇南头,三间正殿,挺宽绰。看祠堂的老乡住在边屋里。我和小徐让老乡帮忙找了两捆铺草,把神案、条几搬过一边,就地铺开。
“刚打开背包,大老方来了。进山后他很久没到团里来,也不像从前那样每到一地先看我们演出。
“看见他,我装出很轻松的样子和他打招呼,他点一下头,马上把脸掉过去,站在祠堂台阶下喊,于珍——于珍!于珍跑出来对他立正敬礼。
“谁让你们住这儿?啊?
“于大姐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不知道他为什么火气那么大。
“这儿是祠堂!老乡祭祖的地方!知道吗?
“他一边说,一边跨进屋。
“谁这么自作主张?啊?真是乱弹琴!
“政委,街上找不到地方……
“他转过身凶狠地瞪着我。你学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啊?老乡的祠堂敬着祖宗牌位,怎么能随地铺草睡人?他把手挥了一下,那么多连队在山上露营,你没看到?
“把祠堂里的草搬出去!地面收拾干净,东西摆放好,到外边开生活会!
“这是我入伍后接受的第一场教育。十几个人没吃晚饭在祠堂外树林里开会。
“于珍先自我批评,然后我做检讨。是我带着大家跑过来的。
“我检讨后于大姐第一个发言。她态度那么严厉,样子那么可怕,像换了一个人。那天晚上我借故不演秀花,前几天有一次吃饭我说小米饭里有沙子……这些我连想都没想过的小事经她一提,我才知道错误多么严重。不光是无组织、无纪律、个人主义,更是小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思想作怪。
“接下来同志们发言。平时在一起有说有笑,现在才知道他们对我有那么多意见。在他们眼里,我是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身坏毛病,缺乏自我革命意识,没有认真改造思想。”
每个参加革命的人第一次接受同志们批评,接受革命队伍的教育,心情都会很沉痛。那时母亲还不明白,同志们发言的时候就像她对于珍说自己的家人,只有用激烈的语言才能显示自己的水平。语言这东西,一旦出口,往往不由说话人自己当家。在什么场合,有什么气氛,它就带着你朝什么方向走。气氛愈热烈,发挥愈得意,它会带你走得愈远。就像小时候甩火绳,蝇头大的火星,用力甩开,就会画出炫眼的光环,漂亮极了。何况政委坐在那儿。领导在场,大家都不甘落后,每个人都不肯错过展露口才和觉悟的机会。
政委最后讲话。他从黑影里发出的声音低沉、浑厚,既严厉又温暖。政委的话深深烙印在她心里,成为她人生的座右铭。
“小曾同志啊,从前你是一枝温室的花朵,现在你是革命队伍的一员。看见地里的麦苗吧?革命者就是冬天的麦苗。同志们的批评像石磙,把你的嫩枝嫩叶压碎,麦根才能扎稳。北风吹,大雪埋,经受住考验,开春庄稼才会发旺。”
这比喻深深感动了母亲。听大家批评的时候,她的确觉得自己像一片被践踏、蹂躏的麦田,嫩绿的小苗被踏碎了,枝梗折断,绿叶委弃在泥里,好端端的一个人,被糟蹋成一堆臭狗屎。大老方这么一说,她的心胸豁然开朗,立刻明白了许多道理,觉得自己的觉悟又提高了一大截。
“接着,我又经历了一次行军掉队的考验。山上一阵云,一阵雨,天灰溜溜的。接连几天踏着泥泞行军,背包越走越重,肩上的枪越背越沉。拐过山头,小徐说她想拉肚子,我说我肚里也很难受。我觉得在八里冲吃的饭不对劲儿。当地老乡看了节目,好心好意杀了几只鸡慰问文工团,为了遵守部队纪律,我们给乡亲付了钱,炊事班给大家改善生活。第二天又用剩汤煮荞麦面。吃的时候我觉得不对味,可我没说。
“走了一阵,小徐佝着腰说,咋办哪小曾,我坚持不住了。
“她这一说,我觉得我也坚持不住了。我们俩相跟着绕过一丛野树,沿着沟坡往下走。一直下到沟底,拐一个弯,隐进崖坡下。
“队伍在沟上,我们在沟下。我觉得没走多远,也没用太长时间。枪没离身,只是把背包卸下来。待我站起身,把衣服整理好,背起背包,拿起枪,转过崖坡,沟岸上看不见人了。
“我惊慌地四下看了看,小徐,路上怎么没人?
“小徐弯着腰把灌木丛拨开,探头向上看。不会吧?团部不是还在后头吗?
“爬上坡,我和小徐都傻眼了。山路上空荡荡的,连个人影也看不见。才一会儿工夫,部队就走远了?
“云雾从山谷里往上涌,远处的山和近处的沟崖被云雾遮住,我们俩像站在云彩里。我伸长脖颈四处看,不敢相信真的掉队了。冷汗像蚂蚁一样沿着鬓角往下爬。心里有个声音说,你怎么了曾超!刚开过生活会,刚在会上保证过!你咋这么笨,这么倒霉!
“雨停了。云缝里透出光亮,山崖露出白色的石头和绿油油的树木。走了一阵,看见对面山洼里有一片零零散散的屋顶,我们俩加快脚步往前赶。绕过山谷,走到对面,越走越觉得这地方有点眼熟。上面的山崖,下面的山谷,沟底下的小溪,崖边的枫杨树、酸枣……走到坡下,我在小徐背上拍了一掌,这不是八里冲吗?
“她仰起脖子仔细查看高处的房屋。不错,就是八里冲!昨天在那边坪上演出,今早在这边崖上吃饭。这是怎么回事?走了大半天,又走回来了?
“汗水顺脸往下流,心口像堵了什么东西。我屏着气仰头向上看。村寨静悄悄的,小徐和我都很紧张,鬓边怦怦直响,两人靠在一起,能听见各自的心跳。摸不清敌情,不敢进寨,咱们还是赶快走吧。
“离开八里冲,我心里更迷糊,四处打量,找不到方向。路在山间绕来绕去,山岭、沟洼层层叠叠,不知往哪儿走才对。云彩在山头飘,天灰蒙蒙的。不知道饿,不知道累,人像傻了一样,不顾东西南北,只管寻着路往前赶。肚子咕噜噜难受,嘴唇干得粘在了一起。
“天一黑,山的样子更可怕。满山树木像洪水一样哗啦啦奔跑,山崖像迎面扑来的怪兽。走着走着路断了,前面黑乎乎的,周围都是山崖。往下看,一条灰灰的小路弯过来,好像跨一步就能过去。我往外走了一步,踩在崖边荆棘上。小徐和我相偎着勾头往下看。灌木下面是黑幽幽的悬崖,小路在峡谷对面的山坡上。我倒吸了一口冷气,要是刚才跨出这一步……
“小徐挽着我的胳膊,我揽着她的脖子,我们俩屏住气往回退。退到岩石边,手拉手站在那儿不敢动。风把身上的军衣吹透,寒气越来越重,耳朵、脸颊发烧,手脚有点麻木。抬头看天,天阴沉沉的,夜里要是下起雨来怎么办?
“绝望中,两人像木头桩子似的站在那儿,不知道这一夜该怎么过去。
“小徐突然把她的手抽出去,侧起耳朵听了听,往旁边挪动一下身子。小曾,你听!
“我转过身侧起耳朵,从哪儿传来咕咕哝哝的说话声。
“循着声音往下看,一点火光在山腰移动,说话声、脚步声从很深的地方传过来。
“小徐往前站了站,两手圈在嘴边,冲着火光喊:喂——有人吗——同志——老乡——
“我也跟着喊,喂——喂——
“回音在山谷里回荡。过了一会儿,听见下面有人喊,喂——徐玉娟——曾超——
“我俩拼命喊:我们在这儿——在这儿哪——
“小徐哭起来,我的眼泪也簌簌往下掉,两人的声音都嘶哑了。
“找到团部,天已经麻麻亮。通向寨子的小路上走过来一个人,他一路走一路用南腔北调的声音唱小曲儿。
……
走到半路哩,
碰见个当兵的,
他把我拉进了黍黍棵里,我的大娘哎——
“他脚步飘忽,歪歪倒倒,身上的褂子在风里摆动。突然看见几个身穿军装的人,他吓了一跳,猛地收住脚步,身子向前栽了一下,嘴里小曲也停了。一张瘦削的脸,只看见一双大眼。这个鸦片鬼,不知在哪儿过足了烟瘾,趁着黎明游游荡荡回家。他的浪曲和那受惊的样子让我的心情放松下来,好像突然从噩梦里惊醒,重又回到人间。”
东方透出亮光,村寨的影子从朦胧的晨雾里显现出来。碎石小路弯上山坡,两个战士带她们走入一处农家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