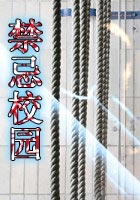他怒了,梅飞飞知道。
但是他凭什么发怒?他以为他是谁?他现在只不过是她的同学,普通同学!连男朋友也不算!而她,却不是前世那个死地塌地要跟着他的梅飞飞,不是那个一天到晚窝在家里想着他什么时候下班要做什么晚饭的小女人,更不是那个被他主宰了十年青春岁月最后被他无情背叛的傻瓜!
一想到这些,她脑子里热血直往上冲,全然已经忘记眼前这个男子,其实与她前世的事件毫无关系。骨子里反抗的一面抬头了,不顾肩膀被他握得生疼,她倔强地抬头瞪回去,大声地道:“是!我就是要离开你!离你越远越好!你这副假装痴情的嘴脸早就让我厌恶透了!不仅如此,我……唔……”
她有一肚子尖酸刻薄的话还没有说出口,已经被他紧紧堵住了唇。梅飞飞脑子里“嗡”地一声响,眼睁睁地看着傅远带着恼怒的俊脸在眼前放大,对口唇上那冰凉的触感一时来不及反应。一瞬间,掠过脑海的念头竟然是——这是我今生的初吻啊!怎么又是他!
然而只一闪神,这个男子身上熟悉的味道便扑面而来,梅飞飞顿时打了个寒战,这是在干什么!
傅远也不管这里有没有人来人往,紧紧地搂住了梅飞飞。一触及那两片柔软的唇,他立时不能自已。这是渴望了多长时间的一个吻啊!刚才的怒火此刻全化为满腔柔情,他闭着眼,沉溺得彻底,忍不住想深入下去……
“嗯……”唇上忽然一阵剧痛,口里弥漫起一股腥甜,他闷哼一声,终于松开了她,捂着嘴倒退一步。
他一松手,梅飞飞立即也倒退了三四步,站定了,喘着气,胡乱用手在嘴上抹了好几下,似乎想要抹掉他的印记,怒火烧得她眼眸晶亮晶亮的。
两人对峙了一会儿,谁也没有开口。只有树上的知了仍然毫无所觉,此起彼伏地叫个没完。
终于,梅飞飞愤然盯了一眼还在他手上牢牢躜着的录取通知书,恨恨地哼了一声,绕过他往回走。
傅远竟然没有再拦她。
走了几步,他的声音低低地从身后传来:“那我们的承诺呢?梅飞飞!”
梅飞飞陡然一震,停下脚步。
承诺?多么熟悉而又陌生的词汇啊!
原来,曾经你也是个相信承诺的人吗?
可惜,现在我却早已不再相信了!
突然之间,梅飞飞觉得这一切都显得这么可笑而又毫无意义。
“不要再提什么承诺了。如果你一定非得要一个理由。”她没有转身,只是无限疲惫地道,“那么我只能说,这是命运的安排。”
“命运的……安排?”他喃喃地重复。
她没有再回答,静静立了一会儿。夏天的风热情无限,吹得裙角飞扬不定。
仿佛过了一个世纪那么漫长,他低低的声音再一次响起,倘若说刚才他的声音里只是不甘与茫然,这时候听起来却充满了失落与绝望:“好,如果,这真是你想要的,我成全你……飞儿……”
最后两个字低如蚊呐,几乎微不可闻。梅飞飞的身子却颤了一下,心,痛得猛然抽紧。
身后终于传来缓缓的脚步声,无比沉重,而渐行渐远。知了的叫声,稍稍停歇,转眼又不知疲倦地大声起来。
她转过身,傅远刚才站过的地方,Z大的录取通知书,正在一地斑驳的树影中,静静地躺着……
母亲本要亲自送她,她却不愿意,最后与方吟一起坐了十几个钟头的火车,到达了G市。在火车站两个女孩分道扬镳,各自登上了驶向自己命运的公交车。
这真的是,金秋九月?
当梅飞飞独自拖着行李站在Z大正门的时候,心里怔然地闪过这样一个念头。
Z大是百年名校,校门有民国时期的建筑风格,古朴而庄严。进了校门就是一条直直的大道,稍稍地倾斜着向远处伸展。
此时正是九月初,在北方天气要开始转凉了,一些树木已经开始呈现出秋的姿态,而这里却没有。道路两旁繁茂的大树,枝叶生机勃勃地与彼此亲密相交,汇成了一条绿色长廊。那翠意浓浓的树荫,让人觉得秋天还离这里很遥远很遥远。的确,在南国之南的G市,这时候分明还是盛夏时节。
刚走进校门,一阵凉爽的风便扑面而来,下火车挤公车一路颠簸至此的疲惫,忽然就被吹散。梅飞飞仔细打量这片顺着大道延伸至不知何处的绿荫,发现栽种的竟然是细叶榕。榕树虽然繁植能力强,但要长高长粗,却是颇费时日的一件事。此时,这道路两旁的每一株榕树,都足有一人抱粗,高达十数米,没有几十年的沧桑只怕不能如此粗壮。梅飞飞忍不住伸手抚了抚,想起这经历过多年风霜洗礼的老树,屹立于此,不知默默地迎送过多少莘莘学子……
她一手拖着行李箱,肩上还背着沉重的双肩包,这时却怔然而立,神思飘远。
忽然有人在一旁问道:“这位同学,请问,你是来报到的吗?”这声音字正腔圆,珠圆玉润,话语里充满了柔和的笑意,使人一听便能联想到他脸上的微笑,真是说不出的动听。
梅飞飞蓦然转头,只见身旁的树荫下,不知何时已经悄然站了一名男子。这人身姿挺拔,如修竹玉立,气质出尘,又如暗夜优昙,等看清这人的样貌时,饶她算是比同龄人多活了几年,一瞬之间,也不由得惊艳了一下。
尖削的下巴,挺直的鼻梁,肤色雪白而温润如美玉,头发稍稍有些长,两侧微微盖住了耳尖,有几绺刘海随意地下垂,遮住了一部分的额头与眉眼。一阵风过,乌黑的发丝扬起,露出两道斜飞入鬓的剑眉,一双狭长的桃花眼中笑意盈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