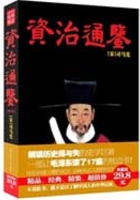我实在为难了,北京的医院我人生地不熟,到了北京我有能力让父亲立即住进医院吗?我住的是平房,没有卫生间,不论刮风下雨上厕所都要到胡同里的公厕。当时父亲体重只剩下70多斤,每天需要点滴葡萄糖,不要说一个月住不进医院,就是一周,怎么办呢?这时朋友鼎力相助,为我在长春市联系到一家医院。权衡利弊,我下决心把父亲送到长春的医院。我因为急着回单位上班,没有送父亲去医院,朋友从医院请来救护车把父亲接走。那一天,我看着远去的汽车,怎么会想到这是和父亲最后的一别呢?父亲去世后,每想到住院的情景,我都心如刀割。我虽然用种种解释为自己辩白,但我从来没有安定过,尤其想到父亲把自己的愿望存在心里,想到父亲怕儿子为难,宁可委屈自己,心里更加沉重。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之所以不安,是因为自己一直没有勇气把内心如实托出,一直为自己开脱。实际上我是不肯承认自己怕辛苦,不敢承认怕父亲来北京自己要东奔西走,托人情、找医院。今天,当我这样想,这样请父亲宽恕时,我心里终于好受一些了。
接到姐姐告急的电话,去火车站买票。因为是电话,你说病危没有根据,不卖;想买一张站台票,进了站再说,但没有当日的票,不卖;到航空售票处,当日的票早售完了,最早也要一周之后……呜呼!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老父已在弥留之际,我却还在千里之外,不知如何上路!幸而朋友聪明,买了一张去西北的退票,用这张当日票买了张站台票,这才得以混入站内,踏上了北去归家的路。但这时已经太晚了,父亲在我登上车厢不久,已经等不及我了。
6年过去了,6年的痛苦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的一生并不就是一件事,并不只是工作,人生还有那么多真挚的东西,那么多动人的感情,这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是能够让我们活得好、工作得更好的动力。父亲的一生没有壮烈的场面,也没有多少得意的时刻,任何地方也留不下他的名字,但父亲的去世,却最后给我留下了一笔遗产。这就是让我悟出了一个人生的道理:珍惜一切美好的东西,不要等到无法弥补的时候。
人生感悟
父爱内敛于心、含而不露;从我们生命酝酿时就已经开始,并将和血液一起伴随我们生命的全过程,让我们珍惜这些美好,不要等到无法弥补的时候,才想到补偿。多关心一下我们的父亲,莫让孤独沉默的灵魂遭受生命的凄凉!
父亲的冰糖葫芦
文/霍忠义
1997年春节前夕,因为有许多事情要处理,一直到腊月三十我才坐上了回家的列车。车窗外大雪纷纷扬扬,漫山遍野银装素裹,我很激动——一半源于美丽的雪,一半源于已经一年多没有见到的父母。
下了火车又换乘汽车,在乡政府门前停下来时已经是下午5点了,家在6里外的农村,我只能步行回家了。下了车,街上人很少,不远处有一个人正推着自行车卖冰糖葫芦,插在草杆子上的冰糖葫芦依然红得耀目,卖糖葫芦的人身上落满雪花,被许多小孩围在中间。糖葫芦卖得很快,他有点应接不暇,有的小孩趁机抓了糖葫芦就跑,他也不敢撵。我想起小侄女叶子,该3岁了,很爱吃糖葫芦,于是我走上前去。
但突然之间,我被自己的发现惊呆了——父亲?那卖糖葫芦的长者竟是父亲!我呆了半晌,才喊了一声:“爸!”父亲回过头来,发现是我,满脸的笑容将原本沧桑的脸挤得更皱,眉上脸上的雪花正簌簌消融成水。我的嗓子仿佛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没想到久别的父亲竟这样与我见了面。
一会儿工夫,糖葫芦就卖完了,我们一起回家,我想驮父亲,但父亲执意要带我,他说:“你坐那么长时间的车,太累了。”就这样,我们父子俩在漫天风雪中回到了家。
家里到处堆着山楂,我问母亲:“下这么大雪,父亲怎么还去卖糖葫芦?”两年前的一场车祸使父亲原本强健的身体变得衰弱,更何况,年龄不饶人。
母亲说:“你爸是去接你,顺便卖卖糖葫芦,也不知你到底哪一天回来,已经连续好几天了。”我的鼻子一酸,转身进屋去和叶子玩。
大年初一那天早上5点多钟,我正在酣睡,被母亲推醒:原来父亲已经在做糖葫芦了,母亲让我去帮帮忙。
我到厨房时,父亲已经将糖葫芦做好了,放在案板上晾着。我说:“大年初一为啥还去卖冰糖葫芦?”沉默了半晌,父亲说:“过年哩,娃娃都有压岁钱,大年初一吃的东西才好卖!”
“为挣几个钱连年都不过啦!”我心疼父亲。
父亲无语,自顾自地将冷却的冰糖葫芦收入纸箱,拿了插葫芦的草杆子,往自行车上扎。
母亲让我陪父亲一块去,我正要穿大衣同去,父亲却说:“你不用去啦!
一会儿就完。”说完,用一根粗绳将腰中的棉袄一捆,推着车出了门。
父亲走后,我和母亲闲聊,又问母亲:“大年初一也去卖糖葫芦,不值!”
母亲说:“孩子,你爸还不是为了你!”
“为了我?”我很惊讶。
“年前你来信说,年后想和梅子结婚,你爸寻思着,你工作才两年,梅子刚工作,你们没有钱,梅子那么娇贵的女娃子,不嫌你当教师的清贫,可我和你爸过意不去,我们想攒点钱,给梅子买个项链,买个戒指,城里兴这个。
唉!俗话说:人过40不学艺,你爸做了一辈子厨师,60多岁的人,又要学做糖葫芦,可真难为他啦,刚开始不会做,要么把糖烧焦,要么做得太软,糖葫芦粘在一起了。一次你爸去卖糖葫芦,做得太软,拿在手里糖往下掉,两手都是糖,粘得连钱都没法给人找……”
不等母亲说完,我就推车出了门。果然在乡政府门前找到了被许多小孩围住的父亲。正忙着卖糖葫芦的父亲抬头看见我时脸上有一种极复杂的表情掠过,穷于应付的他对我说:“你来收钱。”
卖完后刚回到家,父亲就说:“我再做一些,今天能卖!”说罢又钻进了厨房。
但是第二次卖得并不好,剩下许多。晚上,侄女叶子喊着要吃糖葫芦,父亲取了一支,小侄女拿着笑了。父亲给了我一支,说:“快吃,多吃几根,今天卖不完,明天就没法卖了——鲜也不鲜了。”看着剩下的那一大堆冰糖葫芦,我发愁了,母亲说:“没事,卖不成咱自己吃,去年一个冬天我和叶子没少吃你爸卖剩的糖葫芦。”我手里拿着一个鲜红晶莹的冰糖葫芦,那鲜红是血的颜色,那晶莹是汗的光泽,咬了一口,又酸又甜,我不禁掉了泪。
过完春节我要离家时,父亲拿出新新旧旧的2000元钱塞到我的手里说:“给梅子买个戒指,买串项链。”拿着钱我心里酸酸的难受,我实在没有勇气告诉白发的父母,这钱已经没有用了:就在我回家前的两天,梅子因为我没有给她买个订婚戒指就与我吵架,后来又提出分手。
“都说冰糖葫芦酸,酸里面它裹着甜;都说冰糖葫芦甜,可甜里面它透着酸……”每当这首歌响起时,我就想掉泪。
人生感悟
父爱总是在用最单纯的形式向我们展示着最让人感动的一面。能够为父亲所关爱,是作为儿女的一种甜蜜的幸福,但我们也无法忽略这种甜蜜中隐含的酸楚,因为这种幸福包含着父亲与自己淡淡的泪水。
陪父亲过年
文/天外孤星
天气愈来愈冷了,空中不时飘洒着几片鹅毛般的雪花。每天忙忙碌碌的,一晃竟到了过年的时候了。也好,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回老家陪陪父亲喝喝酒了。
我特地给父亲买了两瓶洋酒。父亲爱酒,但一辈子都只喝些自酿的米酒,那酒寡淡寡淡的,没什么酒味,不过是哄哄自己的嘴巴罢了。即便如此,母亲怕他年事已高,不胜酒力,遂限定他每餐只准喝一杯。父亲拗不过母亲,但又贪杯,便每每趁舀酒的机会大抿一口。那满满的一杯酒一抿便下去了,父亲“理所当然”还要加满,因此实际上,父亲每餐都要喝一杯半的样子。有时在酒缸边抿酒被母亲看到,母亲免不了要说上几句,父亲便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似的,羞愧地笑笑。
父亲每每吩我回去陪他喝酒,因为只有此时,他可以畅快地喝,母亲也不会唠叨什么,听凭我们父子俩大吃大喝。然而,我真正陪父亲喝酒的次数屈指可数,尤其是出国后,这种机会就更少了。不过,每年我都会向父亲许诺:今年过年,我一定陪你喝酒!
眼看就是大年三十了,今年别的活动我啥也不干,就是想陪父亲喝喝酒。没什么可犹豫的了,买张机票,一箭回来了。
父亲真老了。听说我要回来,白发苍苍的他一大早起来,硬是挤上那辆最早的公共车,赶到县城火车站来接我。远远的我就看到了父亲,那么冷的天,他棉衣都忘了穿,却伸长脖子在风雪的天空下瞪着浑浊的老眼东张西望。我快走到他的身边了,他还在焦急而忘情地找我。我望着像枯老的树桩一样的父亲,鼻子一酸,轻轻地说:“父亲,我回来了。”父亲扭头一见我,显得十分生疏地继续四周张望,我不知道他在找什么。过了好一阵子,父亲喉咙响了一下,闷闷地说:“就你一个人回来?”“嗯。”我突然明白父亲在找什么了:父亲年年期盼我带自己的男一半回去,可是我又让他失望了。父亲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像是对我,又像是自言自语:“下雪了,过年了。”
一到家,母亲早已忙开了。我把两瓶洋酒郑重其事地塞到父亲皲裂粗大的手中,父亲把酒瓶上的洋文细细地端详了一番,然后走进屋里,把它们藏了起来。出来时,父亲扛着满满的一缸酒,说,“今天咱们就喝家里的酒。”“行,行。”我连忙说。送他的洋酒本来就是让他以后慢慢喝的。
雪花三三两两地下,漫不经心的样子。风虽然冷,却是浅浅的。屋后的平台上,一张木桌、一缸老酒、几碟下酒菜。我坐在空旷的天空下,陪父亲慢慢喝着老酒,邻居的狗在我们的脚下晃来晃去。我说:“年初我就盘算着,过年的时候一定回来陪你喝几盅。”“嗯。”父亲应了一声,把满满的一杯酒喝了下去,我赶紧为他斟满。
记得有回出差,路过家门,我陪父亲好好地喝了一回酒。那是傍晚时分,薄薄的夕阳淡淡地照在身上,我们俩没有多余的话,只是你一杯我一杯地喝着酒。陪父亲喝酒,感觉真好啊。
可是今天,没有阳光,只有雪花,以及不时从远远的地方传来的鞭炮声。这时,父亲突然抬头,怔怔地望着我,说:“你出国也有五六年了吧?”“没有,不到三年。”“你答应过,过年的时候就回来陪我喝酒。”“我这不是回来了吗?”“你答应过,过年的时候把媳妇也带回来。”我一时语塞。父亲说:“你答应过,无论出国,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你都会想办法回来看我。”我喉咙猛地一哽。叫了一声“父亲……”这肘,我听到身后有轻微的抽啜,扭头,竟是靠在门槛边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