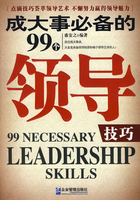我是个有趣的人,我觉得田原应该这么觉得,我始终做着别人认为无趣的有趣事,拿一件小东西,我就能联想到宇宙,而且越小越好,因为我的眼睛深邃且深沉。
那时的我也不例外
微风吹着操场上白杨树的叶子,叶子泛起淡淡的阳光。然后景色会映在教室的玻璃上。
我喜欢这样的风景,风景也需要像我这样的人
有时,我会衬着这样的风景,与田原讲讲有趣的故事。
我们从不谈课上学的,比如解释为什么天会蓝,海会深。人是怎么进化的,哪个才是生命的起源,什么是人生,什么是理想
我时常问她喜欢猫还是狗,还是蝙蝠?她总是笑而不答。
我想她应该都喜欢把。
我还会给她讲讲我与动物们的故事。
小时候,我买了一个小鸡仔,毛茸茸的,很好玩儿,我给它建了一个很柔软的窝,有水,有棉花,以为它会感到很舒服,它整整一晚上的叽叽喳喳更使我确信了我的观点,以为它很兴奋,却没想到第二天它死在了那个柔软的窝里。看到它合上的眼睛还有毛茸茸的小小的身体,让我感到仿佛失去了一个朋友,望着它安静的样子,感觉冰冷的身体有时是那样值得信赖。
它终于不会趁我不注意到处乱走,害得我到处找它。此刻它就躺在我的手里,而且如果我愿意,它会永远躺在这儿,从此以后不会再让心,但真实的它却离开我了。
有些东西看似真正的得到,实际却是真正的失去。可任何得到都有失去的那一天,所以世上遗憾总比团圆多。
我没有把感想告诉她,我不喜欢让别人因为我的故事难过。
她在旁边静静的听着,画面有些安静,也许她有些伤感,但那并不是难过。有些生命注定转瞬即逝,有些故事注定埋没人间。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纪念,顺便纪念一下我们的无能,纪念一下我们的渺小。或者选择不纪念,然后等着别人对我们无用的纪念。
生命有时候是一种罪过,它需要前生和后世的修行,并且用今生来弥补罪过。
我不想让她在伤感的惯性中
于是我又和她讲了讲我的蜗牛,它是一只很漂亮的蜗牛,是我的一个同学送我的。
一开始,它很害羞,我一碰它触角,头就会缩到壳里,我很茫然,因为这样很难喂它吃东西。
或许它饿了,又或许它熟悉我了,它不再那么害怕我,会当着我的面吃着我给的白菜叶,而且竟然还会吃西瓜。我把它放在一个窗台上的一个瓶子中,像水晶瓶那样的瓶子,把瓶子放在夕阳的柔美中,美丽极了,我总是望它望出了神,看它用它那几乎看不见的嘴一点一点吃着东西,每一口都感觉像是对我的赏赐。
她有了些笑意,我很欣慰。
“然后呢?”她好奇地问。
“我养了大约一个月吧,哎,好景不长,有一天我妈关窗户,把瓶子碰掉了地上。”
她立刻把手放在了嘴角,样子像是受到了惊吓。
“但蜗牛完好无损。”
舒了一口气。
她笑了,比刚才更浓。
我也笑了,不知她看没看出来破绽。
其实那个蜗牛死了,它的壳被摔碎了,它回不去了家,第三天就死了。
我本想谈些欢乐的话题,却找不出来,只好把结局说成了团圆。
她幸福的相信了,我感到很幸福。
我想有时故事的真实性有时并不完全取决于故事本身,这个结局对于我也许是假的,但对她我相信是真的,因为我在她的印象中是真的,起码那时是。
衬着景色,她也会给我讲讲她的故事。
我仍记得她说的牵牛花。。
“小学的时候,老师布置写作文,是关于花的,我很兴奋,因为本来就喜欢花。”
我好像听到了花的声音。
一个喜欢花的人的声音自然也像花。
“可老师让写牵牛花,我又不知道什么是牵牛花,只好到家外的花园去看看,小时候真是好笑,看什么都像牵牛花,于是我把它们的特点都写进去了,老师给我打个优。”
我刚要夸她
“可后来有人告诉我,花坛里没有一朵是牵牛花。”
“花都是五颜六色的,以后我就不愿再记任何花名了。花名是看到的人起的,看不到的人不需要记住。”
那天是我第一次知道一个仅仅是喜欢花的女孩儿。她就像一朵没有名字的花,没有人配得上给取个名字。而旁边的我就像一个被很多人取了名字,最终没有了真正名字的人。
我们都没了名字,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世上从此少了两个没有真正名字的人,而多了两个真正的人,却只有彼此发现了彼此,跟世上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