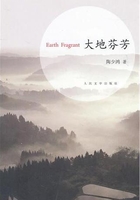忽然想到了什么,摸着下巴疑惑道:“柳诗情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暴力了?”
“她是病人!精神分裂者,”楚佑寒低声说。
“那又怎么了?”袁天辰一时没有醒悟。
“我跟她计较,我还是男人吗?”楚佑寒拍案而起。
“慢着——你,你刚才说什么了?”袁天辰慢半拍的跟上来,“精神病患者?怎么会这样?”
“如果我知道,她就不会得这个病。”楚佑寒气急败坏的锤了桌子一拳头,咔嚓一声,笔记本电脑震得飞起来,落在地上,粉碎。
空气里,即刻静得只能听见那砰砰砰不规律的加速心跳声。
“那她现在在哪呢?”许久后,袁天辰望着楚佑寒那张美得不是人却狰狞得比鬼吓人的俊脸,心提到嗓子眼,小心翼翼的问。
“美国治疗。以后,不需在我面前提起她。”楚佑寒望着窗外,面无表情。
袁天辰似懂非懂的点点头,“哦。”
美国纽约。
新工作,新环境,陈子墨适应得很快。唯一的烦恼就是,他单单适应不了柳诗情。
比如现在,柳诗情就分外的活泼,活泼并不是不好啦,但是不能过头。柳诗情一晚上在地上爬,跟牙牙学语的婴儿一样——可爱。他必须得承认这一点,她确实很可爱。
“诗情,你看这是什么?”他捧着一本儿童看画识字系列丛书之一,指着占据书页大半部分的动物插画,一丝不苟的问。
柳诗情咯咯咯的笑起来,轻轻戳了戳那头小牛的角,脆生生嚷起来。“这是小牛。嗷——嗷——”她学牛叫学得惟妙惟肖,学了一个晚上,以至于陈子墨有点吃不消。
他不过是想测验一下她的心智年龄而已,她有必要那么认真吗?
“诗情,你别叫了,好不好?来,我们吃点夜宵?”他试图制止噪音。
她愉悦的点头,“好啊!嗷——”然后又学了一声牛叫。
陈子墨差点喷血。
晚上,他梦见自己被一群牛包围,惊吓中醒来,发现柳诗情在隔壁嗷嗷的叫个不停。
她精力亢奋,但是他白天上班,时常加班,晚上还不能好好入眠,这便是他的烦恼。
他郁郁的起床,怒气冲冲的踢开她的房间,用很粗暴的口气吓唬道:“你要是再敢叫,我就把你拖出去喂狗。”
医生对病人,看来并不是都那么好耐性。别被天使蒙蔽了眼睛。
柳诗情将手塞进嘴巴里,惶恐的瞪着他,那双无辜的眸子清澈如泉水。陈子墨的怒气消了一些,却言不由衷的欺骗自己,“好吧,看在他那张别墅消费卡上,我就饶你一回。”
回到床上,终于可以睡一个安稳觉。
无论怎样,陈子墨被柳诗情逼得快疯了。
他不止一次的告诉自己,不行,得快点将她治好,不然下一个折磨精神病医生的可能就是他自己。
陈子墨决定,从那本红色笔记本着手。柳诗情发病的那一天,她正好在翻阅那本笔记,或许,那就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
可是,像陈子墨这种纯理科出身,看那些言情故事会掉一地鸡皮疙瘩的人,看到安静如那些写着关乎青春年少的痴爱时,他真的是看不下去了。
“整个一个傻女人!”他在心里咒骂了一句。
是的,安静如是很傻。因为陈陈告诉她,男朋友背弃了她,她就信以为真了。
卷了铺盖,裹了行囊,一个人躲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城市疗伤去了。
然而,她肚子里的孩子却在茁壮的生长着。无时不刻不提醒着她那一段耻辱的过去。
所幸的是,在陌生的城市,随便编一个理由,我已经成婚,丈夫在异地,便能搪塞那些人异样的眼神。
但是,不得不离开那个城市。
更不得不将肚子里的这个包袱甩掉,不然走哪里去都是一样。
她想过堕胎,但是没能成功,她走进医院,医生刚准备为她动手续时,她说她后悔了便不要命的跑出来了。
这个孩子,后来送人了。
安静如遇到了新的爱人,重建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却偏偏与旧爱重逢,他们成为了邻居。
这个时候,电话响起,陈子墨不得不放下笔记本去接电话。
接电话的时候,他有些心不在焉,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丝就在他眼前错综的纠缠在一起,他真想拿一把剪刀,咔嚓将他们全部剪断。
柳诗情和楚佑寒原来是那对情侣各自的孩子?
他们和他们的父亲母亲一样,相爱了。然后又分手了。这是多么惊人的相似。
他们在重复他们父母走过的路。
“陈医师,你有在听吗?”电话那头已经察觉到陈子墨在开小差,连连喊了他好几声。他才回过神来。“哦?”诺了几声,表示自己还在电话旁。
电话是一并随行到美国工作的助手小杨打来的,“KEVINDR说,柳诗情的病例疑似他之前诊治的一个病人,他想跟你讨论一下关于这种病例的若干问题。”
“那没问题。”陈子墨很干脆的应下来。他早已想甩掉这个包袱了,而KEVIN是这方面的权威,有他协助,相信不久就能睡上安稳觉了。
美国的咖啡厅可没有中国的那么娇小别致,偌大的空间,金转角装潢得奢华气派,整个房间显得粗狂又豪放。陈子墨约KEVIN在咖啡厅见面,心里忽然窜起一个问号:什么时候我也沾染了他的恶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