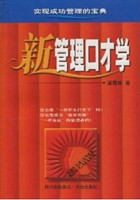最近的某个下午,七个女人聚在曼哈顿,有好烟、有红酒、有奶酪。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话题而来——一个男人——确切地说,是一个曼哈顿的钻石王老五,我们叫他“汤姆·佩里”。
汤姆·佩里,四十三岁,身高五英尺十英寸,棕色直发。他的相貌乏善可陈,可穿着倒是“出类拔萃”——几年前,他用纯黑色的阿玛尼西装配了一条诡异的吊袜带,这直到现在还被传为笑谈。他家从事制造业,富可敌国,第五大道和贝德福德简直就是他的家。他现在就住在第五大道的一幢高层建筑里。
在过去的十五年里,佩里成为了纽约的传奇,一提到“佩里”这个姓氏,每个人都会立刻想到他。他并不是那种“乱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花花公子。相反,他想结婚想疯了。佩里绝对是纽约最名副其实的“连环约会狂”,他平均每年有十二段恋情,但是每次都撑不过两个月,最短的一次只持续了两天。恋爱一出现状况,他就跳出来宣称“我又被甩了”。
对于那种三十岁左右,野心勃勃又有社会地位的女人来说,被佩里看上就像成人仪式一样,是一件既骄傲又纠结的人生大事。那种矛盾的心情有点像第一次坐豪华轿车并且第一次被抢劫的结合。
佩里的战绩绝对不输给纽约城里那些臭名昭著的花花公子。但是平心而论,他的资本可少多了——既没有考特·埃里克·沃奇梅斯特那么帅,也不像莫特·朱克曼似的挥金如土。
我真想知道,他到底有什么本事?
在座的每个女人都和佩里有过瓜葛——不管是上过床还是暧昧过——每个人都声称是她甩了佩里。当我提议大家聚在一起聊聊佩里时,没人拒绝。似乎每个人都对他有些余情未了——或是想复合,或是想复仇。
“像达里尔·凡·霍恩一样”
我们在萨拉家聚会,现在身为电影人的萨拉以前是个模特——“直到我厌倦了那些狗屎,并且胖了二十磅。”萨拉是这么说的。今天她穿着一件深色细条纹套装。“当你回顾你约会过的男人们时,佩里是最没意思的一个,”她说道,“你们想想是不是?这到底是为什么?”
在我们开始各自爆料之前,我们发现了一件让人困惑的事——就在这天早上,我们中的四个接到了佩里打来的电话,而这些女人早就和他没联络了。
“这只是巧合而已,我不觉得他听到了什么风声。”玛格达说。她是佩里多年的朋友。事实上,几乎她所有的女性朋友都曾与佩里有染,而且都是她介绍给佩里的。
“他对我们了如指掌,”一个女人说,“他就像《东镇女巫》里的达里尔·凡·霍恩一样。”
“呃,我看他更像凡·霍尼吧。”另一个女人评价道。我们开了瓶红酒。
“佩里的撒手锏是,”萨拉说,“你刚开始和他约会的时候会觉得他既幽默又会说话,不用工作,还随叫随到。如果一个男人约你一起吃午餐,然后等你吃完饭回去工作的时候,又打来电话问你:‘晚上六点再出来喝杯鸡尾酒怎么样?’难道你们不会心动吗?现在还有哪个男人会一天约你三次啊?”
“‘鸡尾酒’可真是一语双关啊!”玛格达说,“像是凯瑟琳·赫本和加里·格兰特一样。”
杂志编辑杰姬说:“我没认识他多久就开始频繁地和他约会,我们一周有五个晚上都黏在一起。他绝对不会让你觉得寂寞。”
“他很聪明,还超爱用打电话这一招,”萨拉说,“一天要给你打十个以上的电话呢。这会让女人觉得,他肯定是真的爱我。然后你就会忽略他是个长像滑稽的小矮子。”
“但当你突然看到他那些奇怪的吊袜带的时候,你才会突然醒悟过来,心想‘我的天啊,我究竟在干什么!’” 玫芙说,她是个有爱尔兰血统的诗人。
“接下来你会发现他其实一点都不幽默。”萨拉接着说,“他确实攒了一大堆笑话,但问题是当你重复听了一千遍的时候就会觉得烦透了。他就像有自动循环功能似的。”
“他还跟我说我是唯一一个和他笑点一样的女孩,”玫芙说,“但其实我压根就没觉得好笑!”
“接着你会看到他的公寓,那儿居然有二十五个看门人——这是什么状况?”
“你会想,他为什么不把他的那些蠢家具都扔了,直接住在卖门的商店里算了。”
“他还和我显摆过他那些手铐形状的纸巾架。他就是这么挑逗女生的——用纸巾架?真见鬼!”
第一次约会:44餐厅
所以,这到底是如何开始的呢?
杰姬的经历很有代表性。“我正在蓝带餐厅等位的时候,他走过来和我搭讪。他表现得很风趣,于是我想,我的天啊,我和这个人挺来电的。但我又怕是自己自作多情,心想他肯定不会再联系我的。”女士们纷纷点头——我们不都是这么开始的吗?
“结果他第二天早上八点就给我打电话了。” 杰姬说,“他问我要不要一起吃午餐,然后约我第二天在44餐厅见。”
萨菲尔——一个金发碧眼的单身母亲——笑着说:“他可隔了一天才约我去44餐厅的。”
“吃饭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真是既聪明又幽默。而且他还会趁热打铁,约你和他共度周末。”杰姬说。
“大概在我们第十次约会的时候他就让我嫁给他!”萨拉说,“就算是对一个像他那样的人来说,这进度也够快的。”
“他可是在第三次约会的时候就带我去见他父母了!” 布莱塔回应道,她是个瘦高的深肤色女孩,一位摄影促销员,现在已经结婚了。“只有我、他的父母和管家。第二天,我记得我坐在床上,看他展示他小时候的录像。他向我求婚:‘瞧,我可是认真的。’紧接着他居然给我叫了廉价外卖!我心想——嫁给你?你嗑药了吧?”
蕾蒙娜叹了口气,说:“不过话说回来,我当时刚和前男友分手,心情超低落。是他总陪在我的身边。”
于是我们总结出了规律。这些和佩里交往过的女人都是在刚跟男友或者丈夫分手之后,被佩里找上门来的——或者说,是她们主动勾搭佩里的。
“他就像个守在那儿的备胎似的。”萨拉说,“感觉像是你刚失恋,他就走过来问:‘请问你的心情不好吗?那我们约会吧!’”
“是啊,他就像是感情上的五月花号,”玫芙说,“把女人们从一个港湾载向另外一个港湾。你的心情就好像到了普利茅斯似的,感觉好多了。”
他摸透了女人们的心思。“他就像闺蜜似的。”这句话被大家提到了好多次,“他看的时尚杂志比女人都多。”萨菲尔补充道,“而且他对你的事比对他自己的事都上心。”
“他还超级自信。”玫芙接着说,“很多男人都会表现出他们白痴的一面,甚至有时候连自己的袜子都找不着——这可不会给女人留下什么好印象。但佩里却总是对你说:‘我会给你百分百的安全感。你可以放心地依靠我。’诸如此类的话。这总是能让你觉得很温馨。真的,这才是女人们想要的,大部分男人都不懂。佩里很聪明,不管他是真心的还是在装装样子而已。”
接着我们又聊到性事。“他的床上功夫绝对没得挑!”萨拉说。
“和他做简直爽翻了!”萨菲尔兴奋地附和道。
“你们真觉得他那么棒吗?”杰姬问,“我可觉得差劲透了。拜托,想想他的身高好不好!”
聊到这儿,我们发现佩里似乎满足了我们对男人的全部梦想——像闺蜜似的善解人意,体贴入微;在床上又生龙活虎,大展雄风。
那么他到底是哪儿不对劲儿呢?
佩里:尺寸很重要
“就好比是,”玫芙说,“当你多愁善感、神经兮兮的时候,他是最完美的情人;而当他帮你解决了所有麻烦的时候,他就成了一个最大的麻烦。”
“他变得难以置信地刻薄。”一个女人说道,大家都表示赞同。
“有一次,”杰姬说,“我说我穿小号的衣服,结果他居然说:‘你穿不了小号,至少也得是中号吧。我知道小号看起来是什么样的,相信我,你可不是。’”
“他一天到晚让我减肥,还要求我减十五磅以上。”萨拉抱怨道,“我和他交往的那会儿,绝对是我有史以来最瘦的时候。”
“这是种心理转移。男人只有对自己那个地方的尺寸不满意的时候,才会要求女人减肥。”一个女人干巴巴地加了一句。
玫芙爆料了他们去太阳谷滑雪的事。“刚开始很完美,佩里把一切都弄得妥妥当当。他买了票、订了酒店,我以为这会是一次很棒的旅行。”结果他们在去机场的路上就开始争执不休——他们都想坐在车里的同一个位置;上了飞机,他们还在吵,空姐不得不强行分开他们两个。(“我们那会儿在吵到底谁呼吸到的新鲜空气更多。”玫芙解释说)一路上他们就没消停过。第二天,玫芙就开始收拾行李。结果佩里幸灾乐祸地说:“哈哈哈,外面有暴风雪,你哪儿都去不了!”玫芙反击道:“哈哈哈,我有脚,我坐公交车走!”
一个月后,玫芙回到了他老公的身边——这并不是个例,在座的女人中大多数都甩了佩里,重新投入前任的怀抱。
这并不代表佩里放弃了。“他给我发了好多的传真和邮件,还有上千个未接来电……”萨菲尔说,“这种感觉挺不好的。其实他的内心很强大,我相信有一天他会成为好男人的。”
“我把他的信都留着呢,”萨拉说,“都写得好感人啊!你甚至能看见他眼泪的痕迹呢。”她走出房间,取了其中的一封,大声念给我们听:“感情上你并不欠我什么,但我希望你可以勇敢地向前踏一小步,拥抱我对你的爱。我没有送花给你,因为我不愿用非我所创的事物,来分享或贬损你的感情。”
萨拉微微一笑。
“我们要结婚了”
在甩掉佩里之后,女人们都宣称自己过得很不错。杰姬在和她的私人教练约会;玛格达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蕾蒙娜嫁了人,有了身孕;玫芙开了自己的咖啡馆;萨菲尔和她的一个老相好重温旧梦;萨拉和她包养的一个二十七岁的小白脸玩得正开心。
至于佩里,他最近搬家到了国外,仍然坚持不懈地寻觅新的结婚对象。有人听说他最近被一个一心想嫁给公爵的英国女人甩了。“他总是和不适合他的女人约会。”萨菲尔说。
六个月后,佩里回过一次纽约。他邀请萨拉共进晚餐。“他握住我的手,对他的朋友说:‘这是我唯一真心爱过的女人。’看在往日交情的分上,我跟他回了公寓,小酌了几杯。然后,他无比郑重地向我求婚,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呢,于是我决定折磨折磨他。”
“他告诉我:‘我希望你不要再和别的男人约会了,我也不会再去见其他女人。’”
“于是我一边嘴上答应,一边心想这怎么可能,他住在欧洲,而我住在纽约啊。但第二天早上我就接到了他的电话,他说:‘记着,你现在已经是我的女朋友了。’”
“我说:‘好吧,佩里,就算是这样吧。’”
他回欧洲之后,萨拉立刻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一个早上,她正和她的新男友缠绵的时候,电话响了。是佩里。萨拉接电话的时候,她的新男友问她:“要来点儿咖啡吗?”佩里立刻开始发火。
“那是谁?”他问。
“朋友。”萨拉说。
“朋友?早上十点?你是不是和别的男人睡了?我们要结婚了,而你却敢和别的男人睡?”他摔了电话。
结果他一个星期之后又打来了。“你准备好了吗?”他问。
“准备什么啊?”萨拉问。
“我们要结婚了,不是吗?你后来没再和别人上床了,对不对?”
“听着,佩里,我手上的戒指可还没影儿呢!”萨拉说,“你干吗不打电话给哈里·温斯顿预定点首饰,然后我们再来谈这件事。”
佩里没给哈里·温斯顿打电话,他也几个月都没再和萨拉联系。萨拉说她有点儿想他。“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她说,“他总是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天色渐晚,但没人想要离开。大家都发着呆,回味这个男人在她们心中的影像——似乎是佩里,但又仿佛不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