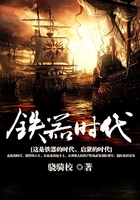任何故事总是开始于“过分的天真”。有一天,我正待在公寓里享用饼干和沙丁鱼大餐,突然接到一个熟人的电话。他的一个朋友刚去了梯吧——一个只允许情侣进入的性爱俱乐部。他在那里大开眼界,玩得爽翻了,脱光了的人们就在他眼皮底下疯狂做爱。SM俱乐部和这里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在前者你可绝对见不到真枪实战的性爱场面。这家伙的女朋友都有点儿被吓傻了——不过当另外一个一丝不挂的女人故意和她贴身而过的时候,她“好像挺有感觉的”。反正他是这么说的。
打电话的这个男人对那地方实在太感兴趣了,但他并不希望我把俱乐部的名字写在这儿。他怕这地方也跟纽约其他体面的去处一样,被流行彻底毁了。
我忍不住开始浮想联翩——身材完美的俊男美女;试探性地挑逗爱抚;只戴葡萄叶花环的金发女孩,长发像波浪一样披在肩上;年轻男孩在腰上象征性地围着葡萄叶,笑起来牙齿洁白;我也穿着葡萄叶制成的超短草裙,香肩半露。我们衣着光鲜、忐忑不安地走进去,然后笑容满面、一身轻松地走出来。
俱乐部答录机的声响把我猛地拽回现实。
“在梯吧没有陌生人,只有你未曾认识的朋友。”说话的声音性别不明,而这一走神我就只听到了最后一句:“供应果汁吧台、冷餐和热餐自助。”——这声音怎么听也不会和性爱或裸体沾上任何关系啊。这让我想起感恩节庆典的时候,就在十一月十九日那天,有个狂欢的主题叫做“东方之夜”。听上去挺有趣吧,但结果“东方”指的是食物,什么异国情调的东方帅哥连个影子都没有,完全就是个“东方美食之夜”。
我当时就应该把这个念头扼杀在摇篮里的。我真不该听信莎莉·提斯戴尔那些可怕又饥渴的话。她热衷于“公开群交”这一现象,并在那本《和我谈性》——一本雅痞色情书——中说道:“这是语言里真正意义上的禁忌……如果性爱俱乐部随心所欲地发展,堕落的地狱之路必将开启……是的,正如人们所害怕的那样,道德的界限必将崩塌……无法控制。”我本该问问我自己,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必须亲眼见识一下。于是,星期三晚上,我的日程表上写下了:“晚上九点,时装设计师卡尔·拉格菲尔德的晚宴,波威里酒吧;晚上十一点半,梯吧性爱俱乐部,东二十七街。”
邋遢女和中筒袜
一聊到性事,人人都兴致勃勃,就连参加卡尔·拉格菲尔德晚宴的那些当红嫩模和举足轻重的时尚编辑们也毫无例外。事实上,我们这桌末座的那几个人简直亢奋得像疯子一样。一个深色卷发的年轻美女声称自己是半裸夜店的常客,脸上一副“看破世事”的样子——实际上她才不过二十岁。但她看得上眼的夜店只有“比利”之类的,因为那儿的女孩都“货真价实”。
于是在场的所有人都附和说胸部小一点也无所谓,起码比隆胸强多了。“真心话”开始了:在座的各位男士,哪位和胸部都是硅胶假体的女人上过床?没有一个男人承认。不过一个三十多岁的艺术家否认得很牵强。“哈,你肯定有经验,”一个大圆脸的酒店大亨挑衅说,“而且你一定还觉得挺享受的!”
“我没有!”艺术家辩解道,“我只是不介意这个而已。”
第一道主菜把他从尴尬境地中解救出来。每个人都忙着倒酒,没有闲话的工夫。
第二轮现场调查开始了——邋遢的女人是不是床上功夫更厉害?酒店大亨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如果一个女人家里没什么乱放的东西,你就能判断出她绝对不是那种一天到晚待在床上,会叫便宜的中国餐外卖在床上吃的女人。她早上非得把你弄起床,然后把你扔到厨房餐桌上吃吐司面包不可。”
听到这儿我心里有点五味杂陈。我绝对是世界上最邋遢的人了。我床底下估计还有几百年前叫的左宗棠鸡外卖的盒子呢。更不幸的是,那些东西都是我孤零零一个人干掉的。算了,不想说这个。
牛排上桌了。“格子裙和中筒袜最能让我疯狂了。”那个艺术家说,“要是看见一个女人穿着那些玩意儿,我肯定完全没心思工作了。”
“我可不这么想。”酒店大亨反对说,“我觉得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你在街上看见前面走着一个陌生姑娘,当她转过头的时候你发现她和你想象中的一样漂亮。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这代表你这辈子都别想追到她!”
艺术家往前凑了凑,说:“我曾经为了一个女人茶饭不思,五年没去工作。”
一片沉默。没人比他狠。
巧克力慕斯上桌了,而陪我去梯吧的男伴也出现了。梯吧不允许客人单独进入,必须男女相携才可以。所以我邀请了我的上一任男友山姆,一个投资银行家。这可是个明智的选择。首先,他是唯一一个肯陪我去的人;其次,他对这种地方颇有经验——很多年前他曾经去过柏拉图庄园,那是他当时的女朋友提议的。结果刚一进门,一个陌生女人就径直地向他走来,把他的命根子掏出来摆弄。他的女朋友看到这番景象,吓得哇哇乱叫,夺门而出。
于是新一轮的讨论不可避免地开始了:热衷于性爱俱乐部的都是些什么人?我似乎是唯一一个毫无见解的人。尽管没人真的去过那种俱乐部,但在座的每一位都坚决声称只有“从新泽西来的乡巴佬”才会去那儿寻欢。有人说性爱俱乐部可不是那种说去就去的地方,你得有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比如工作需要什么的。他们说的这些丝毫没让我感觉好受一些。我只好叫来服务生,又要了一杯龙舌兰酒壮胆。
山姆和我起身告辞。一个打着流行文化旗号的作家连忙发表最后的意见:“那地方肯定糟透了!”他语带警告的意味。其实,他自己从来没去过,却说得跟真的似的。“除非你能主导、控制那种场面。在那种场合你必须得强硬。要把持住自己!”
僵尸之夜
梯吧坐落在一个白色石头建筑里,墙上画满了涂鸦。入口很隐蔽,还围着一圈弧形的金属围栏,看起来很像是山寨版的美仑大酒店。我们正要进去的时候,一对男女刚好从里面走出来。那个女人一看见我就立起大衣领把脸挡住了。
“里面好玩吗?”我问她。
她惊恐地看了我一眼,没做声,神色慌张地冲向了出租车。
大厅里,一个深色头发、穿着条纹橄榄球衬衫的年轻男子坐在狭小的前台里,完全不睬我们。他看起来顶多十八岁。
“是在这儿付钱吗?”
“每对八十五美元。”
“信用卡行吗?”
“只收现金。”
“能开收据吗?”
“不行。”
在安全声明上签字之后,我们拿到一张临时会员卡。会员卡上写着:“俱乐部内禁止卖淫、禁止拍照,不得携带照相或摄像设备。”
我走进大门,正暗自期待能看到狂热的性爱场面,可迎接我的却只是一张热气腾腾的餐桌——就是答录机里提到的冷、热餐自助。餐桌前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孤零零的标语牌立在桌上,上面写着“用餐时请勿裸露下体”。然后我们看见了经理鲍勃,一个穿花格衬衫和牛仔裤的健壮男人,还留着小胡子,看起来活脱脱是个乡下宠物店的老板。他告诉我们,这家俱乐部能生存十五年之久的秘诀就是行事谨慎。“在我们这儿,”他补充道,“不行就是不行,没有商量的余地。”他还跟我们说当个偷窥狂没有什么可耻的,大部分人都是从偷窥开始的。
那我们都偷窥到了什么呢?好吧,房间里放着一个巨大的充气床,有几对正在上面努力地猛干;旁边孤零零地放着一张情趣椅,八爪的那种;按摩浴缸边上,一个裹着浴袍的胖女人在抽烟;有几对男女目光呆滞,不知道在干吗(难道今天的主题是扮演僵尸)?还有好几个男人正没精打采地各自为战。看来看去,最火热的还是那些该死的自助餐桌(里面都有些什么玩意儿?迷你热狗)。
只有这些,太让人失望了。在法语里,梯吧的意思估计就是“骗你玩”。
凌晨一点,人们各自散去。穿浴袍的那个女人告诉我们她是从拿梭郡过来的,她建议我们周六晚上再来。“周六晚上可是饕餮大餐。”她神秘兮兮地说。
我估计她指的是自助餐,不是那些来这儿的男人。
莫蒂默餐厅里的下流话
几天之后,我和几个闺蜜在莫蒂默餐厅共进午餐。聊天的主题毫无意外地再次围绕性事展开——这当然离不开我在性爱俱乐部的所见所闻。
“你难道不喜欢那儿吗?”夏洛特问我,她就是那个伦敦来的记者,“我还挺想去那种地方的。看着那么多人在你面前做爱一定觉得欲火焚身吧?”
“完全不觉得。”我一边说一边把一个鲑鱼籽玉米馅饼往嘴里塞。
“为什么呀?”
“根本就没看到什么啊!”我解释道。
“有帅哥吗?”
“最倒胃口的就是这个,”我说,“那儿一半以上的男人都长得像精神科医生。我下次再去做心理咨询肯定有心理阴影。你想象一下,那些又矮又肥、满脸胡渣儿的男人,光着身子躺在地上,呆滞得像僵尸似的,口交了一个小时还没完。”
没错,我对夏洛特坦言,我们也全脱了——但身上还裹着毛巾。不,我们没有做爱。真的没有,因为我半点儿兴致都没有。中间一度有一个三十多岁、身材高挑、一头披肩黑发的迷人女郎走进来,在喧杂的房间里引发一阵骚动。她像猴子一样光着屁股,然后没几分钟就消失在一群赤裸的胳臂大腿中间了。这种场面本来应该是非常火爆香艳的,但我当时只想到国家地理纪录片里那些交配的狒狒。
事实证明,不管那些媒体新闻再怎么渲染,露阴癖和窥阴狂永远不会成为主流,连SM也是少数人的边缘行为。性爱俱乐部的问题出自那些俱乐部里的人。来这里的都是些接不到戏的女艺人、找不到出路的歌剧演员、落魄的画家和作家,或是永远熬不出头的公司小主管之类的。这些人会在酒吧里缠着你,把你堵在角落里喋喋不休地抱怨——从他们的前妻、前夫一直数落到昨天的消化不良。他们无法适应社会的生存规则,不管是生活还是性事都只能扮演边缘角色。你永远也不会希望你的性幻想里有这种人出现。
不过公平来讲,梯吧里也不全是矮胖、苍白,只会机械运动的僵尸。离开的时候,山姆和我在更衣室里再次遇到了那个窈窕的黑发女郎,还有她的男伴。这个男人是标准的美国帅哥,面庞洁净,轮廓鲜明。他跟我们侃侃而谈,说他是曼哈顿人,最近刚创立自己的事业,和那个女人以前是同事。他看了看自己的女伴——她正在匆忙套上鹅黄色的职业套装,然后微笑着补充说:“她今天晚上可算是圆梦了。”她瞪了他一眼,转身走出更衣室。
几天之后,山姆打电话来,我歇斯底里地向他抱怨。他无奈地问我:“难道整件事不全是你的馊主意吗?”
然后他问我有没有从中得到什么经验教训。
我说有啊,我学会了一件事——要做爱的话,哪儿都比不上家里。
但这一点你从一开始就心知肚明,是不是,山姆?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