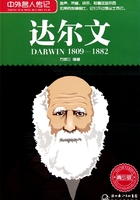回旋上升的台阶尽头,一扇门开了。波恩——一个内衣模特兼影视新星——在他的公寓门口等着我们。他懒洋洋地斜倚在门边,一只手臂举过头顶搭在门框上,深棕色的头发挡住了半个脸庞。看着我们气喘吁吁地爬着台阶,他大笑起来。
“你们总是忙这忙那的。”他说,仿佛生活就应该是整天待在卧室里。你一见到他就会想起来编剧斯坦福·布拉奇对他的评价:“波恩每次出现都像是带着灯光师一样耀眼。”是啊,耀眼到你都不能直视他,生怕刺瞎了你的双眼。
“拿衣服做比喻的话,波恩绝对是黑貂皮大衣那个级别的。”斯坦福说。他最近就跟着了魔似的,话题从未离开过波恩。他会突然莫名其妙地打电话给你,问:“波恩和基努·里维斯谁更性感?”哪怕你根本不认识波恩,也不在乎谁是波恩,你还是会叹口气顺应他:“波恩吧。”
可能这种附和是出于愧疚的心理。你觉得自己应该知道他是谁——他那么出名,时代广场上的巨幅广告牌和城中的公交车上到处都是他代言的广告——只穿内衣,几近全裸,露出完美的肌肉轮廓。但问题是你几乎从来不去时代广场,也从来不注意公交车——除非它们要撞到你了。
但斯坦福一天到晚在你的耳边念叨。“那天波恩和我路过他的广告牌,”他说,“波恩居然想扯下来一块放到他的公寓里——比如他的鼻子那块。我跟他说他应该把内裤鼓起的那部分拿走。这样,再有女人问他那儿有多大的时候,他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说十四英寸了。”
“今天波恩干了一件非常可爱的事情,”斯坦福说,“他居然想请我吃晚饭。他说:‘斯坦福,你为我做了那么多,我也想为你做点儿什么。’我说:‘你别傻了。’但你知道,他可是我这辈子遇上的第一个主动请我吃饭的人!你能相信吗,这么美丽的男人居然人这么好!”
你终于败给了斯坦福的喋喋不休,决定亲自看看波恩到底是何方神圣。
“你会成为巨星的”
我第一次见到波恩是在波威里酒吧,他当时正和斯坦福在一起。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不会对他有任何好感——喜欢一个二十二岁的绣花枕头?别开玩笑了!我估计他也不会对我有什么好感。他看起来可真蠢。更何况,虽然性感偶像在杂志和电视上看起来叱咤风云,但本人绝对会让你大失所望。上次我碰见的那个看起来就像条恶心的蠕虫,跟性感完全不沾边。
但波恩似乎打破了这个常例,他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肤浅。
“我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笑着说。
然后他就在人群中消失了。
两个月之后,我在一个模特的生日派对上又见到了波恩。他站在房间的另一边,身体懒洋洋地靠着吧台,正微笑着看着我。他对我招招手,我走了过去。他一直拥抱我,荧光灯对着我们闪个不停。然后我莫名其妙地和朋友吵了起来。
波恩坐在桌子对面,关切地靠过来问我是不是还好。我说是,心里想这人恐怕不知道我跟我的朋友一向是这么说话的。
斯坦福在好莱坞很吃得开。他带着波恩去洛杉矶参加各种试镜,争取在电影里露脸的机会。波恩给斯坦福的语音信箱里留言说:“你真棒,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你。你绝对会成为巨星的。虽然我已经和你说了很多遍,但我还是要说:‘你是明星,你是明星,你是明星!’”
斯坦福边听边大笑。“他在学我呢!”他说。
我和波恩待在波威里酒吧喝酒聊天,一醉方休。
拿A很容易
波恩住在一间狭小的公寓里。窗帘、床单、被子、沙发……放眼所及,全都是纯白色。我溜进洗手间,企图窥探他用什么牌子的化妆品,但架子上的都是很大众的开架货。
波恩在爱荷华的得梅因长大。他的父亲是教师,母亲是学校护士。念高中的时候,他没有和学校里的风云人物一起厮混,而是主动去辅导低年级的孩子。他门门功课都拿A,大家都很崇拜他。
虽然八年级的时候他就被班上同学票选为最帅的男生,但他那时候从未想过要当模特。他暗自向往着如侦探之类神秘而且有趣的职业,但最后还是遵从父亲的期望,去爱荷华大学念了两年的文学。他有一门课的老师是一个年轻的帅哥。他把波恩叫到办公室,紧贴着波恩坐下,手放在波恩的大腿上。“你知道的,拿A很容易。”他一边说,手一边滑向波恩两腿间的鼓起处。在那之后,波恩再也没去上过课。三个月之后,他辍学了。
最近波恩总是收到电话留言,但内容都是歌。一开始他以为音乐结束之后就会有人说话,但始终没有。于是他反复地听那些歌,试图从中找出线索。“是个男人。”他肯定地说。
爱荷华的童年
我和波恩像小孩子一样趴在床上,手托着脸,小腿交叉着跷起来。“给我讲个故事吧!”我说。“嗯,我最近总是会想起来我的前女友的事。”他沉思着。
那是一九八六年的夏天,波恩只有十四岁。爱荷华的夏日总是天空蔚蓝,田野碧绿,仿佛能听见玉米生长的声音。男孩子们一整个暑假都和朋友们出门嬉闹,开着车在城里乱晃。
波恩跟着家里去了爱荷华州最大的集市。他和几个伙伴在畜牧展示区里漫无目的地溜达着,他的眼前突然一亮。他看到一个女孩正在专心地给一只小母牛洗澡。他激动地抓住他朋友的手臂,大声说:“那个女孩就是我未来的老婆!”
那之后很久,他都没有再遇见过她。一年之后的某个傍晚,他终于在镇上的舞会再次看到了她。他们约会,在圣诞夜里闲逛。“然后我就被莫名其妙地甩了,”他说,“那时真是痛苦了很久。”
又过了一年半,她回来找他。但他装出一副嘴硬的样子。“其实我想她想得发疯。”他说,“然后某天我终于妥协了。”
他们断断续续地交往了几年。女孩后来在爱荷华城当计算机编程师。他们现在还有联系。“也许你有一天会娶她吧?”我问。他笑了,露出漂亮的牙齿,鼻子微微皱起。“也许会。”他说,“在我心里这始终是最美好的一段回忆,每次想到都觉得很宁静。”
“波恩总是嚷嚷着他总有一天要回到爱荷华,当个警察,生几个孩子。”斯坦福说。
“这个想法真可爱——只要他别真的这么干。”我回应道。但不知为什么,我突然为自己的刻薄有点儿后悔。
“我知道我很神经质”
周六晚上,我和波恩去罗斯面包店买吃的。两个女警察躲在角落里抽烟。天气炎热,路上行人的短袖衫都被汗水浸湿了,看起来脏兮兮的。波恩和我分吃了一个奶酪火腿三明治。“我自己就能吃掉四个,”他说,“但我不能吃。现在哪怕吃一个汉堡我都会后悔半天。”
波恩很在意他的外表。“我一天换五套衣服。”他说,“谁出门前不照上百次镜子啊?我的公寓里有两个穿衣镜,我就在两个镜子之间走来走去,心里想着:‘嗯,在这面镜子里我看起来不错,但我还是要看看在另外一面镜子里看起来怎么样。’我知道其实没什么差别,但大家不都这样吗?”
“我经常走神,”波恩接着说,“脑子里乱糟糟的,思绪特别混乱。”
“那你现在想什么呢?”我问。
“你的鼻子。”
“谢谢夸奖。我恨死我的鼻子了。”
“我也讨厌我的鼻子,”他说,“太大了。不过我觉得这跟我的发型有关。斯坦福那天跟我说:‘我喜欢你今天的造型,头发很饱满,显得鼻子小。’”我们都大笑起来。
吃完饭,我们在街上走着。波恩突然用手肘碰了碰我。“他们把‘狗狗’拼错了。”他说。我朝他指的方向看过去,一个穿着工装的男人举着牌子站在一只巨大的灰色獒犬旁边,牌子上写着“狗狗出售”。
“什么?”那个男人问。他身后停着一辆红白相间的破旧卡车。
“‘狗狗’,你拼错了。”波恩说。
男人看了看牌子,嘿嘿一笑。
“喂,我说,那边的街上在卖同样的狗,只要两百块,你怎么要两千块呢?”波恩问。男人只是笑了笑。
回到家,我坐在床边,手撑着脸,望着波恩。波恩躺在床上,一只手放在牛仔裤的腰带上。
“上一分钟我可能还在街上耍帅,下一分钟我就会毫无原因地感到难过。”他说,“我知道我很神经质——我能感觉到。我的自我意识很强,我喜欢分析自己,评判自己。我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很小心。”
他接着说:“我说什么之前都会在脑子里过一遍,这样我就不会说错话了。”
“你不觉得这样很浪费时间吗?”我问。
“也用不了几秒钟啊!”他说。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我在外面的时候,如果有陌生人过来问我是不是模特,我会说:‘不是,我是一个学生。’”
“然后呢?”
“然后他们对我就不感兴趣了。”波恩笑着看着你,眼神好像在说:“你连这都不知道?”
这时我又接到了斯坦福的电话。“波恩给我的电话留言真是全世界最可爱的!”他说,然后放给你听。波恩的声音响了起来:“斯坦福,你是不是死了?死哪儿去了?你不接我电话,肯定就是死了!(一阵长长的大笑)记得赶紧给我回电话!”
“伊凡娜·特朗普的男佣?”
我喜欢和波恩在他的公寓里消磨时光,这让我想起十六岁时的青涩感情。那时候我还在康涅狄格的小镇上,和一个远近闻名的帅哥约会。我们在他的房间里抽着大麻,腻在一起,而父母还以为我们去骑马了。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我那时都干了些什么。
你望向窗外,看阳光映在破旧的褐石建筑上,一片暖洋洋的金色。“我一直都想有个孩子,从小就想,”波恩说,“这是我的梦想。”
但那已经遥不可及了吧。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在那些事情发生之前,在今天之前。
几周之前,波恩得到了一个出演男二号的机会。电影里的其他演员全都是好莱坞的新星。波恩在一个派对上喝多了,带了一个超模回家,完事之后才知道她是剧组另外一个男演员的女朋友。那个演员威胁说要杀了他们,于是波恩只好带着那个姑娘躲了起来。只有斯坦福知道他们在哪里,负责当他们的传话筒。剧组愿意花大笔钱请波恩出来,但斯坦福回敬他们说:“你们把他当什么了?伊凡娜·特朗普的男佣吗?”
波恩跟我说,“我不相信那些胡扯。我还是我,一点儿都没变。人们总是对我说,你千万不要改变——可我能变成什么样呢?变成无赖?蠢货?自大狂?我很清楚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什么觉得我会变?”
“你笑什么呢?”他问。
“我没笑,”我说,“我在哭呢。”
后来,斯坦福问我:“你有没有觉得波恩最近对什么事情都不敏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