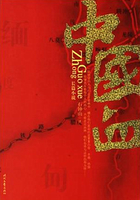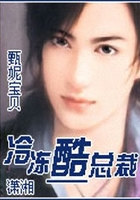君越和心悦走累了就躺在那块最大的礁石上彼此依靠着,晚风吹拂着温柔极了“丫头”君越无神的望着夜空。
“嗯!”心悦应了一声,别过头去看君越的侧脸。
“我想哥哥了”君越伤感的说。
心悦本想挖苦他两句:“男子汉大丈夫,还离不开哥哥了?”可是她知道君越此刻心里一定很难受,于是她笑了:“君越,别灰心,我们一定能找到君卓哥的。”
“你怎么不说我‘男子汉大丈夫,还离不开哥哥了’?”君越半开玩笑地问道。
“我…我本想说的嘛!”心悦嘟嚷着,两个人同时扑哧笑出了声。
但日清晨,心悦睁开眼睛,去找水喝。当她来到海边时,一艘大船映入眼帘。心悦惊喜的连忙跑到君越身边:“君越,君越,船,我们有救了。”
“真得?”君越连忙站起来。
“是真的,你看”心悦突然不说了,对于‘看’这一类的字眼,她比君越都敏感君越变得沮丧极了,低着头不说话。
心悦找不到合适的安慰,她来到海边拼命地狂喊着“喂!”
不知什么时候,君越顺着声音跌跌撞撞的摸索着过来陪她一起喊“君越?”心悦疑惑的看着他。
“我们一起努力!”君越冲他烂漫一笑。
心悦重重的点点头
船越向前声音就越清晰,偶尔被涛声覆盖住。
“秀措?你听!是不是有人在叫?”君卓问。
秀措仔细一听,回头向船舱道:“好像是啊!大哥,把船向岸靠去,岸上好像有人。”
“哎!”良哥应了一声将船靠向岸边。
君卓看到了礁石上站着的两个人,他激动地奋力向他们挥手:“君越!心悦!”
心悦欣喜若狂,抓住君越的手:“是君卓哥哥,他来救我们了,君卓来救我们了,你听到了吗?”
君越那无神的眼睛因为难过与激动而掉下泪来,心悦不再说话。
船靠岸后,良哥将搭板搭到岸上。心悦小心在意的将君越搀扶住,踏上搭板上了船。
君卓向君越扑来,心悦松开了君越的手,君卓将君越紧紧抱住。
秀措在一旁被这一幕感动得流下泪来,心悦欣慰的笑了。
君卓好一阵才松开君越,一双眼睛像是长在了弟弟身上,他抓着君越的肩关切的问:“君越,你们怎么在这儿?
君越自嘲似的笑了:“哥,我和心悦可没你命好被救到船上。这几天,我和心悦沿着海岸走走停停,可吃了苦头了。“心月在一旁帮腔道:“是啊是啊,又累又饿的。“君卓看看心悦、君越两个人衣衫褴褛,浑身脏兮兮的的确狼狈极了,不禁心中一揪:“对不起,对不起,让你们受苦了。““哥,这又不是你的错!跳崖还有挑地方的权力吗?”君越不满地嘟嚷道君卓破涕为笑了。
夕阳西下,一群人围在饭桌前吃饭。
君越因为什么也看不到,心悦便在他身边把夹来的菜都放到他面前的碗里,把碗筷塞到君越手里:“君越,吃吧,都弄好啦。”
君卓奇怪地盯着心悦做完这一系列动作才注意到君越朝心悦感激地笑了笑,然后机械地把碗凑到嘴唇边。便把拉着往嘴里送饭边调皮的说道:“我可不客气了啊,这些天可把我饿坏了。心悦,你也吃啊。”
心悦触到了心伤处,哽咽着嗯了一声,端起碗筷送到唇边挡住脸,怕人看到她流出的泪君卓看出心悦的反常,不由得心生疑窦。待转眼去看君越时才发现他那双无神的眼睛,他被吓了一跳:“君越!”
“嗯?”君越应了一声。
君卓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他一边抬手在君越眼前晃了晃,一边盯着君越那双毫无反应的眼睛秀措忍不住了:“君卓哥哥,君越哥哥的眼睛一直看不见吗?”
君越做了答:“不是的、不是的,是这次摔下崖不小心伤了眼睛。哥,你别太担心了。心悦说了,她能治得好。心悦,你不是这么对我说的吗?”
心悦点点头,放下碗筷,露出一张泪脸。
君卓忍不住了,一行清泪落下。君越那双无神的眼睛和那张坚强的脸像两把刀子在剜着他的心。
秀措连忙安慰他:“君卓哥哥,不是有心悦姐姐吗?你别担心了,她一定能帮君越给哥哥治好的。”
君卓哽咽着点点头:“心悦,交给你了啊。”
心悦这个鬼丫头立刻发挥了她的特长,猛地站起,像得到任务一样严肃的向君卓保证:“保证完成!”
这下一桌子的人都逗乐了,包括一直未曾开口说话的耶律良哥“哥,要我说,还是跟你在一起的好!一跟你分开吧,再见时我就一定得弄一些伤回来!”君越开玩笑道:“记不记得当年我进宫调粮,差点被打死。还好有追月公主救了我,”
耶律良哥听到‘追月公主’四个字,心中一颤。
是夜。
秀措、君卓、君越、心悦四个人并排坐在船头,聊得好不开心。
耶律良哥站在了心悦身后:“心悦姑娘?”
“你叫我?”心悦闻声回头。
“对,跟我来,我有话问你!”良哥给了他一张非去不可的脸。
心悦向众人投去求救的目光。
“我陪你!”君越道。
“不行,必须她一个人。”
“好啦,好啦,一个人就一个人嘛!凶巴巴的”心悦嘟嚷着睁开君越的手,随良哥一前一后进了船舱。
心悦一直慌张的**着衣角。
良哥暗自好笑她这种小女儿的心态,索性自己坐下也不招呼她,只是问了她一句:“你与他们兄弟俩是勤王军的手下吧?”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心悦撇撇嘴。
“在福安,李骁然托我弟弟休哥找到勤王军中一个叫心悦的姑娘”
“骁然哥,死了?”心悦心中一阵难过。
“对,他是为保卫福安而死的。他托我弟弟找到你,并带你到成都找我父亲问清你的身世。”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只是一个没爹没娘的孤儿,从小流浪在中原。你父亲怎么会知道我的身世?”
“那要等见到我父亲才知道,我只想替我弟弟完成这件事。不知道,你对你自己的身世感不感兴趣?”
“当然感兴趣了”
“那你敢不敢跟我回成都?”
“敢!有什么不敢的!”心悦不假思索道,无意间看到了外头,便想起什么似的继而失落的低下了头,沮丧的说:“算了吧,君卓君越兄弟俩”说完她冲良哥抱歉地笑了笑,便跑了出去
不承想,她一头撞到了君越怀里,幸亏君越站得稳才没被撞倒,只是朗朗跄跄的后退了几步。心悦心中有事,不免发了火儿:“喂!走路不长”见是君越,她惊得捂住了嘴巴君卓和秀措被她夸张的样子逗乐了。
君越笑着对心悦说:“我陪你去成都”。
这话里充满了情谊,就连仅有的责备都被情谊包围住了。
旦日,一只雄鹰披着霞光展翅飞来,凌空长嘶一声划破了寂静。
众人赶了出来,良哥打了个响亮的口哨。
那只凌空盘旋的鹰便直线飞了下来,落在了良哥的手腕上。良哥爱惜的摸摸它的羽毛,从它的爪子上解下了一个信筒后放飞了鹰。然后打开了信筒,看罢了信。
秀措问:“大哥,写的什么?”
“父亲说休哥回家了,叫我们不要去中原找他了。尽快回成都,休哥只停几日便走。”良哥道:“秀措,我们照原路返回。”
“嗯!二哥终于回家了,耶律伯伯是真想他了。”秀措点点头。
就这样,他们一行人向成都赶去。
休哥回到了自己的家中,父亲的苍苍白发深深刺痛了他的心。
这一夜他本想与父亲促膝长谈的,可当父子二人面对面时却又不知该说什么好。彼此沉默了好久,烛台上的蜡烛流着泪,火苗固执地踹动着,仿佛要摆脱烛芯,去替蜡烛擦掉眼泪“父亲近来可好?”休哥被蜡烛感动了,于是问出了口。
“好、好,老二,你呢?”父亲点点头,猛地盯着休哥的眼睛问,眼神中留露出的是父亲对儿子的关爱。
“父亲”这爱逼得休哥说不出话来,他低下了头:“孩儿”
“你有话就说吧”
得到父亲的许可后,休哥说了出来:“父亲,宋朝彻底覆灭了。文天祥兵败被俘,很快就会押送到成都来,是吗?”
“是的,张弘范送来的信中是这样说。”
“还有,文天祥一直不肯投降是吗?”
“是的”父亲本想多说两句的,可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是该赞扬文天祥的宁折不挠换是该骂文天祥的不识时务?
“怎么说呢?父亲,一切都在孩儿的意料之中,元国胜利了、征服了,孩儿是该自豪的。然而文天祥,孩儿的确不想他死。”休哥仰头盯着天花板,仿佛是在对他说话“不到万不得已,没有人想他死。他若肯降,皇上会接纳他的。”
“他若肯降,那他就不是文天祥了。”
父亲没有做任何表情,良久他才很空洞的笑了:“你回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吗?”
“我是回来找文天祥的,李骁然在福安对儿子说的话或许你听见了,我知道这样说会伤了父亲的心,可我不想撒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