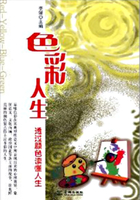天祥抓起酒杯欲饮,睿龄突然拦住了他:“张大人,您太客气了。丞相近日偶感风寒,身体欠佳、不宜饮酒。”
“小酌一杯不为过吧?”
“张大人,不该关心关心丞相的身体如何?”
“倒是下官失礼了”张近东心想也许是自己太过心急了,刚想说什么。
睿龄松开了抓住天祥的手,装作无意的用胳膊肘碰倒了自己的酒杯,酒撒了一地,酒杯倒在地上摔得粉碎。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张近东紧张、天祥疑惑、睿龄却连忙站起来,天祥要替他擦擦胳膊上的酒渍,他却躲到了一边
还不等有人开口说话,副将便推门而进:“报将军,元军已兵临城下。”
“来得好快!”天祥向睿龄低语,却发现睿龄死盯着副将。
副将眼神闪烁,似羞怯、似慌张
“张将军,来得好快呀?”睿龄向张近东开了口,一股不可置疑的怀疑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
天祥奇怪的盯着睿龄,顺着睿龄的目光他看到了张近东在睿龄那犀利的目光的逼视下闪烁不定、似慌张、似逃避
张近东只尴尬了那么一下,便换上了一张笑脸,准备以笑脸相迎。
“您难道就一点点察觉都没有吗?还是你跟本就已暗中与元军勾结设计陷害丞相?’”睿龄冷笑着将天祥面前的那杯酒泼了地上,地上立刻泛出白沫,而他的外衣上有酒渍的地方已是暗呈黑色。
张近东不明白到底哪儿出了破绽,愣在了那里。
天祥看到了地上的一滩酒渍变成白沫,睿龄的衣服上的酒渍也成了暗黑色,顿时明白了过来:“张近东!你是忘了你自己姓甚名谁了、忘了自己生于何处养于何地了吗?,如今宋朝外环频繁、岌岌可危,正是需要大宋臣民同仇敌忾、抵御外敌的时候,岂能甘心投敌,卖主求荣,至天下百姓于不顾?”
张近东被天祥的当头棒喝气得脸色发青,恼羞成怒的喊道:“来人,将他们抓起来。”
谁知踏门而入的却是清羽,他向睿龄道:“先生,外面都安排妥当了。”
“好”睿龄点点头。
“待清羽结果了他!”清羽反手持剑,剑尖直至向张近东张近东不敢逼视清羽犀利的杀气,绝望的喊出了一句:“宋朝已无药可救,丞相你执意抵抗,到头来不过是徒劳无功、一场空啊!”
清羽出剑的速度很快,只消片刻张近东已血溅当场“先生,丞相,大家都还在外头等着呢。”
清羽收起了剑。
三个人先后出了门,只见院中以元庆等兄弟为首,身后是数百勤王军及张近东的旧部近千士兵,仿佛在等天祥的一声令下、仿佛只要天祥一声令下,便可将元军赶出丁州一样。
“丞相,您也别怨张大人,他的妻儿双亲全都在元军手中。”一位副将站了出来。
天祥的心被刺痛,清羽看了看睿龄,眼神中颇有悔意。睿龄和天祥相视一下,三人不约而同向屋里倒在血泊中的张近东表示歉意。
“将张大人以礼安葬了吧,看来敌军是有备而来,我们不能贸然出兵,元军会对张大人的家人不利的。”天祥想了想说道。
“也好,丞相,我想我们应当退守龙岩。对张大人的葬礼也应隆重,最好让元军知道,这也是保护其家人的有效方法,可也不排除元军会恼羞成怒’。”睿龄冷静道:“不过我想,当我们退出丁州之后,他们得到了丁州,也许不会动手,毕竟他们要的只是丁州。”
“祁先生,你的意思是用丁州换张近东的家人?”巩信发问道。
众人也纷纷表示不可。
天祥开了口:“我同意先生的建议,丁州今日失去,明日还可以夺回来。可要是人没了性命,还怎么要的回来?”
“元军若是轻易得到了丁州以后屠杀城里的百姓,那可怎么办?”元庆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不会!”天祥冷静道:“忽必烈改国号为‘元’,想必是想争霸中原、逐鹿天下,一味残忍屠杀,只会激起对方的仇恨,对他来说未必是件好事。”
天祥说的一点也不错,忽必烈在派兵与宋军交战之际曾向他的士兵讲过:“寡人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原本软弱不堪的南宋何以今日变得如此强大,逼得你们节节败退?刚刚浴血奋战得到的城池一个个又被他们重新夺了回去…再照此下去,形势将对我大元非常不利!难道他文天祥真就如此厉害?不!一直以来,我总以为中原人只会舞文弄墨、只会种庄稼,所以只要我们对他们耍狠、只要够狠、只要拿起手中的刀就足以吓破他们的胆!现在看来,武力并没有吓破他们的胆,反而激起了他们的仇恨!他们的战斗方式不还都是老样子?可为什么我们的仗打得越来越不顺?你们想过没有?所以我们不能一味野蛮、残忍,要学会动脑子、讲计谋!要知道,屠杀无辜的百姓并不代表你战功卓著,那是你凶残成性;相反少屠杀一些无辜的百姓,你也不会因此减少威名,更不是什么软弱,而是仁者之风。”
当时在场的是耶律良哥、耶律休哥兄弟两,李恒,伯颜及他们各自带领的军队勤王军抵达龙岩之时,已是夕阳衔山。
“龙岩易守难攻,我们岂不是被困在此了?”天祥道。。
待他回头时,睿龄正在环顾四周。
“你又看到了什么?”天祥笑着问。
“黑水河”睿龄指了指脚下流淌的河水。
“我们没有办法渡过的,太宽了。”
“怎么没有办法?你们当初从镇江一路回到福安,什么难关没闯过?”
“清羽跟你讲的吧?他对你无话不说。”
“可是有件事,他宁愿拦在自己的肚子里也不肯对我讲。”
“是冰玉姑娘的事吧?”
睿龄点点头而说不出话来,他那平日里总是冷静、自信的脸上泛起了一片乌云,淡淡的、忧郁的乌云。
“我想你一定有办法离开龙岩吧?”
“我没有十足的把握,随机应变吧。”
“若能离开龙岩回到南剑州,我想让若藜跟恪儿回老家找怀山去,这样他们娘俩的安全有了着落,我的心也能安了。”
两个人在山头伫立交谈着。
“清羽,先生在丁州府衙的时候给你耳畔说了什么?”可风问。
“没什么,后来你们不是都看到了吗?”清羽笑了笑。
“啊!祁先生简直跟神仙一样,什么都事先知道。”心悦一脸崇拜。
“傻丫头,那叫运筹帷幄、成竹在胸,这都不懂。”君越含着责备的笑了。
心悦毫不领情的回敬道:“傻小子,就你多嘴,你问问这儿的人除了我,谁不知道啊?”
“我是在教你好不好?好心当成驴肝肺。”君越气哼哼的转过身不去理她。
心悦觉到自己的过分了,她拍拍君越的肩,大大咧咧的笑了“嘿!傻小子,给我看看你的驴肝肺好不好?”
君越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惹得大家都笑了。他们在小山坡上说说笑笑,笑声飘出了很远很远
旦日清晨。
天祥见睿龄还在山头观察地形,几步跟了上去:“先生,如何?”
“你看”
天祥顺着睿龄所指,远望左边一代尽是草冈,即元军屯粮的地方;右边是通往黑水河,元军沿河扎营。
“他们还真把我们当神仙了?”天祥笑了。
“元军下令众将协力守住龙岩,却按兵不动。”
“元军坚守不出是想等我们弹尽粮绝之后再来攻击?”
“的确,但是现在北风猛烈、天气干燥,关左尽是枯荣,火攻才是上策。”
“可是关左的砍柴小径崎岖狭窄,兵马过不去,元军又用木石把路阻塞,更是没发前行啊。”
“有一个好办法,务必要使元军相信我军打算渡过黑水河,偷救丁州,丁州不是在龙岩的下游吗?”
“可是若我军渡河一半,元军便出兵偷袭龙岩,又该如何是好啊?”
“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你是想诱敌出动?”
“对!可我现在头疼的是如何让元军得到这个消息,耶律休哥将军智勇双全,可不是那么好骗取的,何况还有一个伯颜,此人更难应付。”
就在此时,吴俊来了。
是君卓和君越俩兄弟向天祥和睿龄前来报告的。
“天祥哥,我见到吴俊了。“君卓道。
“真得?吴俊?他没死?太好了!他在哪儿?“天祥激动不已。
君卓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君越老不情愿的嘟嚷了一句:“他还不如死了的好。““君越!“君卓低声责备道。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天祥见兄弟俩的神色不太对,连忙问道:”吴俊怎么了?““他、他,他叛变、投敌了嘛,现在是来劝降的。“君越憋不住了。
“君越!“君卓见拦不住君越,转脸向天祥软语央求道:“天祥哥,你别怪他好不好?我们都知道他不是一个贪图荣华富贵的人,可是天晓得他受了多大的罪…”
天祥仿佛一句都没听进去,转身便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