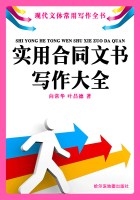“我觉得你是一个好人,因为豹儿喜欢跟你在一起,还记得在忘忧峰,豹儿喜欢在你脚下酣睡吗?”她笑着说,手伸向他的脖颈,轻搂上,他点头,下巴抵在她额间,“那也许是我这十八年来过得最清净的日子了。”
“以后让缘儿陪你一起过下去。”
他怔怔的看着怀中的女人,爱得那么干净,话简单得让人发笑,但却又能让人不得不去回应她的天真。
“好。”
他想抓住她,就算以后会出什么事,他都想就这样抓住她。
第八天,他走出了小屋,在屋檐下,他们告别,桦枫将一方金色锦帕给了皇甫少卿,他又转身交到了单依缘手中,只嘱咐拿好。
“是什么?”
“婚书。”
打开一看,绢面红纸,上面着了金色,上面有她和他的名字,还有他的金印。
在无其他话语,他骑上马飞奔而去,而她立在湖心,看着渐消失的背影发呆……
这一走,又是三十一天,她竟记得这么清楚,从她走后,她就开始数日子,第三十三天,策马奔驰而来的却是桦枫,下马既跪在她面前,面色凝重。
他说,王爷负伤了,在追击敌军的途中中了埋伏,现在在帐内,药也不进了,他来时血还未止住,只是嘴中不停叫着她的名字。
她随他上了马,心中如被刀剜了般难受,她差点就晕了过去,可是不可以,她要见到他,一定要。
“缘儿……缘儿……”
他就在昏迷中一直呼唤着她的名字,剩余的意识让他强撑着,可是就是无法进药,连御医都束手无撤。当她进到帐中,只是微顿后,就即刻端起案前的汤药,药碗里的汤药仍然冒着热气,她就举碗喝下,跪在了皇甫少卿身旁,一口噙住他冰冷发颤的唇,舌尖断续推送,不知彼此的气息交缠了多久,持续的动作,药也终于见底了……帐中所有人动容,这女子早有听闻,多是她与皇子间的纠缠不清,却不曾想,却如此至情至性。
见他稍好些,她环住他的手终放下,回头便问桦枫附近可有森林,桦枫说营地后即是一片森林,说罢,她将腰间一颗白色药丸放进他口中,“这是保命参丸,可续命,但药力不会久,我要进森林采集草药为他止血。”
她走出了帐,将帐外一匹马牵住,跃身上马,一夹马腹驰进那片茫茫山林中。
直到傍晚,她终于从雾气中走了出来,神情疲惫,就像耗尽了一辈子的力气,手中紧捏着许多药草。
桦枫站在帐外,看尽一切,此女人只得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见,只是先叹了这真情是否能值回。
桦枫跟随皇甫少卿十年,从几岁起就在他身边,女人对他根本算不得什么。
只是这女人,他看重了,桦枫心知,他动了真情,只是比起他的雄图,还是有轻有重的。
帐内,她找回了最珍贵的止血药,也把自己摔得遍体鳞伤,额头那点点血珠就是为采这颗灵草摔进了崖壁内,她不会武功,但是有些东西支撑着她爬了起来。
第二日凌晨,血止了,他退了烧,身体又开始慢慢恢复了体温,她也终放心的在他身边躺下,怕触到他的伤,她只蜷缩在榻角沉沉睡去。
“她就一直这样吗?”
“是的,王爷,单姑娘已经连续三天这样守在你身边了。”
皇甫少卿眉宇一皱,看着睡着的她,还拉着自己的手,自己就蜷在那一角,醒来时,她还未醒,还是招了桦枫进来,只是很小声,桦枫也一五一十的将单依缘如何喂他进药,进森林寻药,然后整夜守护的事,都一一禀告了。
“恩,知道了。”他声音有些沙哑,“不过,桦枫,是不是该改口了?”
桦枫低下了头,额头又是一阵冷汗,以后不能在叫单姑娘,要改叫王妃了,婚书还是你递出去的呢。皇甫少卿让他退下,捂着伤口移到了她身旁,顺着她的后背躺下,从身后将她娇小的身子搂进了怀中,头埋进她的颈窝中,“父皇负了我的母亲,而我皇甫少卿永不会负单依缘。”
“一言为定。”
不知何时,她已醒来,听到了他的话,他怔了怔,随后就更紧的搂着她,“恩。”
他想她明白他给她的爱,那是从未给过别人的,他将玉配交到她手中,只淡淡说那是他母亲遗物,也就在没说什么,看见她如获珍宝般拿稳在手中,他终放心了,原来她也是那么在意。
半月后。
那日起来,他没有立刻穿戴,只是看着榻上的单依缘,俯身将她吻醒,在她耳边轻声说:“起来,帮你的丈夫穿衣。”
她慢慢睁开眼,“可是我不会。”她脸上歉意浓重,手缓缓的扯上他半开的袍领,皇甫少卿极力忍着那股又被她勾起的欲望,单手捧上她的脸,道:“不会,我教你。”话,很轻,情,却浓。
她笨手笨脚的将他的玉带缠成了一个解不开的结,“我说了我不会。”她羞红了脸,一个妻子连给丈夫系带都不会,他到不急不恼,反复教她如何解开,然后在系,指尖缠上指尖,低头抬眸间都是那么暧昧痴缠,“慢慢来,就会越做越好。”
她用了半个时辰才系得得体了些,她兴奋的跳到了榻上,一手搂过他的脖颈,在他额间亲了一下,“我终于会了!”她兴奋得有些过头了。
他怔了怔,身子一僵,也不躲避,只是嘴角显出笑意,一手揽过她的细腰,抱进怀中,也不说什么,低头就吻进她的唇口中,似要将她整个吞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