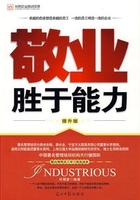“……到现在为止死亡人数已有200人,差不多有相同数目的人失踪。”局长说道,“东海岸仍然不断传来调查报告。荷兰那边的情况也不是很好。他们决了口的海堤长达数英里。我们自己也损毁了两艘巡逻艇。并且‘沙秋鸭”号的总指挥官也失踪了,那个英国广播公司的家伙也找不到踪影。那艘古德温的灯船被掀离了它原来的系泊处。比利时以及法国方面还尚未获得任何报告。等到所有的问题清理出来后,想必赔偿额也不少。”
第二天下午邦德回到了局里。他身上缠着密密麻麻的白色绷带。只要稍微动弹一下,就会感到止不住地疼痛。平时的英俊在他的脸上已经看不到了,一条红色的伤痕呈现在他的左颊与鼻梁之间,但他的两只眼睛仍然很有神。他戴着手套的手上拙笨地夹着一支香烟。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局长居然还会请他抽烟。
“先生,有关于那艘潜艇的什么消息吗?”他问。
“那艘潜艇所在的方位他们已找到了。”局长感到非常心满意足地说,“它就在差不多180 英尺的海底躺着。现在,打捞导弹残骸的打捞船正在那里停泊。已经有潜水员下去视察过,然而它的船壳并没有对发出的信号作出任何的反应。今天一大早晨,在外交部的苏联大使急得团团转,他说一艘他们的打捞船正全速从波罗的海开来,不过我们的人已经通知他,由于那些下沉的残骸有碍于航行,因此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继续等待了。”局长嘿嘿笑着,“假如恰好有人在英吉利海峡下180英尺的深度航行的话,那么那艘潜艇肯定会有所妨碍的,不是吗?但是我真是为我不是内阁成员而庆幸啊。”他语气非常平静地说。“从广播中断开始,他们始终在不停地开会,休会,然后再开会。还没等爱丁堡的律师打开德拉克斯写给全世界的信,他们就已经全都被瓦兰斯给抓起来了。我猜测,那封信肯定非常可怕,可能是和上帝的末日审判书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昨天晚上瓦兰斯把那封信带到国会。”
“我都听说了,”邦德说,“我在医院的时候他就不断地在电话上询问我所有细节,一直询问到半夜。对于有关内情的问题我一时半会还无法回答他。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他们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来使一项有史以来最大的掩盖真相的工作得以完成。编出非常多的科学解释:只燃了一半的是什么燃料;大爆炸是由意想不到的碰撞引起的;什么敬爱的爱国者雨果先生和他的所有助手们不幸罹难;潜艇遭遇意外而下沉;最新的试验模型;由于命令失误,感到心情非常沉痛,还说多亏仅仅只有一个骨干人员,要通知给这些人的直系亲属;英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员也不幸遇难;把英国皇家海军旗错看成是苏联海军旗是难以估量的错误,它们的设计非常相似,已经从残骸中找到了皇家海军旗,诸如此类等等。”
“不过到底应该如何处理那核弹头的爆炸问题呢?比如放射性、原子尘埃以及那蘑菇云,这些东西无疑将会带来非常多的问题。”
“与此正好相反,对于这些问题他们并不担心。蘑菇云将会飘走,就如同一次同样大小规模的常规爆炸所形成的烟云一样散去。对于整个情况军需部并不是非常清楚,因此必需把真相跟他们书说一下。昨天晚上他们派人拿着计数器在东海岸测量了一晚上,这个时候他们仍然没能够拿出什么确切的报告。”局长冷笑了一下,“当原子云升上高空之后,海面上的海风真是帮了一个大忙。
当时的风力非常猛烈,云雾是一定会飘到某个地方的。并且假如幸运的话,这云雾将会飘向北方去。也许你会想到,也有可能它会再飘回来。”
邦德凄然地笑了笑,“我已经能够明白了,那也只能这样了。”
“没错,”局长把烟嘴拿起来,然后边装烟边接着说道,“谣传肯定是无法避免的,并且现在这些谣言已经有所耳闻。你与加娜·布兰德小姐躺在担架上被人从基地往外抬时,很多在现场的人都看见了。波沃特斯公司也对德拉克斯起诉,要求他把所有新闻纸的损失都赔偿给他们。同时还要对阿塔波车被撞翻以及司机丧生一案进行调查。至于你的那辆汽车的残骸自然会有人替你掩饰过去,另外,”他看着邦德,眼光里带着责备,“还找到了一支长枪筒的科尔特手枪。还有军需部,昨天瓦兰斯只得派一部分人去帮着清理那个厄布里街上的房子。不用说,整个过程都如同是在冒险。就算是编得再圆,谎言也终归是谎言。但还能如何选择呢?是去找德国人的麻烦,还是对俄国人进行开战?要知道大西洋两岸的很多人都非常愿意找一个借口。”
局长稍微停了一下,他划着火柴点燃烟斗。“假如公众对这些解释能满意的话,”
他又略加思考后接着说,“反过来这件事对我们也是有好处的。一直以来我们都需要一艘他们的高速潜艇来作研究。另外,能够找到他们原子弹的线索也令我们非常高兴。俄国人清楚他们的冒险失败了,马林科夫的政权肯定无法掌握稳定了。换句话说,就是另一次政变很快就将会发生在克里姆林宫。至于德国人,嗯,我想我们大家都明白有很多**分子隐藏下来,这个问题将使议会更加小心翼翼地对待德国重整军备的问题。至于我本人的些许收获,”他苦笑一下,“我的这份工作以及今后瓦兰斯的安全工作也就可以轻松些了。这些政客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原子时代出现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恐怖的破坏分子——带着沉重皮箱的小人物。”
“这件事报纸会报道吗?”邦德表示怀疑地问。
局长耸了耸肩膀。“就在今天早晨,首相会见了所有的编辑们,”他将另一根火柴划燃点着了烟斗,“我猜测他应该是已经侥幸应付过去了。假如以后那些谣言再次出现的话,可能他就还得再接见他们,并透露出一点儿事情的真相。当然这些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做记者的都有对重要的事情穷根究底的毛病。因此现在一定要努力争取时间,以避免会有人出来闹事。目前,所有人都在为‘探月’号而深感自豪,他们还没有认真追查到底是出了怎样的差错。”此时,局长办公桌上的放置的传呼器突然发出一阵蜂鸣声,红光一闪一闪发亮。局长将单耳听筒拿起来,俯下身来,“喂?”停了一会儿之后,“请为我接议会。”从桌面上放着的四部电话的电话架上,局长拿起了一只白色的听筒。
“是的,”局长对着电话说,“请讲。”没有什么声音。“是的,先生,已经接通了。”他将他的保密器按扭开关按下来,紧紧地把听筒凑到耳朵边上,丝毫不漏一点声音。停了稍长一会儿之后,局长左手拿着烟头吸着,之后又把烟头取下来,“我没有什么意见,先生。”
又过了一会儿,“我为我的手下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同时他本人也非常自豪。是的,先生,他们一直都是这样。”局长的眉头皱了皱,“假如你允许我如此说的话,先生,我觉得那样似乎不是很明智。”稍作停顿之后,局长的脸色再次变得明朗起来。“非常感谢您,先生。当然,相同的问题,瓦兰斯没有遇到。那是他起码应该得到的。”又是一阵间歇,“我很清楚,一定可以解决的。”再次间歇,“你真是一个好人,先生。”
局长将手中的白色听筒放回到电话架上,只听那个保密器按钮喀嚓一声再次回到了普通通话的位置。
局长眼睛盯着电话看了一会儿,仿佛是对刚刚的这一番通话还有些疑惑不解。之后他将座椅转离桌子,两只眼睛望着窗外凝神思考着。
房间里一片沉寂,没有任何声音。坐在椅子上的邦德慢慢活动着身子,以便能使自己坐得更加舒服一些。
他在星期一曾见过的那只鸽子,当然也可能是另外一只,又飞上了窗台,拍打着洁白的翅膀,翘着尾巴,在窗台上来回踱着,咕咕地不停叫着。过了一会儿之后,这个小家伙又振翅飞向公园的树林。各种车辆那催人昏昏欲睡的沉闷声从远处传来。
邦德意识到,所有的一切几乎都已经平静下来了。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真该算是万幸。假如不是由于一个为满足其强烈的占有欲而在牌桌上肆无忌惮地行骗的人;如果不是局长答应帮助他的老朋友;如果不是邦德隐约中记住了那个牌骗子的数次教训;如果不是加娜·布兰德与瓦兰斯的小心谨慎;如果不是加娜·布兰德清晰而准确地记住了那串数字;如果不是整个事件中的那些细枝末节以及机遇,伦敦城现在早已成为了一片废墟。
局长转过椅子来,那把椅子发出了刺耳的嘎吱声。邦德专注地看着桌子对面那双沉思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