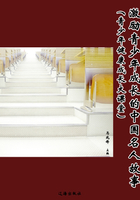为了使接头容易,邦德走出包厢,站在过道中等待着,心里默念着当天的接头暗语。英国间谍之间接头用语,通常只是几句日常用语,每个月按日期变换内容。
车厢晃了晃,列车慢慢地驶出车站,驶进了阳光中,过道尽头的门“砰”地一声关上了。邦德还没听到脚步声,但是,窗玻璃中突然映出了一张红润、金色的脸,那个人已经走到了他的身边。
“对不起,能借一下火柴吗?”
“我只用打火机。”邦德掏出他用旧了的打火机,递给了他。
“那更好。”
“直到用坏为止。”
邦德紧盯着对方的脸,按照程序说出最后一句暗语:“请吧,朋友。”等待着对方的微笑。
可是,那厚厚的嘴唇只是微微动了一下,眼睛中射出阴森森的目光。
他脱下雨衣,露出里面穿着的褐色花呢旧上装和法兰线长裤。上装里面有一件淡黄色的衬衫,系着一条英国皇家炮兵红蓝相间的专用领带,并打着蝴蝶结。邦德对打蝴蝶结的人向来没有好感。他觉得这种人爱慕虚荣,这也是行为举止粗俗的一种标志。但从工作出发,邦德还是决定抛开这一成见。那个人右手小指上戴了一只闪闪发光的金戒指,上衣的口袋中插了一块红色印花手帕,左手手腕上戴着一只老式银质手表。他右手握着栏杆站着。
邦德知道有这么一个典型——战争期间,有一个公立小学的学生被抓了,可能是情报领域的人抓的,抓了以后没人知道该怎么办,因此他就呆在了占领军的部队里。最初,他是军事警察,后来作为高级军官调回国,就被提拔进了情报局。然后被派到里雅斯特,在那里他做得很出色。他想一直留在那里,以免受英国严格的纪律限制,可能有一个女朋友,也可能和一个意大利人结了婚。在撤军以后,英国情报局需要一个人在意大利建一个通信站,的里雅斯特理所当然就成了这个站点。而这个人也是现成的,他们就派他过去。他做的都是一些常规的工作,如在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警察局、情报网络等地套一些没什么价值的情报。一年有一千英镑的收入,因此他生活得还不错,但是也别想从他那得到更多的情报。然而,这一次,他突然单独过来,一定是被这个紧急的任务震惊了。他可能对邦德有点妒忌。脸色奇怪,眼神看起来非常凶猛。但话又说回来,像他们这样长期在国外做情报工作的人应该是这样的,在那样的环境下不得不变得凶猛一点。他是一个威猛的小伙子,一起谋事可能有点笨,但做一个保镖还是能胜任的。M局长肯定是派了这个离他最近的人来帮忙。
当邦德看到这个人的衣服和一般的表现后,这些东西都涌进他的脑中。现在他对他说到:
“见到你很高兴,怎么来的?”
“昨天夜晚,我收到M局长的密电。当时可把我吓了一跳。”
这个人口音奇特得很。像什么地方的人呢?既夹杂着爱尔兰土音,还带点别的腔调。邦德一时难以判断。也许他长期在海外工作,一直讲外语而形成这种语调吧。他说起话来总爱称兄道弟,使人很难受。
“那是肯定的,”邦德表示同情,“上面都说些什么?”
“局长让我今天上午搭东方快车,在二等车厢里与一男一女接头。他大致介绍了你们的外貌特征,要求我护送你们到巴黎。就这些了,老兄。”
他的话里有没有破绽?邦德看了他一下,正好撞上他跳动着血红火苗的眼睛,就好像烧得通红的熔炉打开了安全门一样。但红光迅速熄灭了,通往这个男人内心的门迅速关上了。他的目光又迟钝起来。只有极其内向的人才会有这种眼神。它们不是用来观察世界的,而是用来审视自己内心的。
邦德感觉非常奇怪,心想:这个大个子神经不大对头,莫不是有炮弹炸伤的后遗症?要不就是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可怜的家伙,身体倒是健壮得像头牛,但总有一天回跨下来的。应该及早治疗啊。回伦敦后得跟人事处的人讲一下,查查他的病历。对了,还没问他的名字呢。
“噢,很高兴能和你一起工作。可能现在没什么事情让你做。我们刚上车时,有三个俄国人盯稍,但现在已经甩掉了。车上也许还有他们的人,他们也可能再派人来。我得把这姑娘安全地送到伦敦。今天晚上我们最好在一起,轮流值班。这是最后一个晚上了,我不想再出什么意外。对了,我叫詹姆斯·邦德,护照上的名字是戴维·萨默塞特;那个姑娘叫凯罗琳·萨圣塞特。”
那个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皮夹子,里面好像有很多钱。他从中抽出一张名片递给邦德。名片中间印着“诺曼·纳什上尉”的字样,左下方印着“皇家汽车俱乐部”。
当邦德把名片放进上衣口袋时,他的手指在名片上划了一下,发现名片上的字是雕上去的。“谢谢,”邦德说,“好了,纳什上尉,进屋见一见萨默塞特太太吧。这次旅行,我们没有理由不住在一起的。”他微笑着鼓励道。
令人不安的红火又在纳什眼中一闪而过。嘴唇在金色的胡子下抖了抖:“很高兴见到你,老兄。”
邦德转过身,轻轻地敲了一下门,“我是邦德,开门吧。”
门打开了。邦德让纳什先进去,自己随后跟了进去,随手带上了门。
塔吉妮娜吃惊地望着进来的陌生人。
“这位是纳什上尉,诺曼·纳什,是专门派来保护我们的。”
“您好。”塔吉妮娜犹豫地伸出手。纳什轻轻握了握手,一声不吭地盯着塔吉妮娜。塔吉妮娜很不自然地笑了笑说:“请坐吧。”
“呃,多谢。”纳什硬邦邦地坐在窗子旁的凳子上,他好像记起了什么事——当一个人没话说的时候要做的事。他摸索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说:“请抽烟,请抽烟。”说着,他自豪地用十分干净的大拇指的指甲打开烟盒,去掉包在外面的银纸,露出了香烟。塔吉妮娜拿了一根,纳什马上将打火机凑了过去,谄媚得就像兜售发动机的推销员,替她把烟点上。
纳什看了看邦德,邦德此刻斜靠在门边,不知怎么帮助这位窘态十足的笨蛋。纳什又转身把香烟和打火机递给邦德,那神情就像在给国家元首端了一杯水一样:“你也抽一支吧,老兄?请!”
“谢谢。”邦德说道。他最烦弗吉尼亚烟草。但为了不使纳什尴尬,只得抽上一支。他真想不通,怎么情报局现在会用这种笨手笨脚的人。靠这种人,怎么能在的里雅斯特打开外交局面,结交各方人士,更不用谈从事情报工作了。
邦德找着话说:“你看上去像个打网球的?”
“不,我游泳。”
“一直呆在的里雅斯特吗?”
听到这话,纳什的眼睛里又窜动了火苗:“有三个年头了。”
“喜欢这种工作吗?”
“有时就是这样。这你清楚,老兄。”
邦德讨厌他这样称呼自己,一直在想怎么阻止他这样做,但又不知怎么才能让他不这样。屋里顿时又冷场了。
纳什觉得该自己打破这种僵局了。他伸手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张简报,递给邦德:“看看这条新闻,老兄?”火苗又在眼睛中闪过。
那张报纸纸张粗糙,印刷质量低劣,而且油墨未干。上面有一条醒目的大标题:
惊人的恐怖行动
苏联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被炸
邦德只能大概猜出标题的意思,下面文章就看不懂了。他折起简报,还给了纳什。这个人知道多少内情呢?最好暂时把他当作强壮的保镖,用不着和他费口舌。“太糟了,”邦德说,“大概是煤气管爆炸吧?”此时,邦德眼前又出现了开关设在克里姆办公桌抽屉里的地道凹室里那枚吊着的大炸弹。昨天下午特雷波打过电话后,克里姆的儿子们肯定一个个都怒不可遏,争着要为父报仇血债。是谁去按下了那个按钮呢?老大?也许他们用抽签的方式决定怎样来报仇,由谁来执行。他们肯定挤在那间办公室里,看着他们其中一位按下按钮,然后听到运方传来轰隆的爆炸声。他们一定会为父亲的惨死而嚎啕大哭。那些老鼠怎么样了呢?也一起完蛋了吗?什么时候爆炸的?四点钟的时候那帮苏联人是不是还在开例会呢?那幢楼中当时有多少人?塔吉妮娜的那些朋友总算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这件事现在不能跟她讲。克里姆在看吗?他是否通过瓦尔哈拉殿堂(北欧神话主神兼死亡之神奥丁接待英灵的殿堂)的窗口欣赏到炸弹爆炸时的宏伟景观了呢?邦德仿佛听到了从天上传来他胜利的狂笑声。无论如何,总算有人替克里姆出了口气。
纳什看了看邦德,显得大失所望,说:“我也这么认为。”
过道中传来了一阵铃声,“开饭了。请各位到餐车上用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