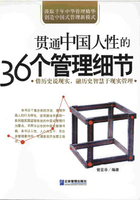我与凌默,断了就是断了,何必再费心经营。
这些年,我一直在想,我与他在一起,总感觉某个地方出了问题,是他付出的不够吗?可我心里清楚,只要我张口,他会愿意为我放弃一切,那日在皇后的寿宴上,他不顾众人的目光追了出来,我心里不是没有感动。
后来,我渐渐想通了,是屈辱。
他总能给我带来屈辱感。
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对我来说,屈辱感如影随形,从未消失过。
初次见他,他先是赞美我一番,待我信以为真后又狠狠浇了一盆冷水,让我明白,他瞩目的是冷秋,我当然不会记恨,但屈辱自那时就开始了。
姐姐入宫不久,他便来找我,他明知道所有人都会认为我鸠占鹊巢,抢走了冷秋的东西,可他还是决定娶我。他是我暗恋多时的人,我来不及多想便匆匆嫁给了他,内心的呐喊就这样被蜻蜓点水般一笔带过。
他和冷秋一起算计我,任我被人蹂躏,他用族人的性命要挟我入宫,他在我最狼狈的时刻告诉我他爱我,我偷偷摸摸地怀上了他的孩子,我和他在宫中屡次私会,一件接着一件事,我心中的屈辱感有增无减。
我甚至不敢承认我爱着他。
八年了,与他在一起做的事大多是见不得光的,屈辱像是蚂蚁,慢慢啃噬空了我的心,消磨的我的热情,我的心还在凌默那里,可是只剩一副空壳了。
我们在一起一直是两厢情愿的事,我没有资格去责怪他,没有我的坚持,他不会最终舍弃冷秋选择我,没有他的青睐,我也没有屹立于皇宫的勇气,你侬我侬,郎情妾意,如是而已。与他分开,谈不上是变了心,移了情,只能怪没有缘分。说来可笑,缘分二字最虚无不过,古往今来,未能修成正果的恋人却都要埋怨缘分,似乎一句缘分不到便可化解一切遗憾。说到底,还是人犯了错,毁了两人的前程,只不过那错是无心之失,毕竟谁都没有能力预见未来,害怕自己自责地太厉害,一句缘分不到便搪塞过去,明知是掩耳盗铃,心中多多少少还是能宽慰些的。
如我与凌默,若他不帮助冷秋,我至今仍是三王妃,若我不吸引皇上的注意,想必会一直做着女史,也不会有后来的擦肩而过。凡此种种,想起只会徒增悲伤,不如装作糊涂,一切都算在缘分的头上。
不知不觉,茯苓也已经快十八岁了,我看着她由一个未留头的小丫头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心中不无欢喜。几年前,贤妃用她威胁我的事她一直被蒙在鼓里,只当是贤妃善心大发才放了我,冰晴的死她也毫不知情,只当是暴毙。我很庆幸那时刚满十四岁的她对丑恶的事实一无所知,她和当年的我一样,都是活泼爱闹的性子,倘若她也开始郁郁寡欢,我会产生一种错觉:上官冷月又死了一回。
我和织锦性子都偏静,我经历了种种波折终于悟出沉默是最安全的生存方式,而织锦却是天生性子沉稳,话一向是极少的,苏升好动,终究是个小太监,茯苓便成了紫湘阁的一抹阳光,有她在,还些许有些生机。
冰晴死后,我的脾气变得极坏,织锦问话,我常常是不答的,可对茯苓却是个例外。
记得有一晚,我赤着脚站在院子中,对着空气,和冰晴说了一夜的话,已经立了秋,我身上只穿了一件薄薄的棉裙,加上连日来不吃不喝,终于支撑不住晕倒了。醒来后便开始发烧,织锦千辛万苦找来的药我连碰也不碰,禁不住她的劝,我刚喝一口便迅速吐了出来。
“小主,你这是把自己往死里糟蹋。”
我闭上眼睛,揉着隐隐作痛的太阳穴,不理会她。
“小主,奴婢说句不中听的话,冰晴妹妹看见你现在这样,恐怕心里不会痛快。”
“她去找皇后时也没有想过我会不会不痛快。”我赌气道。
正当这时,茯苓伏在我耳边,怯怯地说道,“月姐姐,你是怕苦吗?苏升会做白糖糕,吃些白糖糕再吃药,就没那么苦了。”
那是她第一次叫我“月姐姐”。
我缓缓睁开眼睛,看到她水汪汪的眼睛,心里微微一动。
勉强一笑,“才没有那么娇气。”说着端过药碗一饮而尽,织锦的眼中闪烁着委屈,难怪她了,她好劝歹劝,苦口婆心,我不为所动,茯苓一句孩子般的玩笑话却起了作用,正常人都会认为我在针对她。
我没有。只是看到茯苓,就会想起我自己。
没有人愿意让自己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