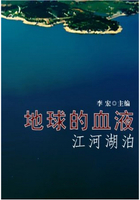冷秋见大势已去,疯狂地扑了上来,“冯瑶,你怎么能这样背信弃义,是我告诉你她怀了龙裔的,若不是我,恐怕直到这孩子生下来你都不会知道。你真是下作的小人!”
看来她还没有完全失去理智,我本担心她为了自保口不择言,将孩子不是龙种的事实和盘托出,还好她没有愚蠢到那个地步。
“来人哪。”冯贵妃只是轻轻一声召唤,紧闭的门突然被撞开,十几名侍卫冲了进来,将冷秋拉开,冷秋不停地挣扎着,发髻散开了,簪子“叮”地一声掉落在地面上,瀑布般的乌发遮住了她苍白的脸颊,嘴里犹在咒骂着,“冯瑶,你不得好死。”
冯贵妃烦躁地提高了嗓音,“拉下去!”
看着冷秋被连推带搡地押了下去,瘦削的肩膀又窄又平,像是一个纯真的小孩子,我已经痛到麻木的心再次剧烈地收缩起来。
“不,不要这样!姐姐!姐姐!”我不知哪里来的力气,甩开了常欢、常聚,“放开她,放开!”我追了上去。
押着她的侍卫停下了脚步,我走上前去,冷秋却回过头,憎恶地瞪了我一眼。只消一眼,我便停下了动作。
原来,原来,对她来说,我的隐忍眷恋对她来说毫无价值,姐姐,我们终究还是因为凌默而闹翻了,我们多年的情义终究还是因为凌默而烟消云散。
这样的结局一开始就是注定的,从遇见凌默的那一刻起就定了格,再也不容更改,可惜当局者迷,我们身在其中,缘来缘去,看不真切,只知顺着自己的心意拼命挣扎,到头来,我们所做的努力只是使我们越陷越深,再也没有得救的可能。
姐姐,我们是如此相像,一样的近乎偏执的倔强,一样的对于同一个人的痴迷,可是我们都清楚地了解,相像从不意味着亲近与友爱。从小我们就处于一种奇怪的关系中,一方面我们形影不离,另一方面,我们无时无刻不处在一种奇异的竞争的关系中,琴棋书画,你的天赋都高于我,母亲带我们一同出门,被称赞的永远是你,你比我乖巧许多,我虽然活泼,那活泼中却总带着一股戾气,让人亲近不得。那么多年,你一直都是赢的那一个,父母对你有所偏爱也是理所应当,我早已失掉了争的想法。
是的,我永远是输的那一个,所以我习惯了退让,习惯了去衬托你,因为与那些光环荣耀相比,你重要得多。后来,我终于赢了一次,我怀上了凌默的孩子,你却永远都没有这样的机会,仅仅一次,却让你下这般毒手,他是你的外甥啊,他还那么小,你怎么忍心,怎么忍心。
我知道,你爱他不比我少,可他毕竟从来没有算计过你,若不是你硬是拖我下水,他心中或许直到现在最爱的人,仍然是你。你认为是我抢走了他,事实上,是你糟蹋了他的真心,他与你一同算计我的时候大概对你的心就渐渐冷了下去,他像是个被欺骗的丈夫一样,发现自己的娇妻原来可以这样阴狠,连一同长大的妹妹都可以出卖。他可以忍受你蒙尘的身体,却忍受不了你蒙尘的心。
姐姐,你的怨,你的不甘,我都理解,但我不能原谅。我可以忘记你为了一己私欲而毁了我的大好前程,但不能容忍你杀死了我腹中的生命,我可以原谅你打乱我的世界,但不能任由你夺去我最后一丝希望。从你找上冯贵妃那一刻起,结局便注定只有两种: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我们是姐妹,却只能自相残杀我一个不稳,几乎摔倒在地。冯贵妃连忙上前搀住我,“常欢,立刻去请太医。常聚,立刻去养荣殿,通知刘总管,冷月女史小产,晕倒在本宫门前,昏迷中不停地叫着皇上。”
“那这里……”常欢问道。
“叫绣蕊、绣菲来,让她们把女史扶进卧房。”
“是。”
后来的事我记不清了,只记得迷迷糊糊地被扶了进去,我躺在一片柔软的云上,沉沉地昏睡了过去,好像一生没有睡过一样累,眼睛一刻都不愿睁开,任由自己陷入黑暗中。可下身却火辣辣地疼,好像被架在烈火上灼烤一样,那疼痛时而出现,时而隐没,我也且睡且醒,睡的时候并不踏实,胸口好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喘不过气来,被痛醒的时候,仍摆脱不了梦魇的笼罩,那痛尖锐而切骨,不留一点缓冲的余地,我忍不住张开嘴想要哭喊,可那哭喊到了嘴边变成了低低的嗫嚅。
朦朦胧胧中,我感到一只冰冷的手放在我的头上,我微微地安下心,听到一个低沉的声音,“悠悠,你老实告诉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悠悠,这个名字好熟悉,一定曾经听过,可我太累了,再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去想何时听过这个名字。
“臣妾知道的也不是十分真切,听侍卫说……”
声音逐渐小了下去,我仔细地听,却一无所获。
我下意识地想,我在沉睡,可这后宫的人却一刻都不消停,一场戏落了幕,另一场立刻接了上去,究竟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