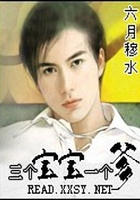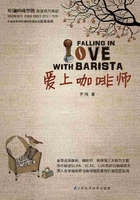贾政站在远处房荫下,来回踱步唉声叹气。
贾赦听完一出戏,见久不开席,心中恼火,问了几次都说东府太爷还没出来。他等得不奈烦,带着手下小厮直接砸了贾敬的房门。
贾敬头发挽在顶上,一身灰布道袍,手持扶尘闭着眼打坐。
贾赦一瞧心中好恼,指着贾敬说道:“大哥,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出家清修,一大家子的事扔给了珍哥。你不当他是你儿子也就罢了,还能不上他认你做爹吗?一年就一次生日,请你家去,你怕染了世俗。一家子费心费力到城外给你过寿,你又横挑鼻子坚挑眼,让他们爷们在太阳底下跪一个时辰了,不心疼儿子,你也不看看你孙子吗?”
贾珍跪得笔挺直,汗珠子顺着脸往下淌,衣服湿答答地贴在前心后背上。贾蓉也没好到哪儿去,这公子哥一年受一次这样的折磨早就习惯了。
贾敬瘦削的脸白里泛黄,眼睛深深地嵌在眼框里,两腮也向内塌着,手持扶尘甩在肩后。缓缓睁开眼睛:“蓉儿起来。”
“是。”贾蓉答应一声,本想起身,看了一眼身旁还在跪着的贾珍,他欠了欠身也没动。“老太爷,孙儿陪着爹爹跪着。”
“唉!珍儿也起来。”
贾蓉这才打在晃携着贾珍起身。
“这就对了,一家子骨肉,非闹得这么着?走,吃酒看戏去。”贾赦见贾敬卖了他面子,心中大喜,伸手以上扯贾敬。
贾敬一甩袍袖,对贾蓉说道:“蓉儿,侍候你两位叔公去吃酒看戏。我还事吩咐你爹。”贾敬看着贾蓉眼里才有了点温度。
“这?”贾蓉用眼神询问贾珍,贾珍轻轻点头。
贾赦早就在此等得心里长了草,贾政也是浑身燥热,渴得喉咙冒了烟,便趁此机会随贾蓉去了。
待贾府爷们走远,贾敬才低吼一声:“跪下!”
贾珍身子一得瑟,腿一软跪在了地上,心里咚咚直打鼓,垂着眼不敢看贾敬。他忐忑不安地琢磨着莫不是那事被老爷知道了。
“你干的好事。”贾敬起身,背着手踹了贾珍一脚。
“老爷,珍儿做错什么了惹您生这么大的气,实在是该死。”
“你是该死,没人伦的畜生,金枝玉叶你也敢染指?当初我是怎么和你说的。”贾敬鼻翼微张喘着粗气。
贾珍脑袋“嗡”了一声,怕什么来什么,不知哪个王八羔子把这事传到观里来了。他跪爬半步抱住贾敬的腿,“老爷息怒,孩儿对她是实心实意,从没敢存亵渎之心。”
“放屁,那是你儿媳妇。”贾敬怒不可竭,气得眼珠子冒火,恨不能将儿子吃了。
“老爷,蓉儿和她从没圆过房。当初,当初若不是您一意孤行,她该是您的儿媳妇才是。”贾珍眼中含泪带着满腔的幽怨说道。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让金枝玉叶给你做填房?你也配。”贾敬气得脸红脖子粗,手背上的青筋跳起多高。
“老爷,低声些。”贾珍抹了把额头上的汗回头看看敞开的大门,警惕地提醒着。忽然贾珍眼前闪过一道灰影。“什么人?”他脱口喊出声来。
“啊?”贾敬也吓得大惊失色。火气冲昏了头脑,竟然忘了避人了,想到此贾敬平地蹿起多高一把薅住一个十五六岁的小道童。
贾珍也奔出门外,紧张不安地盯着道童。“小兔崽子居然敢偷听爷们说话,想是不要命了。”贾珍蹿到眼前,抽出鞭中短刀就想结果那道童性命。
道童当即吓得变了颜色,嘴巴张得老大却没发出任何声音。
“慢着,他又聋又哑随他去吧。”待贾敬看清道童模样,抓住贾珍手腕,踹了道童一脚放他离去。
“老爷,他瞧着眼生,何时入观的?”贾珍看着小道童的背影问道。
“来了几个月了,当初差点同饿死,观主捡他回来让他扫扫院子。不妨事。”经此一闹,贾敬平复了心情。
贾珍关了房门,扶贾敬坐回莲台。
贾敬长叹一声,“事到如今,你打算怎么办?”
“老爷,珍儿已经想明白了,人生在世总得有点盼头,与她在一起就是我最大的盼头。我愿意把这爵位给蓉儿袭了,我带着她隐姓埋名退居山野。请老爷成全。”贾珍再次撩袍跪下,他生于富贵锦秀之地。吃、喝、玩、乐之事无所不精通,他也从没觉着这样过有什么不好。直到她一天天长大,成了他的世界里开得最娇艳的花儿。她在他心里的份量渐渐加重,重到足以让他放弃眼前的荣华。哪怕是粗茶淡饭,粗布裹身唯愿与她携手天涯。
“唉!孽情,孽情。”贾敬摇头叹息。“趁此事没完全败露,你带她走得远远的。”
“谢老爷成全。”贾珍欣喜基狂,此一去名正言顺,他和她都不用再背负伦理的枷锁。
“你走之前把惜春的事安排妥当,给她找个好人家,无需王府公侯,只要人家殷实,男孩清秀肯读书就好。”
“老爷放心。”贾珍答应着。
爷俩个又说了一会话儿,贾敬只在贾府家宴上露了一面,就退回丹房静修去。贾赦领着贾府子侄纵情玩乐,丝毫不避讳场所。
当晚,贾母住在道观。
宝玉下学之后,带着小厮们也到了道观。张真人始提宝玉亲事,宝玉大动肝火,扬言再不见这牛鼻子老道。贾母也以宝玉防需晚娶为由回了张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