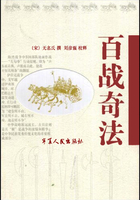慕容吟风出去已经有些时候了,可弋鸿宣迟迟未进来,若然只听得凌怀亦不善的声音:“我家夫人不舒服,你知道大夫说她需要静休的!”
“怀亦!”若然只得高声喊了一声,却一口气提不上来,又猛咳起来。
“夫人!”凌怀亦闻得若然咳嗽,便也不去管弋鸿宣,急忙进帐伺候。
就这样,弋鸿宣亦随着他进帐,静静看着凌怀亦给若然斟茶、递水,沉默半天后,他终于轻声开口打破了室中近乎窒息的寂静:“你倒好,总有那么多人关心。先是花名在外的萧大公子,接着又是新科状元,再是弋阳首富的公子,还有……还有这位大管家。”
尽管内容有些刺耳,可闲闲淡淡的语气,却叫人听不出其中的冷暖。
若然闻言苦笑一声,微微叹息道:“这种刻薄的话不适合你。”
弋鸿宣嗤笑几声,冷冷道:“你倒适合这种复杂的关系?”说罢他指了指若然和凌怀亦此时看似过于亲密的姿势。
“你说什么?”若然先是没反应过来,明了后心中随即一阵怒火,“我的事不要你来管!”
无颜耸耸肩,微微挑了眉,不屑道:“我只是提醒某些人,自家主子的女人本分对待就是,切莫动了歪念——有些女人是动不得的。”
“你说我便是了。他又于你何干?”若然的声音不由得高起来,瞪眼望着立在床边的男子,身子因为动怒又是了阵猛咳。
弋鸿宣竟弯唇笑了,潋滟的眸间光芒闪动。这样奇特的眼神,直让人看不出此刻的他到底是得意还是幸灾乐祸:“我可是领教过你的厉害的。”
知弋鸿宣讲的是自己在鸿宣府中对他的“勾引”,若然泄气地低了头,心中既发酸又恨恨道:“怀亦是君涵派来照顾我的,他只是尽职地做好了本分,你且打住那肮脏的心思吧!”
“也不尽然,或许他真的是太关心在意你了。这次的任务,他完成得够卖命!”弋鸿宣突然打断若然的话,话中带笑,笑中更有话。
若然半敛了眼眸,笑得有些无奈,看来凌怀亦在自己昏迷期间可能对弋鸿宣做过或是说过些什么,才这让落了人家话柄。
见若然不语,凌怀亦以为她生气了,讪讪地道:“夫……夫人,你莫听他胡说。我……我只是见不得他趁老爷不在夫人身边,总找机会有意无意地接近夫人!刚才你……你病着的时候……”
弋鸿宣和若然都没想到凌怀亦会说出这等理由来,不由地都愣在那里。弋鸿宣更是有些尴尬,沉吟一会后,眸间忽地一冷,他低头直视着若然的眼睛,口气变得有些僵硬:“我想和你单独谈谈。”
若然抿唇点头,转头朝凌怀亦道:“你下去吧,我有分寸的。”
闻言,凌怀亦恨恨地瞪了一眼弋鸿宣,无奈地转身离去了。只是他虽离去,可弋鸿宣却没有发话,只是伫在那里,望着方才被若然绞皱的床单,痴痴的。
若然不得不率先开口道:“说吧,你想单独和我谈什么?”特意加重了“单独”两字。
弋鸿宣这才回过神来,冲若然傻笑,有些语无伦次地道:“大家正在庆功宴上喝得起劲,少了你这个大功臣,怎么行呢?”
“我?”若然记得刚才明明说是弋鸿宣派人拦下了要来邀请自己的人,现在他的这番话还真是与刚才弋晟宣他们讲的出入重大呢。
“是啊,你可让那些士兵好找!”弋鸿宣讪讪地答道。
“这死结打的可真丑。”若然皱皱眉,实在不知道弋鸿宣想表达什么,便干脆另寻了一个话题。
本来就很勉强的笑容顿僵,闻言后的弋鸿宣的表情还真是有点好笑。
若然将那条本来放在额头的丝绢抛向空中,乐得开怀大笑,她总算在弋鸿宣面前扳回一局。其实虽然听了凌怀亦的话她便猜测这丝绢极有可能是弋鸿宣放在自己头上的,只是不敢十分确定,但她一诈他,从他难堪的表情就能知道自己的猜测不错。
弋鸿宣没奈何地叹气,轻轻捡起被若然抛落于地的丝绢,语中带笑道:“还不是某人不老实,睡着了也不安生,一刻不停地挠着脑袋。”
“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有些受不了弋鸿宣宠溺的话语,若然回归正题道。
弋鸿宣却不不说话,只看着若然。
“是不是来跟我道别的?”若然垂眸浅笑,声音幽幽的,说不出是心中感伤,还是因为想到今后还有更艰巨的仗要打。
“你知道了?”他低眸瞅着若然,凤眸间颜色流转,光华浅浅,离情深深。
“嗯!”若然重重地点了点头,却更似在给自己一个决断。
瞥到若然床里边的竹简,似想到什么,弋鸿宣了然地笑笑:“也对,即使我不说,你也应该从他的来信中知道朝中情况有变了。”
若然侧身望了望从被子下露出一角的竹简,顺手将它抽出递于弋鸿宣道:“你看看他讲的可是变况的全部?”
弋鸿宣抿唇而笑,目光微微一动,难辨的诡谲突然浮现:“就这样让我看你们夫妻间的悄悄话?”
若然微怔后才反应过来弋鸿宣指的是什么,笑道:“平平淡淡才是真,如果你想在竹简中看到我们夫妻间的甜言蜜语,那恐怕是要你失望了。”
弋鸿宣不再言语,却以极快的速度看完了凌君涵的来信,思索片刻才道:“还有就是庄妃下令逮捕所有与太子有关的人,除了凌家,太子所有的丈人都牵涉入狱,包括南宫敬德。”
若然思索一下,知凌君涵是担心自己会辜念南宫敬德的养育之恩而做出什么不智之举才向自己隐瞒的,心中倒是暖暖的,笑意也更深。
“他倒还真会替你想。”弋鸿宣勾唇笑开,眸色潋滟动人,让人看不出有什么情绪,“不过也真为难他要日日伺候庄妃这个老女人了。”
“他还不是在替你卖命?”若然怪瞋地望了弋鸿宣一眼。
弋鸿宣轻轻叹气,轻道:“若是帮我又何苦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呢?委屈了自己的心志。”
“什么代价?”若然听不得真切,心中更是困惑。
“没什么。”弋鸿宣挑挑眉毛,摇摇头,一脸不在意的样子倒让人觉得他方才真的没讲什么。
若然也没问下去,只是道:“他在朝中替你卖命,我又在军营听你使唤,还当真是夫唱妇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弋鸿宣弯唇浅笑,一脸从容,只是眼角略显苦涩。
“南宫敬德应该很快就会被放出来吧?”若然示意弋鸿宣坐下,一直仰头望着他让脖子有些酸痛。
“你怎么知道?”弋鸿宣本来微锁了似画点缀的双眉,骤冷的眸底掠过一丝惊奇。
若然撇撇唇,尽量说得轻巧无谓:“北朔都囤兵到你家门口了,可你自家后院的火还没息,没有南宫敬德,你拿什么去对付那匹来自北方的狼!”
弋鸿宣的脸色显然有些隐隐的不安,他侧过脸,垂了眸,清了清嗓子,方慢慢道:“虽然我料到北朔会趁我们内之际来袭,可我没想到他们的消息这么灵通,动作又如此之快,让我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
“不对。”若然笑了笑,回眸抬眼看了看弋鸿宣,语气认真地纠正他,“你早就料定了一切,并且一切都掌控在你手中,对不对?”既然弋鸿宣能在太子刚反时,便通知自己一定要拦住南宫敬德出兵,那应该是早就料到各中的变化,留住南宫敬德是为了对付北朔之用。
“一切?掌控?”弋鸿宣有些诧异,也不由得仔细瞄了几眼若然,凝眸时,他的眉宇间阴晴变幻不定。看了半天后,他终于有了结论,倜傥的笑颜浮上面庞,淡然道:“你果然没有完全与凌君涵连成一气。”
说这话时,他不由自主地伸指摸了模自己的脸颊。修长的手指触上眉梢的刹那,那笑容开始自得,神色也慢慢转为自恋的倾向。
若然白了他一眼,没好气地道:“既然我之前已答应与你合作,我自然懂得行规。你可别有某些不应该有的心思。”
弋鸿宣也不反驳,哼哼一声,舒展的眉又皱在一起。
“南宫敬德手上有多少兵力,能对付北朔的八万人马吗?”若然突地想到一个重要问题,扬眉看向无颜时,一脸的担忧。
弋鸿宣摇摇头,眉皱得更深:“不足五万。”
若然愣了愣,哑声笑叹:“看来又将是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
“是不足五万的老弱残兵。”弋鸿宣答话时眸光渐迷离,似在思考某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留下南宫敬德只是做个样子给人看看,朝中兵力本来就不多,多数兵力掌握在边防的异姓或是同姓王爷手上,现在他们不是反了,就是坐山观虎斗……而且北朔的动作又是那么迅猛……”弋鸿宣低声一叹后,声音越说越轻,直至几不可闻。
若然睇眼看着无他,缄默中,目光幽深似潭。“那该……该怎么办?”若然小心翼翼地问出口,现在是先对外还是先对内的问题。
弋鸿宣漠然一笑,睨眸望着若然,一语不发。隐隐绰绰的月光透过大开的窗扇射上他的脸,照亮了他清寂的目光,似雪的容颜。
“你不相信我了?”他勾了唇,语中带着难得的柔缓,却听得若然一个寒噤。
知道弋鸿宣听出了自己对他能力的怀疑,若然咬了唇,转眸想了又想,方轻声笑道:“现在我一点都不怀疑。”
弋鸿宣冷冷一笑,别过头去,不做声。
斜眸偷偷瞟了瞟弋鸿宣不善的脸色,若然心知刚才是自己触犯了他的自信和尊严,忍不住伸指扯了扯他的衣袖,讨好、歉意地朝他笑笑。
弋鸿宣横了若然一眼,眸间依然有似针寒芒:“依你之意,我该怎么办?”
听他软下来的语气,若然亦放下心来,起身从塌旁走至桌边,自斟自饮起来。冰凉的茶水沉入肺腑时,若然才猛然记起今夜一件自己糊涂到现在都没有去关心的事:“大将军府的其他人呢?也一同关入大牢了吗?”
弋鸿宣挑挑眉,若无其事的表情:“象征性地总该关关的。”
“庄妃怎么会傻到在这个时候关南宫敬德?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好。”若然心中虽不信,可事实摆在眼前由不得她不信。
“是南宫敬德主动请求入狱的,可能是锦衣玉食的生活过惯了,想换个环境吧。”此时的弋鸿宣脸上寒色不见,容颜间早已恢复了平日的悠然恣意。只是他的语气实在是呕死人了,讲得似是南宫敬德十分犯贱。
“真的是他主动要求的?”若然犹在迟疑。
弋鸿宣弯唇一笑,展颜间媚惑无穷:“是。心甘情愿,毫不反抗!”
若然不可思议地望着他,无语。
“朝中多人都替他求情,可他就是铁了心那么办。”弋鸿宣再一次强调自己无辜,凤眸里带着比水还要清的澄澈。
若然不耐烦地瞧他一眼,挥挥手道:“知道了,知道了!”但转念一想,又觉不对:“他有必要这样来保护自己的实力吗?”
“是,完全没有必要。不过你想得到他这样做的目的吗?”弋鸿宣侧眸看着若然,古怪的笑容下隐藏玩味和戏谑。
若然再也懒得看他,找了位子坐下,淡淡道:“有什么想不到的,不就是为了抬高他的身价?”
弋鸿宣眸子一亮,赞赏性地道:“为难你能看出来。”
若然也懒得与他的轻蔑计较,撇撇嘴,什么也不说——南宫敬德肯定是想到北朔多半会趁此机会来扰,到时候定有用得上他的地方,再是有人将他从牢中请了去,又是一件不小的功劳,南宫氏的地位也就更牢靠一点。
是夜,是一夜的长谈。
趴在桌上眯了一会,没过多久天便亮了。若然伸指揉揉眼,转顾四周却也瞧不见弋鸿宣的身影。走出大帐,阳光不赖,大营恢复了日前的热闹,人人脸上漾起的笑意温暖得让人觉得昨夜的恶战和生死较量的凶狠到此刻竟虚幻得像是梦中的泡沫。若不是昨晚弋鸿宣最后那凝重的表情深深刻入了若然心中,她还真会以为治国、打仗是件简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