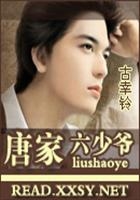弋鸿宣猜得没错,太子虽有三位盟友,可他们心思各异。这不,弋东王这厢被弋晟宣打得七零八落,那厢肃宁王的铁骑却并未直奔开原救急。他反全命麾下提前绕去弋晟宣大军之后的五万兵马对敌的数量不但略多,还占尽了把守关卡的地势之宜,以五万之势摆十万锱兵之重的壁垒,牵制京畿军的后方兵力,迫弋晟宣的铁骑绕道西北,自峡谷驰往岢岚里谷。
若说弋鸿宣上次让剑心去对付笑阳并无特别的必要,那他这次要剑心再出岢岚里谷遏止军笑阳所部向弋晟宣大营的逼近恐怕是迫不得已了。即使京畿军漂亮地解决隆尧王和弋东王,可毕竟他们的兵力无法与太子和肃宁王相比,因此肃宁王一出马,弋晟宣就有些束手无策了。
“军师还未想出对敌之策吗?”大帐内少了剑心,弋晟宣正望着地形图绞尽脑汁,若然坐在一旁摆弄着酒杯,弋鸿宣刚从大帐外回来,看来是行了不少的路,外面严热的天气烤得他白晰的脸宠微红,却更有男子气概。
若然瞥了一眼弋鸿宣,却并未做出回答。
“三哥,你去亲点一下军中粮草还够维持多久?也好早作打算。”清点粮草这种粗重活哪用弋晟宣一个堂堂统帅去做,弋鸿宣这么说也无非是为了暂时支开他罢了。
“有什么要说,就赶快说吧!我还要想对敌之策呢!”若然明白弋鸿宣的意图,待弋晟宣离开后,便也开门见山地对弋鸿宣道。
弋鸿宣无所谓地笑了笑:“肃宁王的军队长途跋涉至此,他们不急,我又何需急?”
见弋鸿宣一副事不干己的样子,想到弋晟宣、剑心和自己这样为他卖命,在心中大叫不值,却又敢怒而不敢言,只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见若然这副架势,弋鸿宣倒只是微微笑了笑,道:“你若真是担心南宫剑心以及她腹的孩子,那便早点说出退敌之策啊!我也可以安排她尽早归来,毕竟南宫笑阳是何等厉害的角色,又岂是她可对付得了的?”
“哼!南宫剑心?我凭什么担心她?况且——我根本没有退敌之策!”若然刻意冷淡的语气,不知道弋鸿宣有没有听出来。
“哦?是吗?”对于若然诡辩,弋鸿宣却是一脸诡异的笑容,送袖中抽出一张纸,在若然面前晃了晃,道:“那这又是什么?”
虽只是轻轻一瞥,可若然可以肯定他手中的自己踌躇该不该交出去很久的作战计划,却想不到弋鸿宣不请自取,心中顿时不悦,道:“你……翻察我的东西?还给我!”其实面对这种地形,若然早就想出了一条妙计,只是这计谋过于狠毒,她虽非善类,却也从未杀过人,亦不想自己的小小计策就让许多将士因此丧了命,故而一直犹豫该不该拿出来。
“啧啧啧……这么好的计策你为什么没早拿出来呢?”弋鸿宣一副很可惜的样子。
“这不是我想的!”若然撇过头去,不承认,亦不想背负起那么多条人命。
“隆尧和他手下的那么多将士是死在你手上的吧?”弋鸿宣冷不丁地问道,“杀一个与杀千百个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你……”若然很生气,却又想不出什么话去反驳弋鸿宣,因为他说的一点都没错,她的手上早已沾满了无辜士兵的鲜血。
“我方才已派人下去按你的意思布防了,听祈枫说下面的将士真说军师好智谋……”弋鸿宣倒是还有心情调笑,却让若然的负罪感越来越重。
八月十四日,京畿军回师北上,弋晟宣所部与肃宁王在苛漳第一次正面交锋。人言肃宁王虽年过半百,却力能扛鼎,果然名不虚传,弋晟宣与他大战三百回合,正酣,却被一支冷箭命中,坠马落地,不醒人世。京畿军也不得不暂时撤回岢岚里谷,却中途被肃宁王早就埋伏着的一万士兵劫杀,大军一时群龙无首,京畿军参军暂命军队舍弃毫无障碍作保护的岢岚里谷,去深河暂避。
“不想亲自看看自己的布防如何困住敌人?”弋鸿宣丢给若然一副铠甲,“还是没这个胆量?”
“去就去。”若然明明知道他是在激自己,可还是打算去看看,去看看自己小小的一个决策到底可以伤及多少可怜的战士。
其实弋晟宣中箭坠马亦只是若然计划中的一部分,为的是诱敌深入。肃宁王行军半生,且为人谨慎,若然如果不花这等心思,还真难教他上当。
肃宁王亦是派出了三支侦察队,确定弋晟宣果真重伤难治,且已往深河暂避,他这才命令部下挺进岢岚里谷,希望能趁此机会夺下个兵家必争之地。
“此地两边树木茂密,如果他们假以火攻,恐怕……”肃宁王果然老谋深算,看到岢岚里谷树木繁茂,便已意识到了局面对自己非常不利,“命后军止步,撤出谷去!”
“不好,他们好像发觉了。”一旁不远处山头小心握着马缰的若然发现敌军开始回撤,知道他们定是识破了自己的计策,不觉大叫。马儿听得主人大叫,像是接受到了指命,顿时兴奋地颠起来。
“啊!”正当感觉要坠地时,不觉腰身一紧,瞬时飞了起来。感到周围有陌生男人的气息,若然不觉挣扎起来。
“别动。不想再掉下去,就安分点。”感到竟是弋鸿宣搂着自己的腰,而此时他们已稳稳地落在了他的马背上,若然放弃挣扎,一动不动。
“放心,他们现在才发现,已经晚了。”鸿宣感到怀里人已经安分下来,可也没有放她下来的意思,说话的语气倒像是成竹在胸。
“还不放开。”听弋鸿宣这么说,若然倒是稍稍松了一口气,却感到对方越搂越紧的力道,便不悦道。
“看——”忽略若然话语的内容,弋鸿宣指引她看向远方。
霎时,火箭如泄了闸的洪水,从山顶两面齐齐落下,敌军在峡谷里的锱重粮草顿时烧了起来。
山谷中火海一片,残叫一片。
若然显然从曾见过如此可怕的场面,双眉不禁拧成一团。
“别怕,这就是战争。”看着若然痛苦的表情,弋鸿宣的脸上亦闪过一些迟疑,却又连忙摇头甩掉了犹豫的心思。
“走吧,我想回去了。”疲惫的语气——虽然前世的自己不算好人,也若然也是秉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信条。可眼前的这些人,与自己无冤无仇,竟都间接地命丧于自己的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王爷,好像下雨了……”祈枫有些慌张地提醒只顾望着怀中女子的弋鸿宣。
“下雨?!”若然的语气亦由疑惑变向欣喜。
“真不走运,听本土的村民说,大雨要今晚子时才到。”弋鸿宣不为意地道,语气中似乎还点着一点点惋惜,“这雨可让军师的完美计策失色不少……”
若然来不及与他抖嘴,只见一处缓坡,坡下陈兵数千,银色盔甲件件湛芒,锋芒锐利寒人。弓箭手在前,弩弓其次,步兵在后。骑兵勒着马缰顿守两旁,蓄势而待发。如此严整的列队,一看就知道不是临时决定的,看来弋鸿宣早就知道这场“及时雨”,若然别有深意地望了一眼亦注视着战场的弋鸿宣,却没发现自己眼线已比过去柔和了很多。
京畿军左右两翼的兵力到现在不过两万,肃宁王有骑兵三万,方才在岢岚里谷被大火围攻的只是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却还只是运送粮草的杂务兵以及一部分骑兵,他们专注于对付这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大火,却不知弋晟宣带领的骑兵已从旁道绕来他们身后,势如雷霆迅猛,待肃军重整旗鼓时,五千玄甲骑兵已如五千利剑席卷而上,肃军欲反身对抗,但为时总晚了一步。
肃军步兵在后,京畿军铁骑上去,怒马踢人,剑锋横扫。步兵能退不能敌,弓弩手想要上前,却抵不住前方士兵似流水的后仰。两侧骑兵闻风支援,铁蹄踏尸,只是此刻他们也再顾不上马蹄下踩着的是本国的勇士和兄弟,只顾一路溅血,飞驰迎上。
“祈枫,看好她!”弋鸿宣朝祈枫一声喝,随手将若然放下马,扬鞭而去。只留握缰待命的祈枫和心绪不宁的若然。
弋晟宣的骑兵的突击有一定的成效。马近身千步,京畿军有千人同挽弓;马近身八百步,弓弦满起;马近身五百步,长箭离弦——马倒下,人难起;一尸隔立,绊倒数活人。京畿军呐喊着挥起了弯刀,拍马杀上前,短兵交戈。
战场终于蔓延至若然视觉、嗅觉可及处——血气扑鼻,喊杀声震天。
此时的若然管不了战场上那么多人,这战也不是她指挥的,她只顾搜索着弋鸿宣的身影,望着他的一举一动,一个手势,一个眼神。战场上的他不同往日任何时候的模样,凌厉,凶狠,决绝,果断,霸道压人的气焰让人仿佛一靠近就会被灼伤。
这样的他让若然想起了《动物世界》中的那些大草原上雄狮,若然的心思飘忽了一下。
似是感到注视的眼光,弋鸿宣回眸看了看朝若然所在的方向,匆匆一瞥,却又纵马离开,一抹墨色并不耀眼却似闪电划过,落入那翻涌不断似怒滔咆哮的千军万马中。
若然骇了一跳,竟有一种想冲入这战场的冲动,事实上她也这么做了,只是祈枫拉回来莫名其妙跑出几丈远的她。
利剑荡开如网织,密密麻麻,夺魂追命。墨衣夹在一群银白和灰暗的盔甲中又是夜色正沉,本并容易让人分辩出来,可就是有这么一个人能看着他一路疾驰,一手牢牢握住缰绳,但凭一只手也能斩杀无数敌军,飞洒的血液沾了他一身。浴血杀敌的他,眼神坚毅阴鸷,面色刚强冰凉,不似那个站在飘飘云端上风仪美曼、潇洒万端着俯视天下的神,而似来自地狱的嗜血修罗,能在血流浮橹间睥睨生死,从容,而又狠绝。
若然倒吸几口气,说不清是胆怯这样的他,还是越来越多倒在地上的尸体。
肃军倒下一拨又一拨,暗血在草原上汩汩流动,交缠着草根泥土,交缠着双方的魂魄,辨不清一场是非多错的战争,就这么,血液流逝,流逝,血腥渗透至骨骸,而若然闻着,心却僵硬着似早已麻木的无动于衷。隐隐的,唯有一声碎裂的叹息自胸中蔓延,浮上眼眸的刹那,怜悯悲哀中,却是深深的无奈。若然只顾暗自沉浸在自己的情绪中,丝毫未发现一道身影临近祈枫,小声禀报了什么事后又迅速离去。
待眼前局势稍稍缓解,弋鸿宣停下厮杀的脚步时,祈枫驰马靠近弋鸿宣,低声禀奏了几句话。弋鸿宣眸色一变,冷眸环绕四周战场后,出声命令:“即刻点两千兵马随我追去。”
祈枫惊声:“爷,那边可是三万的兵力,跟在南宫笑阳身边自西取道的可都是太子手下的精兵良将!”、
弋鸿宣冷然,定声重复:“我说点两千兵马。”
祈枫迟疑一下,正待开口再说时,抬眸望见弋鸿宣深暗隐怒的眸色后复又低了头,无奈道:“末将领命。”
弋鸿宣望了望骑马跟在祈枫身后的若然,返回她身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她,唇角微微上扬,似在笑,又似没笑。
“你很有本事。”许久,他冒出这么一句话。
若然愣了一下,不解地道:“什么?”
“你是个勇敢的女人。”他不多说,只细细打量着若然,然后拨转笼辔,吁马离开,扔下这么一句话。
若然咬咬唇,藏在身后的手在不留痕迹地微微颤动。一道鲜艳的猩红,正自手腕缓缓流下。他没发现就在他转身的那一刹那,京畿军中不知谁射出流矢不偏不倚地射穿了她的手臂。若然也不觉得疼,随手撕下一片衣袂,粗粗包扎好,朝他离开的方向追了上去。
一战不觉,子时已过。是夜不见星月,浓云密布天际,远山孤峰沉在烽烟罩起的层层迷雾中,无邪的墨青黛色渐渐迷离,模糊的棱角在重重隔霭下仅为依稀可见。往日安静无人烟的草原今夜沸啸如汪汪深洋,绝刃兵戈、骏马横驰、杀戮鲜血溢漫楚丘,滔滔似浪卷,一潮既过,一潮又来。
弋鸿宣要的两千兵马很快结集聚拢。祈枫挥了令旗,刹那间,铁骑滚滚踏翻黄土,南风亦如冬季的北风般萧萧鸣彻天地。
淌过一处山溪。溪水暗泽,清透的颜色凝结殷红,拽拽流逝,那一抹丝滑柔软,宛如在大地上铺过一道猩艳张扬的绝色绸绫。马蹄践踏,水花霰漫,绫绸刹那破碎成千万面被割裂的血镜。这镜子照不到人影,但照千万游魂飞魄,映出那焚燃的冥火,穿透天地之遥,直达碧霄黄泉。苍穹亦有哀,是也无奈,一声长叹。
西去之路,迎风有沙砾扑打面庞,不觉痛,唯觉苦涩难奈。若然忍不住伸手抹了一下脸,揉揉酸痛的眼睛。她不知道为何要这样眼着弋鸿宣,只是和他这样策马,前后保护几丈的距离——很好。
驰在前面的弋鸿宣突然回头看了看若然,目光怔了一下后他猛地怒道:“你受伤了?”
若然被他吼得一阵错愕,低眸瞟了眼刚才擦脸的手指,瞧见那上面沾着的淋漓血迹后,她这才醒悟,于是赶紧对着他摇摇头,慌道:“我没事。”
那双本就清凉冷寂的眼眸此刻骤然晦涩幽暗,弋鸿宣冷哼了一声,忽地勒紧了自己坐骑的缰绳停在原地,等着若然靠上前。
“怎么不走?”若然收住马缰停在他一侧,狐疑地瞥了瞥他。
弋鸿宣不说话,只是劈手夺过若然手中的缰绳,拉着她座下的马靠近他。若然挣扎了一下,却拗不过他手下的力道。
风声似乎在顷刻间停歇在耳畔。骏马踏踏,铁骑卷飞如云,身后的将士自他们身边一掠而过,马蹄声依旧匆匆而势猛,无人停留。
“做什么?”若然着急,恼火地瞪着他。
弋鸿宣眸色冰寒,望着她,冷道:“下马!”
若然莫名地看着他。他静静地回视着她,那样坚定不可拂其愿的淡漠眼神,那紧抿双唇透出的决绝和冷酷,看得若然心头一阵发毛。他的神情告诉她没有商量的余地,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命令,而非能让她讨价还价的条件。
“不!”若然甩鞭抽打他的手臂,想要抢回缰绳。
他不但不放开,反而狠狠用力带动马缰将若然和马一同拖向他的身子,她不明所以地望着他,他凝了眸子深深瞅着她,忽地那幽暗晦涩的眸光微微一动,锋芒浅曳的瞬间,那只拉着缰绳的手居然陡然上扬,一掌拍在若然的身上,将她打落下马。
“你!”若然迅速爬起,气得满面通红。
他不看若然,只重重一鞭抽向我的坐骑。马儿吃痛狂奔,迅如追风之速,刹那便不见其影。
若然扣指唇间,想要吹哨喊住坐骑却已来不及。眼睁睁地瞧着马消失在茫茫夜雾下,她咬了唇,扭过头悻悻瞪着他。
弋鸿宣叹气,弯下腰来,伸手抚上若然的脸,冰凉的指腹轻轻揉去她脸颊上沾染的血迹。
若然一把打落他的手,火大地吼道:“别碰我!”
弋鸿宣目色一闪,收回手,什么话也不说,只挥下马鞭,朝着有烟尘翻滚的方向绝驰而去。
“喂!”若然气得大喊,抬手摘下头盔朝他扔去。
手臂受伤无力,铁盔在空中划过一道漂亮的弧度,而后闷闷坠地,不甘地遥对着那越驰越远的金色麾衣。
“留在这里,我会把她完好无损地带回来的!”弋鸿宣没回头,声音自远方飘来,愈渺渺,竟愈见清晰。
若然愣住。半天,才自言自语喃喃道:“要小心啊。”
左臂受了箭伤,右臂被弋鸿宣打了一掌,双手垂落腰际,在不能自控地颤抖。若然转眸看看四周,找了一处可避风疗伤的山岩处坐下,手指轻轻揉搓着伤痛的地方,心中又憋闷又担心。
缓缓,若然褪下扎在手腕伤口的那块衣袂,垂下眸,一瞬蹙眉。滚落不止的殷红血色,衬着白皙柔滑的肌肤,别样怵目惊心。
风吹来。疼。若然倒吸一口凉气,刚才过度紧张,直到现在才突然觉得好疼。伸手自怀里拿出药粉洒上,血止,若然握紧手指,再取出一块干净的纱巾缠住那道伤痕。收拾好伤口,若然闭目,蜷缩着身子仰靠向身后的大石,耐心等待。
黑夜总会过去的。只不过,他唯带两千兵马追肃宁王的八千逃兵以及解救前方关隘处被笑阳围得水泄不通的为剑心所部……
若然寒噤瑟瑟,忍不住发抖,忙抱住了双臂,将自己缩得更紧。过了许久,耳畔的嘈杂声响渐渐沉寂,若然睁眼,望向两侧烽火迭起的地方。南风荡过山峦,吹伏硝烟,战前那呼啸不歇的狂劲此刻变做了一声渐一声低的轻轻呜咽。沙砾静静划破虚空,疏疏暗哑,夹着缓缓消沉下去的怒马嘶鸣声,将士呼喝声,兵刃撞击声,天地慢慢失音,清宇慢慢宽广。
待到万物皆静籁的死寂降临时,乌云压顶,降至了最低点,重重拂上人眼,似乎在按抚着一切命逝不能瞑目的荡荡魂魄。
短暂的气流凝滞后,有隐约的哭嚎在远方此起彼伏,腥气浓浓散开,抵在人心底最坚硬的地方,慢慢地磨,直至那里软弱成了棉絮,虚而无力,垂垂不知生死的距离。心坠坠下沉,下沉,沉入万丈无底的深渊。
若然抬了头,却在这一刻缓缓舒了口气。终于,岢岚夜战止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