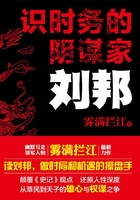拂晓回宫。那时天还未亮,一路宫灯明火曳曳璀璨,一路露水沾衣轻轻湿寒。晨曦一抹微弱地嵌在墨沉天际,日夜轮回,朝鼓嗡嗡,鸟雀离巢乍起,灰影道道如离箭之弦,纷纷冲往头顶上那昏瞑未燃的沉沉苍穹。
一夜徘徊,一夜挣扎,迷失着,彷徨着,苦撑着。
而后神游在外,脑中空惘,步入瞳然居的刹那,说是失魂落魄也不为过。
守在殿里的慕吟上前为梓瞳摘去帷帽,解下斗篷,语气一反往常的平静柔和,满是着急无措的惊惶:“昭容这一夜去哪里了?皇上半夜回来后到处找你,急得都要疯了。”
梓瞳无言,坐落椅中,手指按了按额,头疼得厉害。
慕吟没奈何地叹息,抱着梓瞳按抚了一阵后,转身倒了杯热茶塞在她手中,软声劝慰:“不管出了什么事,等皇上上朝回来后,你们坐下来好好说说,可别再意气用事这般折磨自己了。”
梓瞳静静听着,静静饮茶,想了半日,而后默默点了点头。
慕吟伸手抚摸着梓瞳的发,她的手很柔软,她的动作很轻很慢,只是这般平凡无常的举止却给梓瞳说不清的熟悉和温暖,缓和着她凝僵呆滞的思绪,抵消着她心底的疼痛悲伤,渐渐地,让她靠着她的怀抱,忍不住闭上眼睛,脑子沉沉入坠,仿佛欲睡去前的祥静安谧。
忽而听慕吟低声念叨了一句:“皇上?”
浓郁的琥珀香气在鼻尖散开,梓瞳睁不开眼,只知有人轻轻地将自己横抱而起,脸颊靠入他胸口的刹那,一切如常的贪恋和安心。
脚步声悄然响起时,梓瞳在他怀里低低叹了口气。那人身上的缠绵清幽的香气依然滞留在他的衣襟前,淡淡的甜味,似曾相识的味道,吸入鼻中时,竟陡然有明艳如牡丹的笑魇在脑海里徐徐浮现。
于是当他把她放上软塌的时候,她终是睁开了眼,看着头顶上方那张俊美风流的面庞,痴痴出神。
他怔了怔,半弯着腰,手臂揽在她的腰间还未及撤去,脸靠近在她的眼前,面色有些苍白,微微皱起的眉间些许流露着几丝疲倦和慌乱。
对望半响,他俯下脸来,将冰凉的肌肤贴上了她的额角。
“去哪里了?我找了你一夜。”这声音嘶哑得宛若断裂的弦,寂寞清冷,孤独苍凉,仿佛要遗世独立,却又偏偏小心翼翼地,带着生怕一言将她激发逃离的害怕和紧张,听得她的心顿时难受得狠狠揪作一团。
他分明已猜到了,却还是要问。
梓瞳动了动唇边,努力许久却仍是吐不出一个字,于是只能继续沉默。
柔软炙热的鼻息慢慢靠近下来,他要吻时,她却侧过脸生生避开,轻声道:“不要碰我。”
梓瞳想忘记,不想逃避,可惜脑子却该死地记得那样清楚,不久前,她吻过你。
压在身上的身子猛然一僵,他伸手扳过她的脸,凤眸低垂,紧紧盯着她的眼睛。此刻那目光是她从未见过的深广幽暗,墨瞳里宛若盛满了还未褪却的长空夜色,黑黑地,沉沉地,冰冰凉凉地,光华尽散。他的眼神颓望而又悲伤,却又偏偏带着致命的美丽和吸引,诱惑得人非得要与之一起沉沦、沉沦,继而魂魄消散这茫然不见底的黑暗中,再不见影。
“瞳儿,别走,别离开……”他低声喊,嗓音沉痛,好似她已离他远去再不回头的绝望和孤苦,“对不起,原谅我,原谅我,好不好?”
一瞬还是心软,眼中雾气顿起,朦胧中,她只瞧见他痛苦的神情和愈来愈暗沉下去的眼眸。手指控制不住地抚摸上他的脸庞,轻轻地,划过他的面颊,泪水滚落不断。
“好……”梓瞳点头,泣不成声。
他再一次吻下来,而她这次没再逃。
不知多久后,弋鸿宣伸手揉抚着梓瞳的发,口中低低道:“明日,我会下旨封苏瞳媛为淑妃。”
苏瞳媛?……听说苏瞳媛亦是难产,几走生死边缘,好不容易诞下的皇子……只是是否真的是皇子,梓瞳不知,也不想知道。
心不气也不急,早已料到。她已成了你手中最有用的棋子!梓瞳愣了一下,而后点头:“好。”
“还有一事……”他迟疑,停顿下来。
梓瞳回眸,望着他。看清那眸子间的不舍和痛苦时,她心中一颤,倏然明白他所说之事指什么。心中凉得彻底,寒得刺疼,一道道伤痕宛若撕开的痛楚,淋血不断。梓瞳忍不住冷冷一笑,凝眸看他,轻轻道:“几时?”
“三日后。”
梓瞳沉默,瞅着他端详半日,忽道:“好,好啊。恭喜皇上,喜得太子。”太子的受封仪式就在三日后!
那双盯着她的眼眸瞬间冰冷下去,无边的黑夜被揉碎在里面,一片一片,尽是裂痕。
结局还是这样?你封了苏瞳媛的儿子做太子,那是否意味着朝中局势将会有重大变化?而萧家再容不得我陆家再成为你皇帝的人,会对我下手,对吧?果真!你舍弃的还是我!
弋鸿宣抱紧梓瞳,嘱咐着:“近日不要出去!”
梓瞳一笑不言。
“近日,你一定不许出去……”
他反复命令,这般的在乎终是激起了她的好奇,梓瞳望着他,问:“为什么?”
“萧文渊昨夜遇刺,我怕萧家已经乱了……到时候他们会对你……”他将脸埋在她的脖颈处,搂着她的胳膊不断收缩收缩,箍得她全身都在痛。
哼!你果然当真是要保我的命!可如若那晚我不将整个陆家献于你,你是否还会保住我?你步步算计我,却还与我讲情?
那日若不是你故意要我与你同去慕容在郊外的山庄,知道原来慕容氏根本不会与萧氏合作,又怎能让我心甘情愿地把应允把陆家给你?
你口口声声说爱若然!又反过来说爱梓瞳!你到底爱谁?还是你谁也不爱,爱的只是你的自己,你的江山?
只是你所谓的保我?只是为了万一我有能力自保后,你依旧可以用柔情骗我?还是是真的……?
喜宴,其乐融融。
眼看天下人倾心喜悦,金城九陌街巷皆有红锦铺地,鲜花簇道,锦旗招展。宫廷里外更是焕然一新,几月前因崔太妃(注:先皇成时的崔太妃现在已是太皇太妃)病逝而缠满宫檐栏杆的素色丝帛帷帐统统除去换上了鲜艳夺目的大红绫绸。宫人皆着新装,侍女换彩色的裙裾,内侍换暗红的长袍。清歌坊歌舞日日兴,丝竹绕耳,响彻宫廷,昼夜绵延不绝。
瞳然阁清冷寂寞,独存在四处洋溢着欢言笑语的诺大宫廷中,仿佛死灰笼罩的了无生气。
前些日子有宫人拿了红绸欲系上瞳然阁的殿阁时,慕吟生平第一次发那么大的火,挥掌过去震碎数匹红纱,吓得那几个宫人面色青白,收拾着满地碎布慌慌逃走了。此后也再未敢来。
梓瞳站在窗前冷冷瞧着,入眼云烟,过眼云烟。
慕吟回头看着梓瞳时,面色一恸,梓瞳还未及流泪,她却先哭得伤心断肠,满目不舍和怜惜。她痛得厉害,因为她今世祈愿的最后一个奢望就被梓瞳和弋鸿宣如此这般给狠狠地捏碎了,留给她半世惆怅,半世不甘,半世难解的忧愁和辛酸——对于若然,她是一直有愧的,小姐对皇上或许是有些情谊的,却并不及小姐对凌君涵来得深!这一点,慕吟是明白的,她一直自责于以前那件错事。自若然死后,她便只叫慕吟,而不叫媚仪了。所以当梓瞳,这个像极了若然的人出现后,慕吟先是对她有些排斥,可渐渐地还是接受了这个女子。她对梓瞳好,七分出于她身上的确有若然的影子,三分出于这个女子虽然总在演戏,可对人好,对是实实在在的。因此,慕吟才会提醒她,不要爱上皇帝,那是一辈子的痛苦;因此,慕吟此时才会陪着这个女子一起痛,她明白的,现在是这个女子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了。
这日傍晚,乌云压顶,雷声闷闷作响,虫鸣蝉叫不绝入耳。因天色昏暗,殿里的灯盏早早亮起,梓瞳和往日一般坐在书案前翻阅那些记载着上古之事的竹简,摘抄纪要,专心致志。
慕吟在一旁收拾着衣裳,静静地,耳中只听得丝绸锦缎窸窣细碎的摩擦轻响。
倏而她“咦”了一声,梓瞳抬了笔蘸墨落字,随口道:“怎么了?”
“小主,你看这绛纱……”慕吟抱着那个锦盒走过来,将绛月纱递到梓瞳面前。
梓瞳抬眸望了一眼,愣了愣。这还是第一次在昏暗光线下见这纱料,入目只瞧见银色冰凉,带着流水般潋滟的光泽,寒芒幽幽,耀眼夺目,却又清冷如霜。
果真是漂亮到不可思议的宝物,想不到当初慕容家要娶自己时送来的嫁妆还真丰厚。本来后来与慕容家退了婚,这些个嫁妆是要送还的,可想不到自己进宫前慕容家又命人送来了礼物,其中就有这盒布料,梓瞳当时也未在意,只觉质感不错,怕理皇宫中也少有,便带着一同进了宫。
慕吟道:“过不了多久就暑热难当,这纱料触之清凉,不如我让命人做了这衣裳,小主当夏穿正好。”
梓瞳收回视线,继续写着我的摘要,淡淡道:“慕吟你做主。”
“小主想要什么样式的宫裙?”
梓瞳笔下一顿,突发奇想:“就做最华贵的吧!”
慕吟看了看,沉吟一下,道:“也好。”心中却有些奇怪,以往梓瞳的着装并不要求华贵,凡事从简就行,倒不是她不喜华贵的,只是华贵的衣装多是繁复的,每次她穿时,都会觉得烦琐,显得很不耐的样子,几次下来,便也不太穿华贵的衣衫了。
慕吟转身要走时,梓瞳不知怎地心思猛然一动,忙叫住她,欲开口却又迟疑了半日,思了又思,方问道:“慕吟可知道百花阁的紫罗姑娘?”
慕吟愣在那里,不解:“小主问她做什么?”慕吟当然认识她,就是这个女人,那天险些要了小姐的病!若不是主子……
梓瞳放下手中的笔,想想,还是黯然叹了口气,揉揉眉:“我就问问,听说她的舞不错。”言罢眼睛盯着案前烛火,脑中想着那日萧潋晨与自己坐在百花阁亭里说的话,心中顿时惘然落寞。
慕吟望着梓瞳,默了一会,忽道:“小主若要见她的舞,倒是不难。那位紫罗姑娘自视清高,跳的尽是从宫廷传出去的舞,所以……”
梓瞳闻言却来了兴致,微微一笑,道:“你命人来跳给我看看。”
慕吟轻声一应,捧着绛纱离开了。
“都不见了……究竟是什么,把你身上的快乐和恣意都带走了?一年前我在绫罗城的贾府遥遥地看到一个明彩紫衣的少女在庭院中翩翩起舞,她的笑声明亮清脆,她的笑容娇妩纯净,她的舞姿,无拘无束,无谓无求,旋转在阳光下时,身旁流转的光华能让骄阳之芒也情愿为她失了颜色。”
萧潋晨刻骨幽凉的声音冷冷浮出脑海,梓瞳怔然,而后闭眼摇晃着脑袋,拼命忘却。梓瞳找紫罗,并不是学舞,而是为了萧潋晨那日所吹的曲子。
窗外银光忽闪。一道凌厉的闪电陡然划开谧色天际,墨沉的云雾间露出一抹森森白练,直泻而下,迅疾漫扬开来。刹那后,雷声隆隆欲震破天。
雷霆万钧,滚滚袭上胸口,一声一声敲得梓瞳心中那股抑懑潮涌翻覆,只觉喉中一甜,竟张口吐出血来。
慕吟刚回寝殿来,见状忙摇晃着几近入化呆滞的梓瞳:“小主,你怎地吐血了?”
梓瞳筋疲力尽,低声道:“不妨。我内息不调,吐点血算得什么?”
“唉……”慕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不再多言。
雨后的天空往往静谧清朗,月下有烟花团簇绽放,五颜六色的璀璨争夺衬得今夜月辉愈发地皎洁美好。
只是纵使这天上圆月的银芒再灼灼粲然,却也不及此刻人间明德殿半分的灯火辉煌。
高銮玉阶,明殿喜堂,红锦地衣铺曳连绵,靡丽香气霰漫四周,千盏琉璃灯悬挂宫檐下,烛火耀动,艳丽张扬的红光将昼夜照得瞬间颠倒。
踱上玉阶,靠近殿门。门外内侍欲高声通传时,梓瞳瞥眸过去,德顺公公赶紧挥手让那内侍住了口。
眼前情景有些意料之外的怪异。
殿外是何等地喜色奢华,殿里却不闻钟鼓丝竹之声,也不闻宾客喧哗之闹,一殿千余人竟皆沉默着,脸上神情千般模样。除瑟瑟退在殿侧的宫人侍女不敢抬头外,其他所有人的目光俱专注在殿中一人的身上,眸色复杂怪异,或好奇关切,或紧张担忧,或不屑鄙夷,或索性是抽身一旁看戏的惬意自在,气氛凝滞冻结着,宛若冰封不可破。
梓瞳在门外伫立许久,静静看着殿内情景,不言不动。殿里局面看似应该与她这个未到之人无关,只是不知为何她瞧着瞧着,突在初夏之夜感受到了冬日的冰寒。
殿中央站着的是萧潋晨,金丝勾边的墨绿锦袍(注:他已经很久未着红衣),身影修长挺拔,一人独立于坐着的千人之间,的确是让人想不注意他都难。
高高的金銮上有三人坐着,当中席是弋鸿宣,左首太后,右首皇后。殿下,梓瞳也有几个认识的人。弋曦航到底年幼,稚嫩的面庞纯净如玉石,此刻只顾眨着眼睛,倒是一派天真。慕容吟风垂眸慢慢饮着酒,面色清冷淡漠,不察一丝情感。范以安直直盯着萧潋晨,神色忽晴忽暗,目中锋芒浅露,不知所思。
苏瞳媛弯唇轻轻笑着,笑容一反往常的妩媚,华贵衣裳下容颜端庄可亲,望向萧潋晨时明似秋水的眸光微微闪动着,似是刹那有所恍悟。
还有高高在上的那人……
面若凝霜,薄唇却略微勾起,看是似笑非笑、满不在乎的神情,只是凤眸却冷冽冰凉,目色黑暗得从所未见。
一时仍无人说话,也无人注意到殿外悄悄到来的梓瞳。
终是萧太后座下难忍,耐不住咳了咳嗓子,焦急中隐含无力的嗓音在空寂的殿里慢慢回荡:“潋晨,皇儿赐婚欣妍于你一事,你可要考虑清楚啊!”
“考虑什么?”弋鸿宣忽地出言打断太后,轻轻一笑,横眸,“君无戏言!”
太后眸光闪了闪,不吭声了。
梓瞳闻言一怔。
德顺压低声音在梓瞳耳边道:“这萧大公子究竟何意?竟敢在今夜拒婚,不是驳了皇上的面子吗?”
梓瞳默然,只侧眸看他一眼。德顺低低垂首,道:“小主恕罪,奴不敢妄言了。”
殿里萧潋晨此时长声笑道:“人皆道我萧郞风流成性。可自从我的心里住进那个女子后,便再也容不下她人。”
太后踌躇,看着弋鸿宣:“鸿儿,这……”
弋鸿宣悠然一笑,面色温和,言词却冷:“死者已去,生者何恋?”
萧潋晨笑了笑,不答反问:“如果一个男人连死去的女人都要背叛,他还有何资格坐拥天下?”
梓瞳心中一惊,拢在袖里的手指紧紧一握,暗叫不好。她虽不知萧潋晨今夜有此言此行究竟真是为了拒婚还是为自己鸣不平,抑或存心是要搅乱太子的受封仪式,但他如今此话直直冲向弋鸿宣,摆明是嘲讽他,弋鸿宣怎么会轻侥他?
果然,再转眸看弋鸿宣时,他的面色再维持不了先前的从容,脸庞铁青,目光暗沉透黑,隐隐流转的锋芒凌厉犀绝,竟是杀机已动的愤怒。
他这些年忍得太久,承担得太多,撑到这一刻已属不易,偏萧潋晨还得出言刺激他,怒火一旦引出,再回头便难。
心里一急,梓瞳正要举步入殿时,一直不曾出声的欣妍却柔柔笑起,言道:“这既是我的终身大事,怕由不得你二人做主,争了何用?皇兄,也不问问我的意思?”
听此,梓瞳不由地多望了欣妍一眼。这个才十五岁的小公主倒也有自己的过人之处,今天这番沉着的话语早已没了那日见到自己与潋晨在一起时的冲动,俨然是一派大国公主的风范。听说她是师妃留下来的女儿,先皇带她极好,弋鸿宣也很疼她。
蔚舒萌这时接话,道:“欣妍所言正是。不过皇上,今天带有更重要的正事要办,对不对?”
见太后不满地望了一眼“多嘴”的蔚舒萌,梓瞳也不由地一怔——从蔚舒萌这一年来的表现,种种迹象都表明了她已投入太后一派,现在怎么催着弋鸿宣办太后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呢?
“正是。”弋鸿宣稍稍缓了缓脸色,对众人道,“朕今天还要宣布我朝的太子人选。”
言语一出,在座中引起的反响倒不是很大,因为大家差不多都是聪明人,本朝三皇子出世后的第三天,皇上就为了设下这么隆重的庆祝宴,怕皇上的心思已经很明显啰!这萧家独大的天,怕是要变了……
“皇上今儿个就要宣布?可内阁还未议论出哪位皇子更适合当太子。”也难怪有人要跳出业这么说,因为太子的废立,一向不是皇帝一个人能完全做得了主的。
“怎么?既然爱卿们都讲不出个所以然来!朕的太子,就由朕来决定!”当然太子的立定,前朝也有皇帝直接说了算的例子在,所以弋鸿宣硬要这么多,只要理由足够,中立派也不好提出什么理由来反对。
“不知皇上心中的人选是?”
“三皇子弋胤航。”弋鸿宣会说了这个答案,的确没有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不待萧家的人发难,弋鸿宣便又继续道,“瞳淑妃甚得朕心,三皇子又聪明强壮,朕意已决,此事就这么办吧!”
“皇上!”殿中又一人出列,“皇上正值盛年,立太子一事恐是太早。何况我朝中先有天资过人、由远空大师亲授武艺的大皇子,后有母妃尊贵的二皇子……”
来人说的倒也极有道理,且样样针对皇帝刚才的话——大皇子贤,不是刚出生的三皇子可比的;二皇子的母妃尊贵,不是苏瞳媛可比的(历朝选太子,向来重视其母亲的出身,虽有母凭贵,可何尝不是子凭母贵呢?)。
弋鸿宣拂悦,望了一眼殿下的出头鸟!梓瞳也不禁皱眉,这个男子立太子的准备怎么如此不充分?被人驳了一两句,就讲不出话来了?
“黄大人所言不假,但却也不全。”还是宋元韶及时站了出来,“大皇子虽贤,其母妃的出身不比淑妃;萧贵妃虽然尊贵,可二皇子累年病弱,怕是不合适吧?”宋元韶肯这么做,倒也是抱了得罪众人的决心,谁让他是弋鸿宣的铁杆追随者呢?
被宋元韶这么一说,倒也是极在理的,让人觉得思前想后,比来对去,还是三皇子的综合实力更胜一筹。
“是啊,鸿儿。”见火候正够,众人所谈也不出乎自己的意料,萧太后终于开口道,“你正当年轻力强,也不急于立太子。何况陆昭容也是皇宠正盛,为咱们皇家再添一丁也指日可待呀!”
呃?绕来绕去怎么绕到自己身上来了?
慕容吟风终于慢慢抬起头来,微转的眸光似冰水之色,幽凉而又深邃。满殿无人得知梓瞳的到来,唯有他凝了眸直直望向她的方向,嘴角弯了弯,笑容雪般冰寒,却丝毫不掩那炫目的美。梓瞳发愣时,他稍稍一拧眉,冲着她微微眨了眨眼,眉宇间尽是妖异至绝的得意之色。
“表哥”,我服你计策不断,如今这一刻我才知借手与弋鸿宣谋萧在明,是幌子,联萧谋弋鸿宣却是暗,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既不可得便索性让它牵扯了朝政一起大乱……以财富换势力,先帮弋鸿宣除去了萧氏在弋南的势力,实则是趁虚而入,抢占了弋南的地盘,现又出计萧氏,要他们将我陆氏也拉下水,在这锅粥中搅上一番!原以为是聪明人各有算盘,却不知其中布局层层圈圈,真假不明,步步皆谋。
天下博弈的棋局上,立太子一事前后背里纠缠不断,种种晦端暗潮皆藏其下,一步踏错,一个不慎,便是整盘皆输,且毫无翻身的可能。而这之前,弋鸿宣步步皆没错,甚至还将你数子。
错只错在,利用我的人聪明地看清了我为陆家的欲望和狠毒,却没有看懂我的心。而如今你又把一举扩大慕容氏的赌注押在了我身上……表哥,怕只怕,你又算错了这一步。
殊不知我也是狠心之人,萧氏既狠心对若遥,君涵、舒璎之死也由他们间接造成,我即使放弃一切也不会便宜了他们,更何况是弋鸿宣不真正掌权,我如何从他手中夺走一切?
别说一个小小的陆家,我不放在眼里!哪怕是人尽数卷了我在弋南的所有暗处势力去,我也在所不惜!
梓瞳脑中思索不停,心里苦笑不已。
半日,终是深深吸了口气,站稳了身子,挺直腰,略一昂头,眸光睥睨笑望向殿间,口中淡声道:“公公,劳烦您为本宫通传一声。”
“诺,”德顺轻声一应,随后便扯了嗓子,高声呼道,“陆昭容到!”
满殿闻声死寂。
而后诸人纷纷转眸看梓瞳,千双眼光如千道剑芒,齐齐直戳她的身上。瞬间,殿间私语低低响起,唏嘘短叹声不绝。
梓瞳先为慕容氏儿媳,又改嫁皇帝是以为天下所不耻;入宫一年从未怀孕,各中消息早已传得沸沸扬扬;整个陆家在这非常时期也是退不得,进不得——退,不选择皇帝,那慕容氏定然取而人之;进,萧氏联合慕容氏,陆家的产业亦岌岌可危!可这一切都要自己去面对,没有哪个人可为自己挡风遮雨,甚至将自己推上风口浪尖处的人还是他!
早在让德顺通传时,梓瞳便知自己今日的境地是避无可避的尴尬和窘迫,然一步既迈出,她只能选择独站在那危危的浪尖上,承受着脚下无尽无止的浪起潮涌,承受着心中的割裂疼痛,脸上,偏偏还要表现得风情云淡。
缓步踱至金銮下,欲要行礼屈膝时,太后却连忙摆了摆手,欢喜道:“昭容免礼。你来了便好。”
梓瞳直起身,蹙眉笑了笑,佯装什么都不知,道:“臣妾虽然抱恙在身,可今日是太子的受封仪式,臣妾怎能不贺?”
太后有些愕然,想不到梓瞳会如此直接地表态。
萧潋晨走来梓瞳身旁,妖娆的眉眼间隐有忧虑和浅浅的愧色。见她望见自己,他抿抿唇,开口说话时那忧色和愧色刹那不见,唯余一脸淡定自如的笑意,堂堂然道:“依昭容之见,可是觉得立三皇子为太子合适?”
“嗯?”梓瞳轻声一应,转眸看看弋鸿宣和苏瞳媛,略作不悦,“皇上圣明,雷霆圣断,岂有不合适的道理?萧大人如此说,怕是大不敬吧?”
萧潋晨声色不动,慢慢解释道“臣只是实话实说。淑妃贤不及皇后,贵不及贵妃,德不及你昭容,才不及清修容……实在不配为太子之母。”
梓瞳拧拧眉毛,笑望着萧潋晨——倒是好个突破口,不谈皇子,只谈母妃,硬是把陆家和慕容家都拉了进来!
萧潋晨直直看回来,眸光流转,脸上笑意瞬间又深了几分。
彼此的意思此刻皆不言而喻。梓瞳要止了这话题,他却偏偏顺着话往下纠缠不休。
想来明明对彼此都有所不忍,此刻却是为了各方利益竟当众对峙如此,也是悲哀。只是想想,他也是苦的!萧潋晨虽不支持萧氏现在的做法,也早已脱离了他们权力的中心,可他不忍眼睁睁地看着偌大的萧氏被弋鸿宣连根拔起啊!
梓瞳低低一叹,笑道:“淑妃将来只是太子的母妃,有皇后这位贤后作为母后,众人还有何不放心的呢?日后,再配以出色的太子太傅,太子太保……我太子如何不出色?”
萧潋晨垂眸望着梓瞳,轻笑,不以为然:“日后?既是如此,何必急于立太子?”
梓瞳一扬眉,问回去:“你说呢?”
萧潋晨眸色一动,默了片刻,忽地却改了口:“也罢,只要皇上能给个合理的解释。”
梓瞳笑而不语。
萧潋晨抱揖施礼,转身,回到自己的案席。
梓瞳松口气,转眸看看四周,见銮下右首空着的席案正欲踱步过去时,一个声音却又将她唤住:“昭容,听闻后宫之中你与淑妃娘娘势成水火,互不相容,可有此事?”
梓瞳顿住脚步,回眸看着说话的那人,沉默。
那人坐在前排,一身灰红色的锦袍,面容苍老清癯,目光无惧无畏地盯在梓瞳的脸上,神色间是丝毫不能退步的坚持和固执。
德顺低声提醒,道:“昭容,这是大学士。”
梓瞳微微一颔首,正待开口时,弋鸿宣却冷冷道:“朕后宫之事岂容外臣插嘴?”
大学士起身躬腰,道:“皇上明鉴。后宫之事,虽是皇上家事,却也是朝廷大事,国家大事。若是淑妃善妒,怕不适合为太子母妃吧?”
他的话一落,诸臣皆纷纷起身称是,请求皇帝明断。
梓瞳忍不住冷笑,瞥眸看弋鸿宣时,他却神情不动,面容甚至较先前萧潋晨挑衅时还稍有缓和,凤眸微凝,唇角轻勾,漫不经心的笑意下眸色诡谲变幻,似怒似喜,似悲似恼,别人看不清一丝一毫。
梓瞳才发现他今日穿着绯色流纹的长袍,艳丽的色彩衬着那张俊美魅惑的容颜,顾盼之间的飞扬神采盖下了满殿的光华。
一殿千人,独他最耀眼。
只是他的肤色今夜却有往常不见的苍白,薄唇也浅得近乎没有血色,长长的眉毛虽舒展着,眉宇间却凝结着比蹙眉苦恼时更多的愁和恨。
一殿千人,独她看出他心底此刻的伤和那蠢蠢欲发的勃然怒火。
于是待他开口前,梓瞳先笑了,亲自去留给自己的那张空席案上执了酒壶,拿了酒杯,转身对众臣们道:“诸位不必如此忧虑。梓瞳与淑妃娘娘情同姐妹,在后宫亦是和平相处。今儿个是三皇子封太子之日,梓瞳正要敬娘娘三杯。”
诸人互视几眼,略一迟疑,仍站着不动。
梓瞳侧身,满上酒杯,将酒壶放在苏瞳媛的席案上,捧着酒杯弯腰而拜,笑言清晰:“梓瞳恭喜淑妃娘娘。”
言三次,次次锥心滴血。
酒三杯,杯杯凉彻骨骸。
弋鸿宣,我助你至此,你若负我,不得好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