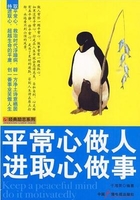望了眼殿外阴瑟瑟的天气,几片乌云拉耷在天际,百花凋零,尽是一片残枯之色。这种初春时节的黄昏瞧在眼里,任谁心情都难以维继。
但此时此刻,本朝最年轻的皇帝岂止心情不好,他根本是濒临发火的边缘。
如果面前这御史大夫再不停嘴的话:“皇上,臣刚才已说得很明白,太祖皇帝定此作战之法,本就是变相牵制,没道理传至今日无端被废。”
很少用这种严厉语气与臣子说话,只是自己的主张一再被挑衅,一向以和善、儒雅示人的弋鸿宣也难免会上火气:“朕也说得很清楚了,将帅一旦上战场,便要依势而为。若每个行动都受作战之法所制,这仗还要怎么打?祖宗虽有法制,但未必每项都适用现今……”并非不知殿中所站的人多数都是老顽固,但鸿宣在这件事上不愿再继续委曲求全。
“皇上,这是武官的事,不如就交由他们去研究吧。”侍中上前道,显然他觉得弋鸿宣对战事是一窍不通。
自己的权威被质疑,弋鸿宣不由地一翻苦笑——从小到大,朝中军事动向,他向来关注,无论是北朔的骚动,还是国内零落叛乱,每日邸报一到,他总会细细研究。只是自己的这些臣子们却都不知道,连击败太子的那些战略布署也大多是自己的主意。可这些事弋鸿宣现在又不能说出来。听侍中的那些话,摆明在说他不自量力。赌着一口气,心中不免也是火起。只是这样却更让弋鸿宣认识到收回权力的重要性了。
见皇上终于不再言语,却是冷着张脸望着殿下众人,眼里又闪起倔强而深邃的眼光,侍中胡伯璋大人也心知最后一句未免说重。可牵涉到政事,这个耿直的老臣脾气一上来,也向来不先让人的。
今日决定要改两事,便没有奏一事便被吓回去的道理。弋鸿宣暗暗稳定下情绪,再次启口:“关于弋山封禅一事,众亲家有何意见?”
“自先皇在时,朝廷便颁下檄文,传旨全国,中封弋山。这几月来,全朝上下为此事做足准备。但据臣得知,到目前为止,为这仪式所花银两,光玉帛、牺牲、庶品、粢盛一项便需四十万贯,更别提仪仗马匹,赏赐诸事了。而且此次随行司职,竟高达两万有余,臣问过封禅官大人,只怕不超用八百万贯,绝对压不下来。只是一个祭祀,便要花去国库三分之一的银两,这未免太过了。皇上三思啊!”宋元韶早就与鸿宣唱一出双簧,方才那事他本也想说话,却被侍中那个老顽固以文官不懂战事给噎了回去,这次他一定要据理力争。
弋鸿宣朝宋元韶送去了个会心的微笑,殿中也有一些无派系的人知道宋元韶是皇上的晴雨表,见他如此表态,想来圣意也八九不离十了。
“只是一个祭祀?”只是侍中又冷哼着一笑,显然他今天是和弋鸿宣扛上了,“你竟不知弋山封禅对国家之利,岂是单单一句祭祀能囊括的?我朝开国以来,太祖太宗皇帝保此心愿却无法成行,及至皇上这一朝,若能达其所望,扬我国威,也不失为大功一桩。敬天祭祖原本就是极其严肃之事,规制严格,礼仪繁复,容不得任何差池,倾倒山之力,在我看来,也是值得的。”
“太祖太宗皇帝三十年节俭治化之功,海内才见殷富。封禅一事再重要,也无须铺张穷奢至此,何况现时国情与数月前又是相异,外患内忧之际,军费开支如此勒紧,还花费大笔银两在……”虽然一些人愿意随皇帝的意思,可碍于侍中大人这样说,而蔚相与萧大人都不曾表态,众人也迟迟按兵不动,宋元韶才得不孤军奋战。
“军费自有军费额度,尚未挪用,你无须担心。”胡伯璋一句话便又把宋元韶挡了回去。
“治国以百姓为本,这番糜费,致使仓廪空虚,若一旦入不敷出……”宋元韶依旧不依不挠。
“不会的,户问自有打算……”总之胡伯璋就是利用宋元韶无要职,对一些形势没资格了解而大做文章,让他讲不出什么话来。
“皇上!繁华不是常享之物,剩下的三分之二不足以……”眼见着自己的话句句被胡伯璋兜回,宋元韶索性直接对着皇帝道。
“和你说了不会的!”只是胡伯璋似乎说上了瘾,也不看弋鸿宣不善的面孔,直接又将宋元韶的话挡一回去,语气颇是不耐。
“弥补全国基奠,照此下去,国敝民疲……”宋元韶却也是火了,朝胡伯璋一挥衣袖,继续对弋鸿宣道。
“……”见眼前这个青年榜眼这样讲不通道理,侍中也有些怒火,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朝廷何必慕虚名而受实祸……”宋元韶也豁出去了,不停翻动着嘴皮子。
“闭嘴!祭祀乃社稷大事,岂容你……”胡伯璋倒也没料到宋元韶如此得寸进尺,便也继续道。
“如果届时……”宋元韶见胡伯璋又发话,便也立马紧接着道。
“朝廷自有……”
听着整个朝堂哪还有半点议事的氛围,弋鸿宣不由地抓起桌上白纸,狠狠一捏便掷了下去,吼道:“都给我闭嘴!”
随着他一声呵斥,殿中立时极静。
苍茫暮色透过窗棱,后浪推着前浪,快速降临。满室摆设,呆楞在原地,在阴影笼罩下,仿佛早已僵硬。
那纸团正中宋元韶额头,一弹,落到地上滚了两圈,耽搁着再也不动。
他们互相瞧着,思想在共同的傻愣中混成一片,憧憧地,竟都起了些零落的茫然。
片刻后,还是弋鸿宣先别过眼,把头撂过一些,“别说了,你们退下吧,让朕清静两天!”用手一捏额角,声音已略显沙哑疲惫。
看着他,张了张嘴,却再也无话,宋元韶心上忽起一丝儿凄凉,强行隐下。从容地一躬身,平静开口:“臣……遵旨。”这件事的确是他办得不好,只是他也没料到胡伯璋这个老头虽不拉帮结派,可却是个十足的老顽固,认准了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来。众人离殿,望着宋元韶下殿,绕过门时,还不经意地摇了摇头,弋鸿宣明晰他心中感觉,亮堂得犹如自己心中一样。回头,瞟了眼站在边上的蔚修远,其嘴边微笑,了然透彻,让他感觉无所遁形。
蔚修远见弋鸿宣面上不悦,忙跨上一步,也不止笑,俯身一揖,语气从容,温和开口:“老臣……只是认为急进了些。”
静了片刻,弋鸿宣忽然咳一声,转过头去,从侧面,瞧不清他脸上表情,只听他低声道了句:“没头没脑,说的什么?”
这内中真处,别人不明,蔚相却是知道的。想弋鸿宣极有主张,哪能受得这般主意被人驳回?只是蔚修远根明白有些话大家心知肚明便可,没必要说出来,于是当下止口,退回惯常站的角落,唯脸上笑意更深,沿着皱纹舒展,这笑果真有些狐狸的味道。
适才蔚相短短一句话,聪明如自然懂其深意,也心知若非有何更深层次的话要讲,那话断难宣之于口。只是此刻,自己心中也是紊乱,不由起身,下台阶,捡起孤零零躺在地上的纸团。惨淡的夕阳斜照,稀薄的光线在他深沉的脸上晕开,他却盯着那不大的纸团,恍恍惚惚,浑然未觉——夺权之路,竟是如此艰辛!
当弋明宣跨进资政殿时,看见的便是自己向来英明神武的六哥,居然手里握着个纸团,站在殿中一脸神思不属的样子。明宣趁其不意,上前一把抱住他腰间,跺脚嚷道:“六哥,六哥,快点回魂!”
弋鸿宣给他吓了一跳,待看清来人,伸手一敲他脑袋:“什么回魂,越来越没大没小。”
弋明宣这才嘻嘻哈哈地放手,一歪头,“哪有?这不,小弟给六哥请安来了。”
“这个时辰,你还想到来请安?说吧,又有何事相求?”话意虽不屑,语气却十足宠溺。生长帝王之家,亲情于他,向来是种奢侈,可自从身边常伴这精灵古怪的小弟,自己总算还能享受片刻手足真情。弋明宣是代宗的第八儿子,今年不过十七岁。
见六哥将纸团顺手扔进纸篓,回座上坐了,弋明宣忙跟上去,不服气道:“六哥,你真将我看扁了,难道我每次来找,都是有事相求不成?”
“哦?今儿个转性了?”弋鸿宣眉间尽舒,唇边顺带出一丝久违的轻松笑意。
弋明宣索性下巴一翘,嘴巴一噘,“我刚打祈泽宫那儿来的。”
三宫中,祈泽为尊,乃太后寝宫。弋鸿宣一听,笑意不知不觉收了几分:“母后有何指示?”
“三哥,她以为我年纪小听不出,其实我哪有不明白的?她那是旁敲侧击,绕了半天无非想套我的话。你整整一个月没点过牌子,她当然急,不敢当面问你,就把主意打到我身上来了。”
“你怎么回的?”眼神一谙,脸色不免浮上些话不悦。
“我说六哥你修身养性,一门心思为国为民,不正是那求都求不来的好皇帝,她还吓操个什么心?”弋明宣向来对那群宫妃捩眼,现在自然乐得帮弋鸿宣说好话。
弋鸿宣眼角微扬,真笑了,却不忘应有的提醒:“怎生这番回话?她毕竟是太后!”
太后又怎么了?这皇宫大内看似锦绣,实则藏污纳垢。除了打小一心一意爱护自己的六哥,他没一个喜欢,没一个信任的。弋明宣有片刻愀然不乐,但眼珠儿一转,立时回嗔作喜,扯了弋鸿宣的手臂道:“知道了知道了,我这不马上跑来知会一声吗,以后她真耐不住了叫你去问话,你可别怨小弟我不讲意气。”
手臂被摇得生疼,也由着他,一刮面前挺直的小鼻梁,弋鸿宣笑吟吟道:“知道你最讲义气,今日留下来陪六哥用晚膳吧。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弋明宣却没了声响,待弋鸿宣去看,才慢慢开口:“一月零十三天。”忽然跪下,将头靠在弋鸿宣腿上,双手紧抱住他腰间,话声渐落,终至几不可闻:“我们已一月零十三天没一起用膳了。””
霎时认真的语气,让弋鸿宣听了微愣。他知道,打自己登基以来,每日政事繁忙,少有时间相陪。原以为小弟并不在意,可现时听这寂寥伤怀的话,借着夕阳细细打量,只见他向来不识愁滋味的天真双眸,不知何时,竟也染上一层复杂落寞的色彩,眉间稚气尽脱,唯玉貌珊珊。这模样,早非当年那个没了母妃,孤苦无依的小孩子了。这番蜕变源于何时,自己这当兄长的,居然未察觉半点。心下不禁默然。
两人静拥片刻,弋明宣想到什么,一抬头,脸上不复适才的可怜样,又回了惯常的嘻笑之姿:“六哥可是在为什么事烦恼?”
“朝堂上的琐事,就是繁琐些。”弋鸿宣用尽量轻松的语气回答。
“六哥骗人,六哥跟明宣说过要爱惜纸墨,若不是发火,断不会乱扔的!”弋明宣眼中闪着清明。
弋鸿宣有半刻意外,待会意过来,心里不免升起几分感动:“为难你还记得。”
“六哥,其实我还有一事要跟你说。”弋明宣拉拉弋鸿宣的衣角道。
“说吧。”弋鸿宣对自己的这个弟弟向来是好耐性,所以并未表现出不耐的样子。
“今年我们可不可以不去冥域涧?”良久,弋明宣终于鼓足勇气颤颤道。
弋鸿宣的脸上顿时闪过不悦和一丝缥缈得几不可闻的杀气:“不行。”
弋明宣倒也知道自己的六哥在这件事上从没有周旋的余地,便识趣地退到一旁不再作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