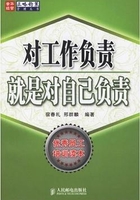莘菲气呼呼地走出才刚坐的小花圃,迎面碰上正笑嘻嘻走回来的书儿和篆儿,二人见莘菲满脸通红,急步走出,便问道:“姑娘这是怎么了?怎么一头汗呢?”
莘菲也不答,带着书儿、篆儿径自回府了。
回到韩府,见了母亲韩张氏,便矮下身子伏在韩张氏的膝头,半晌没有抬起头来。韩张氏大惊,“这是怎么了?好好的,不是跟随端淑公主前去别苑避暑了吗,怎么就这般模样了呢?”
莘菲还伏在母亲膝上没有说话,韩张氏便怒目问向书儿、篆儿,“你们俩不是跟着伺候的吗?姑娘为何这样啊?”
书儿、篆儿也不明所以,只得跪下身子,“奴婢也不知道啊,回侯府时,姑娘还好好的呢。”
莘菲此时才抬起头来,满脸都是泪水,“母亲,不关她们的事。是女儿自己心里头难受。”
韩张氏听言也流泪道,“我的儿,委屈你了。娘知道要你在侯府里讨生活是为难你了。谁家的女儿不是娇养在深闺的,只苦了你,为了我这把老骨头,哎。”说完也是止不住地拿帕子拭泪。
莘菲赶紧擦干自己脸上的泪,“娘这是说什么呢,是女儿不孝,惹娘伤心了。其实女儿没受什么委屈,公主待女儿很好,那侯府里的人也都忌惮着,对女儿也不错,只是女儿想着在侯府里伴读终不是长久之计,还是得想法子有咱们自己的进项才是。”
韩张氏听得此言,方止住伤心,也叹道:“娘又何尝不知呢,只是你爹的病和丧事几乎耗尽了咱们的存银,要置办些田产、商铺什么的也恐手头不济啊。”韩张氏擤了擤鼻子,“且咱们孤女寡母的,就算有些田产、商铺什么的,又交与何人打理呢?”
莘菲听言,扶着书儿的手站起身来,端了茶杯递给韩张氏,“母亲也不必太过忧虑,依女儿看,也不是全无可能。这些日子,府里的束修还有老太夫人的赏赐和宫里公主的赏赐,都折成现银的话,咱们手里也已有了二百两的银子了,女儿想着先托人打听着,看有没有合适的铺子,先盘个下来,至于打理,咱们也可雇个妥当的掌柜,女儿也可照看一二。”
韩张氏道,“这倒也是可行,只是侯府里的差事你不打算接着做了吗?”
莘菲的眼前顿时浮现出周士昭那副高高在上冷漠的眼神,心里便一阵恼怒,“是,女儿孤身一人在侯府,还是有着许多不便的,能辞了最好。”
韩张氏叹了口气,“你自己看着办吧,千万别太委屈了自己。”
莘菲又与韩张氏说了会话,陪着用了午膳,便回房歇着了。
打定了主意,第二日,莘菲一早就起来,照例带着书儿、篆儿做了遍广播体操,用了早膳,便来到了侯府。
到了庆安堂外,莘菲整了整衣服,也整理下思路,便着红菱去通报,说要求见老太夫人。
一会老太夫人遣人说传莘菲进去,莘菲便进了庆安堂的厅中,老太夫人刚用完早膳,正由荣嬷嬷扶着在厅里的前廊下逗鹦鹉玩呢,莘菲上前给老太夫人行了礼,“给老太夫人请安了。老太夫人的气色真好。”
老太夫人转过身来,示意旁边的小丫头们扶起莘菲,“韩丫头真真会说话,我这把老骨头气色还好,都是你们不嫌我老了讨人厌,哄我开心呢。”
莘菲笑道:“老太夫人当真是气色好呢,莘菲惯不会哄人的。”
老太夫人也笑了,“前几日,你随公主去了别苑,妙姐儿便天天来烦我,说等不及的要见到韩先生,以后再有这样的事,你便带了她去吧,省得来闹我,闹得我头疼。”
莘菲道:“妙姐儿聪慧得很,莘菲只在一旁伴读,也觉得假以时日,妙姐儿必是样样都在众人之上呢。”
老太夫人听言也说,“韩丫头教的好。也尽心,他日出阁我必奉上厚厚的添箱礼。”
莘菲听得脸便滚烫起来,“老太夫人笑话莘菲了。”
一旁立着的丫鬟、嬷嬷也都笑了起来。
莘菲见状,便欲转移话题,“老太夫人,莘菲今日是想求老太夫人赏个恩典。”
老太夫人说道,“你说说看,莫不是要我给你作个媒什么的吧?”老太夫人说完,众人撑不住又笑了一回。
等众人笑得差不多了,莘菲才正色跪下,叩了头,说道,“莘菲感激老太夫人,让莘菲给妙姐儿伴读,才能全莘菲的孝道!莘菲给老太夫人叩头了。”顿了顿,又说道:“莘菲的母亲自从父亲过世后,身体便一直不大好,莘菲不能在床头侍疾,实在是心里有愧。近日天气炎热,暑气重,母亲身体更是不好,因此莘菲求老太夫人宽恕莘菲不能再给妙姐儿伴读之罪。”
老太夫人听得莘菲的话,命身旁的荣嬷嬷扶起莘菲,红了眼圈道,“也是苦了你了。也难为你,一个女儿家家的,唉。既如此,你当然是以孝道为重,但实也不必辞馆,不妨考虑几日吧。”
莘菲见此,也只好谢了老太夫人,退出了厅堂,才走出门口,便看见一身暗青色锦袍的周士昭站在门口,莘菲福了礼便退下了。
走出庆安堂,莘菲便带着书儿、篆儿去往春华居,刚到春华居月洞门外,便被周士昭档住了,莘菲皱眉道:“侯爷这是何意?”
周士昭冷冷看向跟在莘菲身后的书儿、篆儿,书儿、篆儿被他看得直发毛,只得退后了几步。
周士昭看着莘菲,“怎么了,知道自己不胜伴读教导妙姐儿之职,便欲逃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