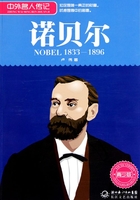1931年4月,志摩的母亲病逝,享年58岁。继祖母之后,又一个疼爱他的人去了,尚未来得及报答她的养育之恩,便再也看不见她慈祥含着爱意的目光了。
母亲,那还只是前天
我完全是你的,你唯一的儿;
你那时是我思想与关切的中心:
太阳在天上,你在我心里;
每回你病了,妈妈,如其医生们说病重。
我就忍不住背着你哭。
心想着世界的末日就快来了;
……
但是,妈,亲爱的,让我今天明白的招认
对父母的爱,孝,不是爱的全部;
那是不够的;迟早有一天。
这“爱人”化的儿子会得不自主的
移转他那思想与关切的中心。
从他骨肉的来源。
到那唯一的灵魂。
他如今发现这是上帝的旨意
应得与他自己的融合成一体——
自今以后——
不必担心,亲爱的母亲,不必愁
你唯一的孩儿会得在情感上远着你们——
啊不,你正应得欢喜,妈妈呀!
因为他,你的儿,从今起能爱。
是的,能用双倍的力量来爱你。
他的忠心只是比先前益发的集中了;
因为他,你的孩儿,已经寻着了快乐。
身体与灵魂。
并且初次觉着这世界还是值得一住的。
他从没有这样想过。
人生也不是过分的刻薄——
他这来真的得着了他应有的名分。
因此他在感激与欢喜中竟想。
赞美人生与宇宙了!
……
——《给母亲》
志摩对母亲怀着深厚的母子之情,母亲的离世,志摩心存愧疚。父母与小曼不和,感情的天平,他最终移向了后者,未能尽孝子之道。母亲晚年病重,一心期盼儿子在身边,但是因了陆小曼的关系,她只能生生忍着与儿子分离不得相见的苦楚,以致到死也难平一颗郁郁之心。
志摩赶回徐家,彼时陆小曼在上海,向他表明欲参加葬礼的心愿,但是徐父不肯。他满心盼望的是另一个媳妇张幼仪前来送终,而不是不予承认的陆小曼。这使得志摩的处境更加雪上加霜。郁积许久的怨忿终于一骨脑儿爆发出来,与父亲争执一番之后,他在信中写:
我家欺你,即是欺我:这是事实。我不能护我的爱妻,且不能护我自己:我也懊懑得无话可说。再加不公道的来源,即是自家的父亲,我那晚挺撞了几句,他便到灵前去放声大哭。外厅上朋友都进来劝不住,好容易上了床,还是唉声叹气的不睡。我自从那晚起,脸上即显得极分明,人人看得出。除非人家叫我,才回话……
我这份家,我已经一无依恋。父亲爱幼仪,自有她去孝顺,再用不到我。这次拒绝你,便是间接离绝我,我们非得出这口气……眉眉,你看,我的难才是难。以前我何尝不是夹在父母与妻子中间做难人,但我总想拉拢,感情要紧。有时在父母面上你不很用心,我也有些难过。但这一次你的心肠和态度是十分真纯而且坦白,这错我完全派在父亲一边。只是说来说去,碍于母丧,立时总不能发作。目前没有别的,只能再忍……
——《爱眉小札·书信》1931.4.27硖石
可以想象得出,志摩为了小曼与父亲间的关系僵持到何种程度。丧期过后,他动身回京,又开始以往的拮据奔波生涯。
1931年伊始,六个月之内他往来京沪两地共八次,情书更是一封接一封地发出。许是身处异地的相思与无奈,加之小曼不如以往那般热情与依赖,他便将满腹不得纾解的情思全数宣泄于纸上,以期得到她的回应。这时候的志摩,与其说是一个苦等妻子回音不得的丈夫,不如说是一头扎进“爱情”的软巢再也出不来的飞鸟。他的灵魂被束缚住了,风雨飘摇的世界看不见崭新的日出,连心都冻得发瑟。
你又犯老毛病了,不写信。现在北京上海间有飞机信,当天可到。我离家已一星期,你如何一字未来,你难道不知道我出门人无时不惦着家念着你吗……你难道我走了一点也不想我?现在弄到我和你在一起倒是例外,你一天就是吃,从起身到上床,到合眼,就是吃。也许你想芒果或是想外国白果倒要比想老爷更亲热更急。老爷是一只牛,他的唯一用处是做工赚钱,也有些可怜:牛这两星期不但要上课还得补课,夜晚又不得睡,心里也不舒泰。天时再一坏,竟是一肚子的灰了!太太,你恶心字儿都不肯寄一个来?
——《爱眉小札·书信》1931.5.12北京
我近来也颇爱孩子。有伶俐相的,我真爱。我们自家不知到哪天有那福气,做爸妈抱孩子的福气。听其自然是不成的,我们都得想法,我不知你肯不肯。我想你如果肯为孩子牺牲一些,努力戒了烟,省得下来的是大烟里。哪怕孩子长成到某种程度,你再吃。你想我们要有,也真是时候了。现在阿欢已完全与我不相干的了。至少我们女儿也得有一个,不是?这你也得想想。
——《爱眉小札·书信》1931.6.14北京
说到你学画,你实在应得到北京来才是正理。一个故宫就够你长年揣摹。眼界不高,腕下是不能有神的。凭你的聪明,决不是临摹就算完毕事。就说在上海,你也得想法去多看佳品。手固然要勤,脑子也得常转动,才能有趣味发生。说回来,你恋土重迁是真的。不过你一定要坚持的话,我当然也只能顺从你;但我既然决在北大做教授,上海现时的排场我实在担负不起……
我已在上海迁就了这多年,再下去实在太危险,所以不得不猛省。我是无法勉强你的;我要你来,你不肯来,我有什么法想?明知勉强的事是不彻底的;所以看情形,恐怕只能各是其是。只是你不来,我全部收入,管上海家尚虑不足。自己一人在此,决无希望独立门户。
——《爱眉小札·书信》1931.6.25北京
无论是企盼小曼来京与他团聚,还是希望将来二人共同孕育新生命,志摩可谓是低声下气地在恳求了。读到这里,肯定有不少人要为志摩抱不平了,最痴情也不过如此,陆小曼为何身在福中不知福呢?
爱情由萌芽、开花再到结果,需要一个悄然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的起初,因着两个人对爱抱有极大的幻想与热情,当浓情蜜意渗透至心扉时,它是真的入了心。而一旦它开出甜蜜的花来,这朵花要维持一定的花期,但不等于说它永远开得旺盛不败。它总会有萎谢的一日。这一日,并非世界末日,不是说,花谢了,爱情就死了。而是说,恋爱过了高潮进入相对平缓的阶段,这个阶段正是恋人结为夫妻过了最初的蜜月期后一段平淡的日子。
志摩永远是天真烂漫的人,在他的心目中,婚姻与恋爱无异,甚至更甚于恋爱。但这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试问世上有几个徐志摩呢?又有几人能够明白他的心?
陆小曼大概想,我是爱你没错,但我永远成不了你。换言之,我是我自己,我不可能完全按照你的想法处世、生活。当初,陆小曼因着她的个性与无畏与志摩恋爱、成婚,而今,她同样因着那独一份的个性与无畏做她认为对的事,过她认为应该过的生活。我爱你,但我没必要迁就你。
这就是陆小曼。你若爱她,应该爱她的全部,包括她的缺点。当志摩看到了小曼的缺点,并努力按照他的想法要将这些缺点抹去时,陆小曼便不再是那个高人一等、我行我素的陆小曼了。也许志摩的死,成全了两个人最美的爱情童话,否则,以她的性格,以志摩追求完美主义的理想,两个至爱的人很有可能成为一对怨偶,分又分不开,恨又恨不得……爱,更加爱得辛苦。
1931年10月29日,这是《爱眉小札》里志摩的最后一封信,将它完整摘录如下:
至爱妻眉:
今天是九月十九日,你二十八年前出世的日子,我不在家中,不能与你对饮一杯蜜酒,为你庆祝安康。这几日秋风凄冷,秋月光明,更使游子思念家庭。又因为归思已动,更觉百无聊赖,独自惆怅。遥想闺中,当亦同此情景。今天洵美等来否?也许他们不知道,还是每天似的,只有瑞午一人陪着你吞吐烟霞。
眉爱,你知我是怎样的想念你!你信上什么“恐怕成病”的话,说得闪烁,使我不安。终究你这一月来身体有否见佳?如果我在家你不得休养,我出外你仍不得休养,那不是难了吗?前天和奚若谈起生活,为之相对生愁。但他与我同意,现在只有再试试,你同我来北平住一时,看是如何。你的身体当然宜北不宜南!
爱,你何以如此固执,忍心和我分离两地?上半年来去频频,又遭大故,倒还不觉得如何。这次可不同,如果我现在不回,到年假尚有两个多月。虽然光阴易逝,但我们恩爱夫妻,是否有此分离之必要?眉,你到哪天才肯听从我的主张?我一人在此,处处觉得不合式;你又不肯来,我又为责任所羁,这真是难死人也!
百里那里,我未回信,因为等少蝶来信,再作计较。竞武如果虚张声势,结果反使我们原有交易不得着落,他们两造,都无所谓;我这千载难逢的一次外快又遭打击,这我可不能甘休!竞武现在何处,你得把这情形老实告诉他才是。
你送兴业五百元是哪一天?请即告我。因为我二十以前共送六百元付帐,银行二十三来信,尚欠四百元,连本月房租共欠五百有余。如果你那五百元是在二十三以后,那便还好,否则我又该着急得不了了!请速告我。
车怎样了?绝对不能再养的了!
大雨家贝当路那块地立即要出卖,他要我们给他想法。他想要五万两,此事瑞午有去路否?请立即回信,如瑞午无甚把握,我即另函别人设法。事成我要二厘五的一半。如有人要,最高出价多少,立即来信,卖否由大雨决定。
明天我叫图南汇给你二百元家用(十一月份),但千万不可到手就宽,我们的穷运还没有到底;自己再不小心,更不堪设想。我如有不花钱飞机坐,立即回去。不管生意成否。
我真是想你,想极了。
摩吻
十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