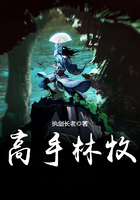司徒文跟着莫金走到树根下,那里本来挤满了人,不过前头开路的几个人似乎说了好些话,顺便亮了亮腰间的刀剑,便让那几个人走开,空出了一个老大的位置让身后的一众同伴坐下。
司徒文看架势,还是一路以来的老规矩,他独自一人坐在中心,其他的十二个壮汉背对着他、面朝外面的团团坐下,看似围着他,实际上防外人比防他还要严谨些,一个中年人刚刚走过来准备打声招呼,却不料被莫金冷酷的眼神生生吓走。
见司徒文这伙人这般大得气派,相似某个高门大户的纨绔弟子出门巡游,边上的那些赶路人也客气了不少。
这些赶路人大多是宁清府人,也有更远处的生意人,五湖四海的闯荡,见识倒都有,如今聚在一起,都天南海北的乱侃起来,其中不乏一些神仙鬼怪之类的话题,很是让司徒文听得心动,只不过他被严密的保护也不能踏出这个圈子,只得竖着耳朵当个听墙角的。
莫金等人待了一会儿确定周围没甚么要紧的人物,纷纷松了一口气,拿出一些吃食往嘴里塞,还依照规矩将最好的肉脯、干粮分给了司徒文。
司徒文正好肚饿,接过吃食就旁若无人的大吃大嚼,这也是一路上养成的习惯。司徒文吃了一些东西下肚,又休息了许久,身体也缓和了许多,继续津津有味的充当看客和听客。
约莫过了三、四个时辰,雨势终于渐渐缓下来,也有一些人继续上路了。司徒文估摸着时辰也已经是傍晚要入夜的十分,今天无论如何也赶不到宁清府了,而且他的马也瘸了,靠着步行更加迟缓。眼看树下的人渐渐稀少,司徒文心中叹了一口气,今晚得露宿街头了。
这时,远处又旋风般卷来十几匹马。这十几匹马上的人都是身穿黑衣,胯下黑马,如同一个个黑夜涌出的魔神一样,腰上的铁刀雪亮,十几匹马狂奔的势头,整个地面都隆隆的震颤起来。
这种威势,司徒文也是第二次见到,第一次当然是跟着莫金这伙人在官道上疾驰。
十几匹马到了伞状大树前,马上的黑衣汉子都拉住了缰绳,马匹仰天长嘶,或是原地打转,暴躁的践踏着泥水。树下歇息的人顿时全部停住嘴,大气都不敢出,更有胆小的不住后退。
昏暗的天色下,那十几匹马上的黑衣汉子冷冷的扫射着树下的人,空气凝固得像胶水一样,司徒文看不清他们的神色,只觉得一双双盯过来的眼睛都发着光,让李乾想到山林里的狼。
司徒文面前的那个胖子莫金倒是平静,见那些黑衣人目光射来,咧了咧嘴,其他的从人不约而同的把手放在了腰畔。那些黑衣汉子中领头两人低头嘀咕了几句,一甩马鞭。十几匹马没有停留,又席卷而去,眨眼间就消失在远处。
树下歇息的路人才一个个喘着大气,仿佛避过一劫,挣扎到岸上的溺水人。莫金还是沉静的看着那远去的黑衣背景,低声道:“这些人都是绿林道上的好汉,打家劫舍,杀人放火跟吃饭喝水一样,我等在这露宿,恐怕不得安生?”
旁边的一个汉子伸长脖子低声回应道:“老大,这伙子人看来也没甚么了不起的,要是惹了我们,宰了便是,怕什么?”
莫金瞄了一眼身后的司徒文,低声训斥道:“我们也不是真的绑匪,怎能随随便便就喊打喊杀,而且公子还在此处,若是闹大了,没得让人发现,你我可不好回去交差。”
旁边的汉子顿时哑口无言,只得腌了吧唧的缩回了脖子,默不作声。这两人自以为说话低沉无比,应该没人能够听得到,却不妨司徒文为了听墙角,正把真气凝聚双耳,因此听了个正着。
司徒文心中盘算着,晚上在这里过夜没有热水、热茶,也没有热被子、热饭,很是有些不舒服,不如跟着前方的那个盐贩子抄小路到一处偏僻的客栈投宿。
虽说那个客栈主要招待一些没什么钱的走南闯北的小商小贩,肯定不如城中的大客栈条件好,不过总算是处遮风挡雨的所在,不比淋雨强的多,只是怎么说呢?总不能告诉莫胖子,我可以听到十几丈远的对话吧,那以后的日子还过不过了!
正当司徒文筹谋怎么想个说辞将自家知晓的消息传达给莫金的时候,一把可爱的、响亮的声音从十几丈外传了过来。“这位兄弟,你可是有近路,怎不早说,我们一起走吧,这天色,一起走也安全点。”树下的有人听到附近盐贩子的话,有几个性急的就站起来嚷道。
“我草上飞在宁清府贩盐十几年,也算薄有名声,各位信得过我,就一起上路。”
“原来是盐商,失敬失敬!”这些人一听草上飞的身份,都纷纷恭敬起来。连一些本来还坐在那里无动于衷的路人听后也纷纷动心,盐商,向来要和官府关系密切,拿到盐铁司郎中的批条才能做得,那可不是普通人能做的买卖。
莫金本是正儿八经的官府中人,自然知晓盐铁司与盐商的勾当,也听过有关盐商的行事,这些人多半是一方大豪,不会轻易触犯律法,除非是贩运私盐的时候被官兵围攻,否则也是规规矩矩做人,又见众人都来应和,也把最后一丝疑虑放下。
晃悠悠的站起来朝花当拜了一拜:“大当家的,我们是远方的客商,前去宁清府进货,如今天色已晚,我等在外地多有不便,不知大当家的是否方便指点我们,倘若过了这一遭,我家主人还有丰厚议程相送。”
“客气什么,哈哈哈!我草上飞最是喜欢结交朋友,有客商不远千里而来,这可是我们宁清府的荣光呀!都跟我走吧!”草上飞拍了拍自家的双掌,豪爽的大笑。
草上飞看见莫金一行十三人,有十二批好马,一匹瘸马,心中本来疑惑这伙子强人怎么不打马狂奔,原来是有个人的马腿瘸了,跑不动。当下就叫人将运货的麻袋都重新填装了一下,在平板车上空出一个一人坐的位置,司徒文又是一番感激。
草上飞一共有六辆平板车,每辆车上堆二三十个麻袋,刚才重新填装货物的时候,麻袋打开,里面都是白花花的盐粒。
这让周围的人都红了眼,东海郡每年要向外地出口大批的海盐,这六车百八十袋盐,卖出去可就是天文数字。
特别是南方少盐,寻常人家每年弄个十几斤粗盐就了不得了,看这麻袋里盐粒的精细度,怕是一些官府特供的精盐,这种盐粒一斤起码二两上好的纹银,还是有价无市。
这六车盐怕是不下两万两白银,这等富贵,周围这些赶脚商人们哪有不眼红的道理。可眼红归眼红,草上飞手下也有二十来号赶脚车夫,个个都身强体壮,这大冷天里赤膊搭背,只是大声吆喝,烧刀子当白水来喝,一看就是些好汉子,可没有人敢动小心思。
强买强卖的心思不敢起,别的心思却是有的,树下这些赶脚商人哪个不是精滑之辈,都和草上飞套起近乎,自然是想收些私盐,自家到外面去买。
他们手里有的是路子,平价能搞到些上好的精盐,转手从黑市里就能翻几倍的价钱,也不用多,这上百袋精盐,匀他们一袋,转手就能赚上百两雪花花的银子,何乐而不为。
草上飞看上去也挺和气。论身家,他一个盐商,这里所有卒贩加起来也比不上他,这些人来套近乎他都是笑脸相迎,谈到私盐不说行也不说不行。众人看他掉胃口,心里的热切更急了。当下草上飞上路,树下的人几乎都跟了上来,也有三四十号人,车马牛也有几十匹,浩浩荡荡的走。
草上飞掏出一个铁烟斗,眯着眼睛,点上烟,坐在一辆牛车的辕上,和众人只是说笑,走了没多久,叉进一条小路。小路更加崎岖,十分窄小,边上又是山包树林,前方一片黑洞洞,平常这些卒贩怎敢走这样的夜路,不过现在仗着人多,又热闹,也没觉得怎样。
司徒文坐在牛板车上,随着车子摇摇晃晃,迷迷糊糊,似睡非睡。随着夜色渐深,车队里开始还热闹的声音也渐渐平静。众人也都疲倦了,也没有多余的力气说话。山野里漆黑处偶尔会响起一两声老鸹的惨烈叫声,催命似的紧起,让人毛骨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