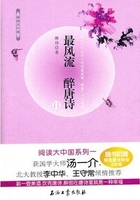骆烈抚摸铁链,对亲手的杰作满意的不得了。大爷似的拍拍生父后脑勺,阴阴笑道:“很好!”抹着药膏的小白脸看上去毛骨悚然,冰冷寒气从脚底心直逼上窜、窜遍全身。冷!真冷!真他奶奶的冷!
路青配合他的阴冷,双手抓住链尾急抖,软软的链子瞬间变成竖硬铁棍,“砰嚓”一声沉响,混合着内力笔直插入地面,没入的长度约半米。为防止苍狼醒后挣脱,他还特地从怀里摸出只墨绿色瓷瓶,拔塞,瓶内翠绿液体围着链子浇一圈。“呲啦、呲啦”一阵急音,仿佛硫酸销响。绿烟冒过,铁链与地面融为一体,坚不可催。
骆晶晶不叫了,抱头瞪着铁链呆若木鸡,一尊美人惊愕的雕像就这样轻而易举完成。
做罢,路青收起小瓶,拍拍手道:“我得赶紧准备准备别的,确保万无一失。”说罢,屁颠屁颠跑了。
房内只剩母子二人,骆晶晶僵硬的转动脖子,呆愣的瞅着儿子颤抖嗓音道:“烈儿……你这么做又要无家可归了……”事已至此,铐都铐了再说解已不可能,况且儿子的态度又无比坚决。天……脑中浮现出苍狼醒后的惊天地、泣鬼神模样,“狼堡”……她能不能晕?她能不能睡了不再醒?她太想如此了……
“怕什么,这次有他陪着,无家可归我也认了!”语毕,二次拍上苍狼后脑勺。流浪算什么,有爹在身边的日子太渴求。
苍狼趴在桌上睡得像头死猪,被折腾半天也没见有个反应。
受惊过度的骆晶晶此时才察觉出异样,拉儿子入怀不安道:“他为什么不醒?”
“醒?”骆烈扬起左眉,看向苍狼幽幽森森的笑了。“路青在他筷子上抹了药,他能一觉睡到天亮。”
骆晶晶身形一晃,头昏目眩。抹药……不亏为路青,笑眯眯煞是无害,却阴人于无形!
“时候不早了,你歇息吧。”骆烈将她推上床,转身。
“烈儿!”骆晶晶哪有心睡,一只被拴的大野狼就趴在桌上,况且明儿个一早又要……
拍拍她的手,骆烈意味深长的道了句:“跟你想的不一样,看着就好。”拨开她的手,像只斗胜的孔雀般骄傲离去。
瞪着阂起的房门,瞪着睡去一塌糊涂的苍狼,骆晶晶双眼一翻,晕撅。
在她倒床的下一刻,烛火“突、突”急燃扑腾,几下后“扑”果断熄灭,应映着房内的气氛与诡异之事。
翌日清晨,红日驱走黑夜,将昏蒙的天空擦划出金色暖调。蓝天、白云逐渐清晰入目,万物经过一夜的休整重新复苏。
鸟儿枝头喳叫,花草树木迎阳。两只喜鹊拍打着翅膀落于房前那颗高大笔直的荫荫绿树上鸣叫嬉戏,画面喜庆和谐。
房内,骆晶晶眨动长卷睫毛张开眼眸,醒来的她头胀痛,眼酸涩,全身都不舒服。转头,看向圆桌,苍狼未醒。惆怅攀涌心头,这一刻,真希望他永远都不要醒来,不要醒来面对侮辱的真实。
“嗯……”趴着的苍狼从鼻孔中溢出低哑低吟,醒了,缓缓撑起身子。随鹰目张开、视野扩大,看清自己竟趴在桌上打起盹。“啧……”手抚额,头痛、晕晕沉沉。为令头脑清晰,下意识甩头,头一甩立即引得铁链“哗棱、哗棱”作响。
在铁链碰击脆响的同时,房外嬉戏于枝头的喜鹊突然遭受到乌鸦群袭。“啊……啊……”乌鸦的丧音鸣散了喜庆和谐,换上阴诲黑暗。
“嘎嘎、喳喳。”喜鹊不敌群袭,不敢反抗、不敢停留,拍打翅膀仓皇而逃,逃走时落下两根黑白相间的恐慌羽毛。
骆晶晶浑身一震,险些被过大的鸟鸣穿破耳膜。身缩,缩缩缩,缩进墙角,直勾勾瞅着视线下调的苍狼。
颈上冰冷坠感及“哗棱、哗棱”作响的链音均令苍狼面色大变,先前睡意一扫而空,当目光接触到胸前铁链时大脑走过一秒钟空白。紧接着,单手抚颈,一只铁套不知何时套上他脖子。摸一摸,拽一拽,套得真他妈牢固。“吼……”狮吼顿起,一脚踹翻桌子,桌翻、帐薄通通摔地,有的倒扣、有的翻页洒落。“骆晶晶,这他妈是怎么回事?”愤怒的他指着哆哆嗦嗦的人儿嘶吼,鹰目转瞬冲血,嘴呲,尖牙暴显,冷光掠闪。
“的、的、的”骆晶晶上下牙不停打颤,揪着棉被挡在身前怕怕的一会儿摇头、一会儿点头,额滚冷汗,一滴滴流过美颜。
“你别给我摇头点头,说,怎么回事?”苍狼大吼,揪着铁链甩甩甩,“哐啷、哐啷、哗棱、哗棱!”链子与地面摔击声震得人心脏砰跳、耳膜鼓动。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烈……列儿……路青……”骆晶晶在牙齿的拼命打架下恐慌吐出犯罪者的名字。
听罢,苍狼呆愣当场,比石化还要硬上三分。大脑雪白一片,骆烈?路青?一个是他儿子、一个是他最信任的总管,二人竟合起伙把他给拴了?而且还拴在脖子上!妈了个腿子!绝饶不了他们……“吼吼吼……”森吼,响彻天地,房顶掀飞,“嗖”窜入云霄。
骆晶晶仰头望,瞅着没了影的房顶傻语:“哇……好高……”
傻货还说高,房顶飞了就不会再回来受气,光个房子没顶,看晚上怎么过。
“吼吼……嗷……”吼着吼着苍狼弱势,后半音狼嘨哽在咽喉里,只因他太愤怒,忘记链子另一端与地面坚固镇守,以置于冲到距离极限被硬硬勒住脖子。“咳咳咳……咳咳咳……”镣铐刚好抵住喉结,差点没勒死他,急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