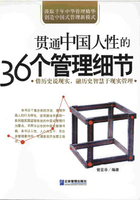为什么偏偏是我。
霓裳起初要我帮她答到的时候我断然拒绝:“中文系沈霓裳一开口,别说答到,哪怕是考6级作弊,全校3/4的男生也会前赴后继地帮你。”
美女如霓裳,很多事不用自己亲自做,只要懒懒地撒一撒娇,该有的,便都会有。
但她摇摇头,语气轻轻怯怯似委屈:“子歌,你知道的,我只喜欢他。”
一时我也受感染,便接了这活。
我叹口气,拿过笔记继续写。
霓裳只顾看她细细描绘的法式指甲,却没头脑地冒一句:“子歌,昨晚,他回来了。”
没写完的方程式孤零零地戛然而止,我偏头看霓裳,她认真的表情不像在说谎,双目便突然泛起无可救药的悲哀。
你,像我的梦境中一样,果然回来了。
可你告诉霓裳,却独独不肯和我说。
在遇见你之前霓裳曾说:“这世界,子歌你,是我最在乎的人。”
可之后就变成了你。你是落在我和霓裳心尖的一颗刺,逐渐长成茂密的荆棘,把我们的亲密无间,隔成心有芥蒂。
“但他呆C城的时间不长,他总是跑来跑去。”霓裳凄婉无助的表情和语调都很到位,让人一时分不清真伪。
但我其实想笑,霓裳,霓裳,他骗了你。
在梦中我记得,我奋力拨开人群奔向你,我们相遇,约好周六在咖啡厅见面,叙旧,但只有我和你。
霓裳,霓裳,他骗了你。他不会走。他为了我而骗你。
霓裳忧伤地在我旁边,而我却满心欢喜。
本来哪怕友谊万万岁,但终究还是抵不过爱情大过天。
我和霓裳,即是无话不谈的蜜友,即是争锋相对的情敌。
为你。
课后大喇叭里便开始放校园广播,dj是播音系的陆单生,栏目叫“秘境”。他放着周杰伦的《七里香》。他说,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温暖,那种植物有干净惹眼的白色,以及随风飘散的芬芳。
我听到缱绻温存的声线,反反复复地纠缠一句:“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恰如其分。
而霓裳却蹙起眉,因为陆单生说:“这首歌,是点给中文系的沈霓裳。”
霓裳众多追随者当中最出名的一个,因为每天利用职权点首或温暖甜美或委婉哀伤的情歌给霓裳,风雨无阻。
你看,霓裳烟视媚行目光流转,人尚在心却冷不丁便寻觅到别处。不像我,一心一意只有你,梦境里翻来覆去都是你。你的眉眼,单薄到一穿即破的地步。你的语调永远短但字字珠玑。你喜欢蹙眉因为你总在捕捉飞溅的灵感。你你你。
见到陆单生是因为我写很多随笔,闲着索性拿给广播室读。
那日是他接待我,翻阅过后他目光赞许地说:“写得很好。”
“我知道。”我丝毫不曾谦虚。
我的文字极佳,是因为你。你写了很多的字,散文小说诗歌随笔杂文,刊登在大小报纸和杂志上,出过小说出过诗集出过散文集。
我一路追随你,自然沾染上你的气息。
曾在很多个睡不着的夜里执着一盏灯,读那些翻译得生涩暗晦的外国小说,《呼啸山庄》,《红白黑》,《茶花女》,《简.奥斯汀》,也读唐诗和宋词的精选集。起初是因为想拿借书来接近你,看你也好和你聊天也罢,只有我和你,没有霓裳。怎么会有霓裳呢,她只喜欢翻那些《瑞丽》,《昕薇》,《vogue》,看衣服搭配看化妆技巧。可没想,我陷进文字的美好里,它像森林深处的沼泽,深不可测却盛开着甜蜜的花朵。
如此看来,我比霓裳内心更贴合你。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君是你。
满目山河空望远,不愿怜恤眼前人。人是我。
我要出淤泥而不染,才能配得上遥远的你,清凉含蓄,美得不似在人间的你。
我还在回忆,陆单生打断我:“你可不可以帮忙约下霓裳。”
“约会?”我单刀直入地问。
“不是,是接受采访。”
“哦?”我好奇起来。霓裳那样功课门门只在及格边缘的学生,有什么好采访的。
“刚好我们推出个新栏目,每期介绍一位学校的风云人物。第一期,我想要霓裳上。”
我又沮丧起来,竟忘记霓裳有副好皮囊,漂亮得令人心惊。她站在你身边,郎才女貌如此匹配。
一比一,还是分不出胜负。
采访那天我陪着霓裳到广播室,要问的问题事先打印在A4纸上,我探头看一眼不痛不痒,没什么问题。
我在外面等霓裳,透过窗子,渐渐看见她的面孔难掩悲伤之情,双眼蓄满泪水,仿佛再眨一下,就会扑簌而落。
我冲进去,把霓裳拉起来掩在怀里。她仍旧那么瘦,嶙峋骨割伤了我的忧愁。她哭得断断续续:“子歌,他问我到底喜欢的是谁,可是子歌,我说不出口。”
我知道,我知道霓裳说不出口,因为关于你只埋藏在我们心底,不肯拿出来与他人分享。因为怕一旦说出口你便不再是我们的唯一。
他人都够不着你的衣裳,你也不需要迁就,你本来就该站在云端拨下云头俯身而视,唇畔带着冷漠的笑。
霓裳的脸颊上还挂着泪,却凝视我:“子歌,他要走了,你要不要跟我去送他。”
我的内心泛起细密的疼痛。难道是真的,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今天要走,我们还约好了周六见面。
我掩住脸,不想再去猜测被谎言击中的人究竟是谁。
你不会骗我。你怎么愿意骗我。
是霓裳在撒谎吧。她总是这样,拿谎言让我猜忌怀疑,让我伤心难过。她就小计谋得逞。
别忘了,我们是情敌。
陆单生坐回去,放王力宏的《Finally》,男子忧伤隐忍的声线在凉薄空气里流淌,让我双眼潮湿,整颗心开始缓慢而用力地痛起来。他唱:“无论发生什么事,我永远都会和你在一起。”
可是现在的你,是和霓裳在一起吗?你会不会问她,子歌呢,子歌为什么没有来?你会不会问哪怕一句也好,哪怕轻描淡写也好。会不会。
突然就无限悲伤起来。答案无比清楚地在心中浮现,你们不会谈到我,就像我和你在一起时,也绝口不提霓裳的。
可是霓裳,她哪里抵得上我。如果你在当面,我决要问个清楚,你到底喜欢谁,如果是我我便欢喜,如果是霓裳,或者,或者其他女生,我便要执着追问你到底喜欢她哪个动作,喜欢她哪个表情,喜欢她怎样叫你怎样拥抱你,喜欢她穿怎样的衣裳给你看。
此时陆单生把转椅转过来,双手环抱在胸前,认真地观察我脸上起伏的表情,问出一句毫不相干的话来打断我的思绪:“子歌,你有没有和他联系上。”
我愣住:“他?”
陆单生一双漆黑的眼,吐字异常清晰:“顾尘寰。”
“你怎么不问霓裳?”我拔高声线地质问,多少带着点敌意,明明是霓裳的追随者。
“她不肯说。”他倒不以为然。
的确,他刚才追问过霓裳可霓裳只是哭。
“我只是想确认他的存在。”陆单生神色始终沉着自如,“我想帮她。”
“帮什么?你难道没有听见,霓裳说去送他了。”我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
“我在网上查过,作家顾尘寰一年前因车祸而去世了。”陆单生的目光深不可测,缓慢地说,“你们怎么会不知道?”
我疲惫地闭上眼。他怎么会知道他怎么会知道,你是在我须臾记忆中勃勃生长的不朽,你骨骼分明的十指时常涌动出让人由衷赞叹的惊奇,你是流浪的诗人行走的歌者,你怎么会死。他们都不知你只是热爱自由。世上,唯有死亡才能永远获得自由。
只有我和霓裳知道,他们都被你骗了。你只是假装不在人世而已。
有葡萄藤的院落,那日你搬来。我与霓裳彼时皆年少,热衷电视节目,汽水,捉迷藏,后来再添上你。
去窗下巴望你,是霓裳的计谋。
那时我还心系比我先一步领走流浪猫咪的小男生。霓裳便说:“他家也有猫。”
我不知为何素日腼腆胆小的霓裳,却大胆起来。
直到见到你我才明白个中缘由。
你在书桌前练毛笔,衣袖翻过几折褪到肘下,霓裳附到我耳旁:“子歌,你说他是不是很好看。”
那时我只目不转睛地看你,听到霓裳冷不丁的话像猜中心思般转过头,两只挨得近脑袋碰到一起,霓裳吃痛地“哎哟”一声。
你明知是小女生,却嘴里不饶人地蹁跹过来:“阿生,你乱嚷什么?”
到窗口,你俯身下来拿左手撑着窗沿,看着两个无处躲藏的小女生假装惊讶:“诶,不是阿生啊。”
霓裳的脸颊还挂着不可避免的泪水,她气得鼓鼓:“我当然不是那该死的猫。”
面对霓裳的凌厉姿态,你竟在我们面前笑起来,眼神里收纳下她蛮横时的模样。
你后来才把目光递给我,眼角浮起连绵的笑意。我还未及将台词想好,你就先声夺人扣下我的心弦来:“哦是你。”
你看我的眼神,就像在雨天看你怀里的阿生一样,温柔,溺满湖水。我瞳孔流光暗转,心事陡生。
你很安静时常不说话,练字看书听广播,我便帮你喂阿生。霓裳是有些粗线条贪玩的女生,直到长大之后才开始逐渐变得纤细,但那时却愿意在你旁边收拢羽翼,安安静静,一边看你的侧脸一边翻杂志昏昏欲睡。
我知道,是因为爱情。
那时,我始终不似活泼的霓裳,因为漂亮所以有足够的自信,可以直来直去地面对你。于是,我从未开口。
虽然我和霓裳各怀心事,但平日却始终是三人行。一同看画展,去吃饭,散步,逛百货,谈诗论曲,哪怕不喜欢,但谁也不愿意被抛弃。
那晚你取一笔稿费回来,请吃火锅。三个人围着一个小锅,青菜,豆腐,莴笋,蟹肉捧,鱼丸,土豆。霓裳与你并坐,你们一同为我夹菜,一同举杯和我碰杯,一同对我笑意盈盈。像,你们是一对,而我,是多余。
想此,便举箸不定食不知味,一时心碎。
回去的路上霓裳也挽住你走在前面。偶尔你回过头来看生怕我丢失,却很快被唧唧咋咋的霓裳唤回头去。
旁边有人兜售拍立得,十元一张。霓裳兴致勃勃地要拍,你答好,和她拍完转过头央求我:“子歌,要不要和我拍一张作纪念?”
我记得四月的夜晚,你的发间杂着几瓣纯白的樱花。月光透过树叶的浅黄残骸流泻在石板上,一路蔓延。空气中有股暧昧的味道,甜而略苦。
霓裳微笑着等我拒绝。
周围静得可以听到花瓣脱离花萼凋零的细碎声音,轻柔的花瓣顺着风柔软地撞击着我的唇。
我竟说好,但只拍下我和你在街灯下的影子。
拉长的影子,轻微的重叠,像靠在一起的普通情侣,亲密无间如此登对。
你去过很多地方,每到一处便寄漂亮的明信片回来。下雪的北京,美得心惊的墨脱湖,丽江,桂林,乌镇水乡,西安,鼓浪屿,牡丹江,去的时光长长短短,但留在C城不过寥寥几日。不够,连触碰你眉毛抒写你嘴角勾勒你侧脸的时间都不够。
那次你又要离开,初略一算一季光阴,霓裳看挽留不住你便猛拍桌子,豪迈地说:“老板,来一打啤酒!”
如果喝醉就可以不用面对事实,那我只愿沉醉不愿醒。
等我醒来时看见霓裳立在我床前,双手环抱居高临下,语气极淡:“尘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