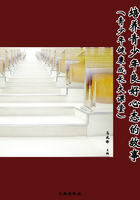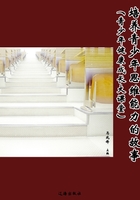“小心那盏灯。”阿曼乐把劳拉扶上雪橇时,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雪橇座位上铺了好几条马毡,马毡的尾端,毛茸茸的野牛皮袍子下面,点着一盏油灯,它把劳拉放脚的地方烤得暖暖的。
当他们经过布鲁斯特家时,劳拉跑进屋子去,布鲁斯特先生说:“你们该不是打算在这么冷的天气里坐雪橇回家吧?”
“我们要回去。”劳拉回答说。她不想浪费时间,她跑进卧室,把另外一件法兰绒衬裙穿在身上,把另外一双羊毛长袜套在脚上。她把厚厚的黑色羊毛围巾折成两层,在脸上围了两圈,把兜帽一起包裹进去,然后把长长的围巾尾端缠绕在脖子上。在围巾外面她又再围上头巾,把头巾的两端交叉着塞到胸前,最后把外套扣子全部都扣起来。她一口气跑了出去,赶紧坐上雪橇。
布鲁斯特先生站在那里劝说他们。“你们两个傻瓜,别干这种傻事!”他说,“这太危险了,让他留在这里过夜吧。”他对劳拉说。
“你觉得呢,最好还是别冒险了吧?”阿曼乐问她。
“你要不要回去呢?”劳拉问。
“我得回去,我要照料我的牲口。”他说。
“那我也回去。”她说。
王子和淑女迅速冲进狂风中。冷风穿透了劳拉身上裹着的羊毛衣物,冷得她喘不过气来。她深深地埋着头,可是冷风仍然迎面扑了过来,就像冰水一样,从她的脸颊和胸前流淌过去。她咬紧牙关,免得牙齿打战。
马儿精神抖擞,一路飞驰,它们的马蹄踏在坚硬的雪地上,就像打鼓一样咚咚作响,雪橇铃声也应和着蹄声,欢快地响着。劳拉感到很庆幸,以这辆雪橇的速度,很快就会到家,他们过不了多久就要摆脱这冰天雪地了。可是,不久,马匹的速度慢了下来,劳拉开始有些担心了。到后来,它们更慢了,只能蹒跚而行,劳拉心想也许是阿曼乐想让它们歇一歇,也许马儿迎着刺骨的寒风不能跑得太急了。
当阿曼乐把马儿勒住让它们停下来,跳下雪橇时,劳拉感到非常意外。她隔着黑色的围巾,模糊地看到阿曼乐向马匹走去,走到它们低着的马头前,说:“等一下,淑女。”他边说边用戴着手套的手放在王子的鼻子上。过了一会儿,他刮了一下,然后把手拿开了。王子把头高昂了起来,把雪橇铃铛摇得叮当响。阿曼乐很快在淑女的鼻子上也做了同样的动作,淑女顿时也昂起了头。阿曼乐然后又上了雪橇,把自己裹在袍子里,马儿又开始飞奔起来。
劳拉捂住嘴的围巾上满是冰霜,开口说话会很不舒服的,所以她什么也没有说,不过她很想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阿曼乐的毛皮帽子拉得很低,盖在了眉毛上面,围巾把他眼睛以下的部分全部包裹了起来。他呼出的热气在围巾边缘结成了厚厚一层白霜。他用一只手驾着雪橇,另一只手放在袍子下面取暖,然后两只手不断地交换着,免得双手被冻僵了。
马儿的步伐又慢了下来,阿曼乐又走下雪橇,把手放在它们的鼻子上。当他走回雪橇时,劳拉问他:“怎么啦?”
他说:“它们呼出的气结成了冰,把鼻子封起来了,这样它们就没法呼吸。我必须把冰弄掉。”
他们没再说什么。劳拉想起了那个漫长的冬季,在十月暴风雪里,牛群的鼻子被冰冻住了,完全无法呼吸,要不是爸把牛鼻子上的冰敲掉的话,那些牛早就死了。
寒风从野牛皮袍子外面侵袭进来,穿透过劳拉的羊毛外套和羊毛衣裙,再渗入她的法兰绒衬裙,以及套在法兰绒连身内衣裤管外面的两层羊毛长袜里。尽管那盏油灯散发出了一些热气,可是劳拉的双脚和双腿感觉越来越冷。她咬紧牙关,连下巴都咬疼了,太阳穴隐隐有些刺痛。
阿曼乐伸手过去,把野牛皮袍子拉高了一些,塞在她的手肘后面。
“冷吗?”他问。
“不冷。”劳拉清楚地回答说。她的牙齿一直在颤抖,所以她只能说出这两个字来。她没有说实话,不过阿曼乐明白了她的意思,她是说还没有冷到无法忍受的地步。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一直向前走。劳拉知道,他也冻坏了。
阿曼乐又把马儿勒停,走下雪橇,在寒风中去把马鼻子上的冰块弄掉。接着铃铛声又欢快地响了起来。可是现在,在劳拉听起来,这铃声与无情的狂风一样,听上去让人觉得有些残酷。虽然围巾遮住了她的眼睛,她还是能看到阳光正照在雪白的草原上,显得十分刺眼。
阿曼乐回到了雪橇里。
“还好吗?”他问劳拉。
“好。”她回答说。
“每跑上三公里,我就得停一下,它们不能坚持得太久。”他解释道。
劳拉听到这话,心一直往下沉。也就是说他们才走十公里左右,还有十公里才能到家。他们迎着凛冽的寒风继续前进。虽然劳拉在尽力坚持,可浑身还是抖个不停。她把双膝夹得紧紧的,双腿还是止不住地在颤抖。那盏放在脚下的油灯好像一点儿热量也没有了。她的太阳穴剧痛起来,肚子也一阵阵地剧痛,好像要缩成一个硬结。
似乎又过了很久,马儿才又一次慢下来,阿曼乐又让它们停了下来。不久铃声又响起来,先是王子的,然后是淑女的。阿曼乐行动笨拙地爬进雪橇里。
“你还好吗?”他问。
“好。”劳拉回答说。
她渐渐适应了寒冷,没有刚才那么难受了。但是肚子还是疼得缩成一团,不过也没有刚才那么厉害了。风声、铃声和雪橇底板滑过雪地的声音,混合在一起,融汇成一种单调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悦耳。当阿曼乐又跳下雪橇去刮马鼻子上的冰块时,劳拉能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仿佛是在梦里一样。
“还好吗?”阿曼乐问她。她点点头,没有出声。说话太费劲了。
“劳拉!”他抓住她的肩膀,轻轻地摇晃了一下。她却感觉被摇晃痛了,这种疼痛感再次让她感受到了寒冷。“你困得想睡觉了吗?”
“有一点儿。”劳拉回答说。
“不要睡!你听见了吗?”
“我不会睡的。”她说。她知道他的意思。如果在这么冷的天气里睡着了,那就会被冻死的。
马儿又停了一次。阿曼乐问:“现在好些了吗?”
“好。”她说。阿曼乐下去处理了马鼻子上的冰块,回来后说:“现在已经不远了。”
她知道阿曼乐想让她答话,于是她说:“太好了。”
虽然她一直努力地睁大眼睛,可是绵绵不断的睡意却像海水一样,一波又一波地袭来。她摇晃着头,大口大口地吸入冷空气,极力挣扎着,让自己保持清醒,可是又一波睡意袭来,接着又是一波。经常是当她疲惫得准备放弃挣扎时,阿曼乐的声音会及时地来挽救她。她总能听见阿曼乐问:“还好吗?”
“好。”她说。她因此会清醒一会儿,能听见雪橇的铃声,也能感觉到风在呼呼地吹。接着,又一波睡意袭过来。
“我们到啦!”她听见他说。
“好的。”她回答说。猛然间她意识到,他们已经到了家的后门前了。这里的风还算温和,第二大街对面的建筑物把风势挡掉了一部分。阿曼乐掀开袍子,她尽力想从雪橇里走出来,可是她浑身都僵硬了,完全站不起来。
后门猛地打开了,妈冲出来紧紧抱着她,惊叫起来:“我的天啊!你冻僵了吗?”
“我担心她太冷了!”阿曼乐说。
“赶快把马赶到牲口棚去,别让它们冻坏了,”爸说,“我们会照顾她的。”
雪橇铃声渐渐远去,爸和妈搀着劳拉的手臂,她摇摇晃晃地走进厨房。
“把她鞋子脱掉,卡琳。”妈说着,解下劳拉的围巾和羊毛兜帽。劳拉呼出的气结成了冰,把她的围巾和兜帽冻在了一起,解开它们的时候还是连在一起的。“你的脸色还很红润,”妈松了一口气,“真是谢天谢地,脸还没有冻成苍白色。”
“我只是有点儿麻木。”劳拉说。她的脚没有冻僵,不过她几乎感觉不到爸的手在揉搓它们。现在坐在温暖的屋子里,她从头到脚都开始颤抖起来,牙齿也颤抖得咯咯直响。她紧挨着火炉坐下,喝着妈为她熬制的姜汤,可是她仍然没有暖和起来。
她挨冻的时间太长了,从这天早上一起床就开始挨冻。在布鲁斯特家的厨房里,她坐的位子离火炉最远,而离窗户最近。吃完早餐后,她踩着积雪,走了很远的路去学校,一路上迎面刮着寒风,而且风还在她的裙子下打着旋儿。学校的小屋里寒气逼人,她却在那儿坚持了漫长的一天,最后又在寒风中赶了很远的路回家来。不过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好埋怨的,因为她现在终于到家啦。
“你这样做太冒险了,劳拉,”爸严肃地说,“我起初并不知道怀德要来接你,直到他出发后我才知道。不过我想他一定会在布鲁斯特家留宿的。当这个发疯的家伙出发时,气温已经是-40℃了,很快连温度计都给冻住了。后来气温还在不断下降,现在没有谁知道到底有多冷。”
“结果很好就什么都好,爸。”劳拉回答说,颤抖着笑起来。
她觉得自己好像永远也暖和不起来了。不过,能在充满快乐气氛的厨房里吃晚餐,然后躺在自己的床上睡个安稳觉,这种感觉真是太美妙啦。等她一觉醒来时,发现天气已经好转了。吃饭的时候,爸说气温是-20℃。最冷的时候已经迅速过去了。
这个礼拜天的早晨,当劳拉在教堂里时,她想到自己把自己弄得这么紧张这么不安,就觉得自己这样做太愚蠢了。只剩下两个礼拜她就可以回家住了。
礼拜天下午,当阿曼乐赶着雪橇送她回布鲁斯特家的时候,她向阿曼乐表示了感激,感谢他那天接她回家。
“不用谢,”阿曼乐说,“你知道我会来接你的。”
“呃,不,我不知道。”她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啦?”他问道,“你以为,在你非常想家的时候,我却要硬下心来把你留在布鲁斯特家?仅仅因为这事对我没有什么好处,我就撒手不管了?难道我是这样的人吗?”
“呃,我……”劳拉无言以对。事实上,她从来没有好好想过,阿曼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她仅仅知道,他比自己大得多,他是个拓荒者。
“跟你说实话吧,”他说,“那天要不要冒险跑一趟,我其实也是左右为难。整个礼拜里,我都计划好要驾车来接你的,但是当我看到温度计时,我几乎就决定不来了。”
“为什么还是来了呢?”劳拉问。
“嗯,当我驾着雪橇出门时,在福勒的五金店前停了一下,我进去看了看温度计。温度计的水银柱已经降到了底,-40℃了,而且风越来越冷。就在这个时候,凯普·格兰从我旁边经过。他看到我在那儿,知道我准备到布鲁斯特家来接你,正在看温度计。于是他也看了看温度计,你知道他对我做出了一副什么样的笑脸吗?当他往福勒五金店的里屋走去时,他扭头对我说,‘上帝讨厌懦夫’。”
“于是你就来了,因为你受不了这种激将法?”劳拉问。
“不,那不是激将法,”阿曼乐说,“我只是觉得,他说得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