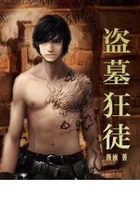医院里,劳勇坐在病床上,怜爱地看着熟睡中的孩子:臂如藕节,小脸蛋胖嘟嘟的,虽然多日的无食无水使之苍白,但还是掩盖不住曾经的白皙红润……劳勇看着,忽然,像想起了什么,冲出病房,疯狂地奔向那片废墟……
到了,劳勇的眼前是机械轰鸣的忙碌场景:十几部挖掘机正在清理废墟,一辆辆拖拉机跑来跑去……劳勇要寻找的那间小门卫房——孩子的家,根本无法分辨出具体的位置。劳勇的脑海里“嗡”的一声,蹲下身,双手插进浓密的头发,不停地抓搔,仿佛要将头皮抠下来,又用拳头不断地狠狠擂打着自己的额头:由于一时的疏忽,让自己的不幸又在这个孩子身上重演了!
劳勇的不幸发生在三十年前,那时候,劳勇和现在这个孩子一般大小,一场无情的地震摧毁了他的家,也夺去了他的父母。劳勇的父母也用和这孩子的父母同样的方法保护他。三十年来,多少个无眠的夜晚,劳勇努力想象着父母的样子,可是,任凭他绞尽脑汁,他的父母,连一丁点儿的影儿也不让他觅得——当年,哪怕是父母一张残旧的照片也没有留给他。
劳勇固执地认为,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捧着父母的照片入眠。本来,这种幸福,劳勇是能够为这孩子创造的,就在刚才移开楼板的时候,那孩子母亲的手里还捏着一张照片,是一家三口的合影。可是,由于当时只顾着救人,劳勇竟然忽视了那张照片。
现在想来,地震发生前,这对年轻的夫妇一定是正带着他们的孩子甜蜜地欣赏着照片……现在,照片在哪儿呢?
挖掘机慌乱地忙碌着,激起的灰尘弥漫了这片天。劳勇顾不上疲惫,虔诚地在那片废墟中搜寻着,双手刚刚凝结的伤口又一次鲜血淋漓……
东方的天空泛起了鱼肚白,寒星点点,晨风呜咽,机械的轰鸣声显得倍加疲惫。偶尔,几只劫后余生的老鼠的跑动声渲染着废墟中死一般的沉寂,空气中隐约弥漫起阵阵血腥味。劳勇却似一只饿狼,砖石搬了一块又一块,汗水、血水流下又干,干了又流。可那张照片,冷漠地不知躲藏到何处,丝毫也不理会他。
劳勇将最后的希望放在了殡仪馆。
殡仪馆里停放着一具具白布覆盖的尸体。虽然是冷冻间,但还是冻结不住丝丝尸臭。劳勇仍不听战友的劝阻,他睁大双眼,小心地揭开、盖上,再揭开一块块白布,捧起一具具女性尸体的手,又放下……劳勇不相信那张照片能从人间蒸发。
现在,只剩下火化间里的几具尸体了。劳勇挣脱战友的拉扯,快步走进火化间。
劳勇看见,一位火化工正将一具女尸缓缓地推向火化炉。他的眼睛开始模糊了,大叫一声,纵身扑向尸床……
手捧照片,一家三口向着劳勇绽放出灿烂的笑容。烈烈炉火里,劳勇看到那位年轻母亲的脸上似乎正渐渐生出淡淡而欣慰的笑。劳勇长长地吁了口气,他知道,那是来自天堂的笑容。(摘自《微型小说选刊》 张爱国/文)
标:母亲的汇款单
按照惯例,每个月池野都要给母亲安藤纪子汇去高额的生活费。虽然池野的工作日渐有了起色,但除去供养母亲的那一部分后,所得只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开支。
家住日本松浦川的池野靠画插画为生,经过几年的辛苦打拼,终于在松浦川安了家,并娶了妻子青木雪子。母亲仍然一个人住在老家。池野几次要求把母亲接过来同住,都被拒绝了。
母亲脾气不好,年龄越大,对子女越加严厉,因此池野和妻子在母亲面前一直恭敬小心,事事让着她。
虽然雪子善良懂事,但因受了委屈,有时也在池野面前哭诉母亲的不是:“我知道,自从你父亲离开后,她独自将你抚养长大,吃了不少苦,你现在每个月给她生活费我都可以理解,但她对人太苛刻了,每次她来这边,总是训斥我,说我这也没弄好,那也没做好……”
“唉,妈妈年纪大了,你多包容一下吧。”
无可奈何的池野只能从中调解劝慰。对于母亲,他心里总是怯怯的,因为不论他多么成功或失败,她总是用一种恶毒的语气辱骂他。
又是几年过去了,雪子开始在池野面前不停唠叨,特别是当她知道了池野每个月汇给母亲的钱已是最开始的五倍之多——相当于池野每个月辛苦作画版税的一半。因为随着池野的事业越做越好,母亲一次次地坚决要求提高汇款数目。有一次池野因为手头的事情太多,迟迟没有给母亲汇款,许久不联系的纪子突然打来电话,开口便骂:“你想把我饿死在乡下吗?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子,娶了媳妇就忘了娘……”已是中年人的池野恨不得马上挂掉电话,再也不理这个蛮横刁钻的老妇人,但他不敢在母亲面前表现出任何的不满,只得连连赔罪,答应马上汇款。
那时候,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孩子,雪子第一次为母亲的事和池野吵架:“你以前给她的钱,养老绰绰有余,而我们呢?就连出去看场电影都要仔细盘算。她成天就想着把你的钱都吸干,怎么不替你考虑考虑?就算不为你,我们总得为孩子的将来打算吧?”
池野心里赞同雪子的话,但却不敢多发一言。
“你必须和她谈谈,不能再像这样给她汇款了……你再这样,我就带着孩子离开你!”
雪子的抱怨加上本身对母亲的不满,使得池野继续给母亲生活费的念头开始动摇了。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几次之后,池野最终同意和雪子一起,到母亲那里和她谈判。
好久没来,母亲家里还是池野搬出去时的老样子,简简单单几样家具,房间显得冷清空旷。
简单行礼和寒暄之后,雪子推了推池野,催促他说出来意,但池野仍难以开口,最后还是雪子开门见山地说:“妈妈,我们不能再继续给您汇款了,因为孩子,家里有了不小的负担,希望您能够理解。”
纪子沉吟了一会儿,把头偏到一边:“池野,你也是真心这样认为的吗?”
“妈,我……”池野因为激动脸涨得通红。
令人难堪的沉默持续了许久,纪子突然站起身独自回到房间里,将他们俩晾在一边。看着母亲日渐伛偻的背影,池野心中百味杂陈。
在池野印象里,母亲一直少有笑脸,他不小心做错事了,母亲拿起烧饭的锅铲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好打。后来池野逃学和社会上的小青年鬼混,一次次从家里偷钱出去买酒喝,只要被母亲发现了,也是立即揪着耳朵,边打边扯回家,每次都让池野的同伴笑话不已……终于有一天,池野发誓再也不回家了,这才彻底逃脱了母亲的打骂。
回到松浦川后,池野还是背着雪子给母亲按期汇款。“就当是还债吧,以前的饭钱住宿费什么的。”池野喃喃地自语道。
但母子之间的鸿沟,就像汇款的数目,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深,他们的联系更少了。
一年过去了,母亲又打电话过来。看到熟悉的号码,池野猜测母亲又要催款了,因为正急着交稿,就没有接电话。到了晚上,电话铃声顽固地响起,池野叹一口气,接起电话,不料电话那头却是母亲生前唯一的好友由美子阿姨。她语气沉痛地告诉池野:她在接到纪子的电话之后匆匆赶去,纪子因为癌症晚期,现在已经昏迷不醒了。
池野大吃一惊,等赶到母亲床前时,她已经离开了人世。
怎么会这样?一旁的雪子仿佛松了口气,而池野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由美子阿姨递给池野一封简短的信和一本存折,说这是纪子临终前要她亲手转交给池野的。
“我知道你生性挥霍,又喜欢招待朋友。你每个月汇来的钱,我都帮你存在这本存折里。这是我最后能给你的。”
在信纸的一角,母亲潦草地画了几笔,那是母亲在世间留下的最后笔迹了。池野久久地看着这几行字,掩面大哭,跪地不起。
(摘自《知音·海外版》 多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