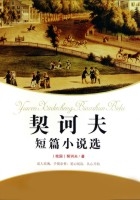然后,我分别敬各位先生女士一碗酒。尔后,就由吾儿媳陪你们喝酒、吃肉。因为鄙人负责了周遭六十里地的治安联保,山外在打日本强盗,山里近几年就蟊贼如蚁,匪盗猖獗。鄙人身为保长和治安联防队长,就自然不敢掉以轻心。”美仙见一碗淡绿色浓稠的蜂蜜酒举在面前,立即站起身来,端起碗,暗忖道:“我从没用碗喝过酒,三碗酒进肚,还不烂醉如泥?但克城先已说过,山里人,你不喝他敬的酒,就会说你瞧不起他,轻则嘲讽辱骂,重则拳脚相加和兵刃相见。我要行几百里的蛮荒之地,今日是头一家,若不喝下这三碗酒,实怕难过此关。”她见谭丛虓鼓着铜铃般的一双大眼睛直视着自己,那架势完全像粗犷的将军般咄咄逼人。未饮酒她便被他的气势吓得两腿像筛糠似的战栗着。她瞟了眼桌上的人,在松枝烛火下,都目光闪烁直视着她,时间不容许她再去多想下去。“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拼老命也要硬过这头一关。”只见她与谭丛虓两碗“啪”地一碰,一仰脖子,便把一碗酒咕噜咕噜地灌进嘴里。
美仙喝完刚放下土烧碗,就见谭丛虓又给她斟上了第二碗酒。她心里一喜,想道:“嗨,这个酒是甜蜜蜜的,酒味不浓烈,应该是酒劲不大的甜酒吧。”想着,她又端起第二碗酒,把头一仰,又哗啦一阵灌进喉咙里。她放下碗,笑着说:“谭老伯,小女子酒量有限,但老伯的一片心意我却盛情难却。此碗酒能不能让我的克城大哥代饮?”“不能,不能,万万不能!三小姐巾帼豪杰,岂能旁人代之。喝了这碗酒,老生便把你安全送过豆沙关!”说毕,他连连地摆手,那盛气凌人的架势丝毫没有同情和怜悯少女的护花之心。美仙推辞不过,谦让不了,又头一仰,将一大碗酒灌进了胃里。她还没有放下碗,谭丛虓立即带头鼓掌,并伸出大拇指,连连地夸赞着美仙的海量,够朋友,讲义气。今后就是上刀山下火海,只要有他谭某人在,一定效犬马之劳。美仙喝下这三大土碗的蜂蜜酒,又听谭老这么一说,心神顿时感到飘荡,她惺忪着醉眼,与谭丛虓一击掌,便说:“难得有你这么豪爽的大伯当护仙使者,过豆沙关,仙妹就全靠大伯你了。
”她一侧脸,对着张克城,说:“你还闷着干啥,既然大伯与小妹已结金兰之盟,生死之交,你还不赶快敬大伯三碗水酒,谢过大伯的真情与豪爽呀?”张克城立即拿过酒壶,端起满碗的酒,给谭丛虓斟满,豪言壮志地说:“我家小姐金枝玉叶,既然与你结拜了兄妹,这碗酒是我的祝贺酒,请老爷干了!”谭丛虓执拗不过,也只好一抹胡须,端起碗,豪爽地一饮而尽。克城再斟上第二碗,和颜地说:“我们初次与老爷相见,老爷便这么真心款待我们,请接受小弟一碗感谢酒。”谭丛虓将手一摆,说:“我已有言在先,小姐三碗,余者我敬一碗,我还没开始敬你,你就先下手来敬我,不妥,不妥。”克城用手将他的腕臂轻轻地按下去,固执地说:“古人说‘有来无往非礼也’,既然你已经敬了三小姐三碗,当然我们要回敬三碗啰。”谭丛虓性本豪爽,听张克城这么一说,也觉得在理,又嘴巴一张,将一土碗酒一倾而尽地喝进了肚子里。
张克城见谭丛虓经不住劝,又给各自的碗里斟满了酒,端起一碗递给他,用感激似的口吻说:“我们明天就要上路,老爷说要护送我们过豆沙关,我们预先喝碗分别酒,远去天涯海角,也好留个思念,这就叫它思念酒,请老爷喝下吧。”谭丛虓把碗往桌上一放,不满意地说:“今天才接风就说分别,不行,不行,先罚你一碗错话酒,我俩才能喝下这第三碗酒。”张克城见他说要喝下这第三碗酒,二话不说地接受了罚酒。喝完这碗,他立即斟上,与谭丛虓碰了碰碗,便各自闷无声响地喝干了这一大土碗的玉米酒。谭丛虓眨巴了一下半眯的醉眼,暗忖道:“不能小看这伙乳臭未干的人等,若再与他们拼干几碗,恐怕我也抵挡不住。这玉米蜂糖酒虽然入口甜淡,但它的后劲足,不知道的人都会被它的甜淡所迷惑,多贪几碗后都是败下阵来,与我跪地求饶。但今天这三人,未必会给我跪地求饶,任我宰割他们了。”他在心里笑了笑,便给菊花斟满了酒。菊花先是谦让,然后甜甜地颂扬了他几句,一仰头,眨眼间便是个碗底朝天。谭丛虓想就此饮毕好退出饭厅,哪知菊花却不依不饶,她拉住他的胳膊,定要一视同仁地干三碗。不然,她便无脸面在人世间行走。
他抵挡不住她软硬兼施的甜言蜜语,只好痛快地饮下了三碗。龚嫂见老人公已是豪言壮语,手舞足蹈,醉眼蒙眬,偏偏倒倒,就求饶似的对美仙干笑着说:“三小姐,算了吧,他晚上还有事,明天又要找人找马送你们。把剩下的酒都寄在谭家,今后来寨子再喝吧。”邵美仙给张克城一摆手,说:“听龚嫂的吧,今晚喝酒就到此为止,让大伯吃点儿菜好去办公事。”谭丛虓连连摆手,晃头晃脑地说:“你们请多吃菜,我有事,先退席了。”说完他左脚碰右脚,哼着《西厢记》里的曲子,高一脚矮一脚地向后院找“崔莺莺”去了。
美仙尝了些野菜便放下碗筷,克城和菊花美美实实地饱胀了一顿,为明天的上路储备了足够的营养。晚饭结束后,美仙出门便感到全身轻飘飘的。抬头一望,见天上的星星特别明亮,像是大屋顶上缀着的灯火,在向她眨闪着诡秘的眼睛。她想伸手去摘一颗星星下来放进怀里,她踮着脚双手向着天空,仿佛自己是在腾云驾雾一般。她哈哈地笑着,嘴里直嚷道:“我成仙了,我飘起来了。你们莫拉我,莫拉我。让我坐在弯弯的月亮里,骑着回家,回家……”张克城和任菊花见邵美仙真的醉了,忙扶她进了寝室。菊花给她洗了脸和脚,便扶着她上了床。很快,美仙就长睫轻覆地眯上双眼,喃喃地耳语似的睡着了。
一觉醒来,已是红日东升。太阳斜射过山垭,照在清涟的横江水面,波纹移动的山影,宛若一幅大师手笔的风景山水画。美仙痴痴地盯着江面,出神地感受着这里的粗犷与美丽。正在她遐思飞扬的时刻,龚嫂的一句话,打断了她畅游的神思。她回过头来,只见一个牧马人带着三匹烈马,来到她的面前。龚嫂说:“你们一人各骑一匹马,那只骡子驮你们的行李,由牦牛的表哥犍犊送你们到豆沙关。”刚说着,谭丛虓笑着,抱拳出来送行。美仙听着要骑马,再一看那几匹嘶鸣的老马,便急红了脸,直摆着手,说:“我骑不来马,我骑不来马。”龚嫂唤过骑在马上的犍犊,寡着脸对他说道:“你先下来,牵一匹温驯的牝马给三小姐,教她骑上去。学会了就上路——啊,三小姐,昨晚的住宿钱和今天租马的钱,只给二十个袁大头或孙大头光洋就行了,酒和饭是牦牛他爷爷请的。”美仙叫张克城付过了现洋,便让犍犊教她骑马。她刚走近那匹个头略小的稍带黑色的牝马,那马便扬鬃尥蹶子,不愿生人接近。
犍犊走近牝马,用手摩挲了一会儿马脸,并轻声说:“听话噢,不能奋蹄,跟着我走。”他扶美仙坐上鞍子,刚动了几步,那马便前蹄一跃,整个身子仿佛要站立起来,它嘶鸣一声,便把早已吓得胆裂的美仙摔下鞍辔。犍犊伸手从料袋里抓了把泡过的胡豆和豌豆,喂到它的嘴边,待它吃过后,便扬起手中的鞭子甩得山响,随后又扶着它整齐的颈鬃,怒吼似的说道:“再烈我打死你。好,乖乖地听话。”说过,他又扶美仙跨蹬上了马背。那马拗不过主人,只好乖乖地跟着犍犊,一颠一颠地走着。训练了几圈,犍犊将缰绳递给了美仙,并说了一番骑马的要领和掌握缰绳与自己两腿夹马的技巧,便让她自由地上马,骑着在江边来回地跑了几趟。张克城少年放牛时骑过不少骣骑,所以上马就能骑。任菊花上了一匹高大的骕骦马,她恶狠狠地吼了它几句,将鞭子一甩,那马便默不作声地听她使唤,真是“恶有恶克,善有善报”啊,马儿们只欺负从来没有骑过马的美仙。
美仙和克城三人,在马上抱拳与谭丛虓和龚嫂作过再见,便由犍犊引领着,嘚嘚嘚地穿街而过,很快,他们便走出杠祜寨大门,向着山峰巍峨的羊肠山道缓缓地前行而去。美仙觉得骑马新鲜好玩,她在马上仍然四顾观山望景,任由马儿跟着犍犊的马前行。菊花的马紧紧跟随美仙,她身后是驮行李的骡子,克城殿后。不知走过了多少山头,爬过了多少岩坎,美仙望山望得颈脖子酸痛。不望山时,在马背上几颠几簸,她似乎睡着了。在一个转弯的山嘴,牝马一扬身,美仙来不及抓住马缰,一个筋斗便翻身落马,哧哧地一阵滚溜,她被摔下了山岩。张克城正催骡子快行,蓦见前面的美仙落马,像滚石头一样的飞快地向山岩下滚去。他心头一惊,说时迟,那时快,他立即提住马缰绳,停住马下来,一个箭步窜上去,随着美仙滚落压伏的荆棘和草丛,哧溜一声窜到把美仙挂住的一蓬杂树前,他左手抓住树梢,右手一把拽住美仙的衣袂,俩人刹那间跌在了一起。
此时的美仙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全身不知是颤是抖还是疼,她紧闭着双眼忽然间感到有人已滚来抓到她的身子,她毫无意识地突然将两只胳膊紧紧地抱住滚过来的人,一股求生的欲望顿时催醒了她的意识,她睁开眼,恍惚只见是克城强壮的胳膊托住了她。她霎时流出了眼泪,一股股的冷汗陡地湿透了她贴身的衣衫。任菊花见美仙落马,也纵身从马背上跳下来,她还没来得及抓住邵美仙,张克城已一个箭步追着她滚溜下了山底。待她稍微明白过来,克城已在下边喊:“菊花,菊花,快叫犍犊放根绳子下来,我已抓住三小姐了。”张克城的喊声和美仙落马的滚动声,早已惊动了走在前边的犍犊。他向后一看,立即勒住马,飞身跳下马背,见落马人已滚向悬崖,悬崖下的江水哗哗地拍打冲击着山脚。他快步挤到菊花的前面,趴下身子向悬崖下看。忽地,他听见了一个男人喊递绳子的声音,他飞快地爬起身来,向自己骑的马跑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掏出褡裢袋里的棕麻搓成的绳索,拴上一个长条形圆石,往下一抛,绳子便滚向被树梢挂住的两人。
张克城见有绳子放下来,他两脚蹬着岩石稳住身体,抽出手来迅速将绳子拴住美仙的腰,他扣上结,望着头,拼命地向上面喊:“轻轻,轻轻上拉,我已经把三小姐捆住了。”上面的人听见喊声,立即将绳子一头拴在一棵树上,四只手不由分说地拽住了绳索,慢慢地将吓得昏死的美仙提上了岩坡。见美仙被拉上来了,菊花立即抱住了美仙的腰,把她抱到了山路旁的草坪上,解开绳子让她躺在草坪上。犍犊顾不上问候一句三小姐,飞也似的又来到岩边,他如法将绳子抛向谷底。张克城见又有绳子抛来,立即抓住拴在腰上,随着绳子的上提,慢慢地从岩石上爬了上来。任菊花见张克城上来了,满身是泥,西装外衣已被划破,颈项和脸部还有道道血痕,她立即拥着他痛哭了一阵。张克城牵挂着邵美仙的生命,很快松开任菊花,跪向草坪。见美仙裙衫多处被挂烂,手腕和颈脖几处有血迹,幸喜脸上只是青一块紫一块,没有划破的血迹。张克城俯下身,用手背去感受她的呼吸,忽见她身子一动,挂满泪痕的眼睛一眨一眨地慢慢睁开。张克城他们三个人立即拥抱在一起,撕心裂肺地痛哭了起来,哭声震动着山岩,在山间沉闷地回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