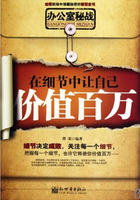青纱帐,红木床。
女子醒过来张开眼的一刹那,就有满头银发的男子握紧了她的手,忐忑不安地问道:“蜻蜓?”
她摇头:“蜻蜓?我是云溪,云溪。”
她于醒转过来之时瞬间就生了一颗鲜活的玲珑心。
她只要他对自己好。
到底他爱的是不是本来的自己,真正的自己,她不管。
风月无关。
英容无关。
一瞬间老了十年的胡亭寿继而惊喜地扶她起身,只是在低头的一刹那,他恍若因失去了十年的性命而双眼生花,将那枕边的玉石像看作云溪恬静温婉的模样。
但他浑然不觉,他只觉得自己比连白舒幸运。
他因为当药人,余下的性命也不多了。
但刚好,够十年。
便能与云溪同生共死。
不必忍受没有她而独活于世的痛楚。
遥记得儿时孝轩的话语,他说,莲蕊,你的眼中总有一片浮云,犹若翅翼。当时,他正替一只受伤的幼鸽取下绑裹伤口的布条,紧接着,莲蕊就听见那鸽子咕咕地叫了声,便扑拉着翅膀飞上了天。
她抬头,那云翳,若有若无地呈现在瞳中。
莲蕊在桂郡经营一爿花店,总有好心的花农怜她身世凄零,独给她留一份与众不同的应景之物。
或是一把红色的栀子,或是一把双生的芍药,或是隆冬季节,一枝绿萼的梅花。
众人爱她这一爿店铺的洁净素雅,常寻了借口来照顾她的生意,但无论何时,她都是安之若素,不动不喜。
穿月白色的衣衫,不多修饰,一些稀疏的藤萝、蔓草,围绕脖领与袖口,怯怯地生长着,像她自己,少言怯懦,只在孝轩来时才露出浅浅的笑颜。
“莲蕊,你猜我给你带了些什么?”他总爱把手背在身后,逗她说话。
“是,南记的艾叶粑粑?”她甜甜软软猜着,迎着门扇前那斜射进来的阳光,仿佛要从满室花香中嗅到艾叶的清新味儿。
“不是,不是。”他摆摆手,把手呈到她的面前,“是江南那边进来的决明子,可治眼疾。”那小小绿豆模样的种子在手掌上滚来滚去,发出沙沙的摩挲声。
莲蕊刚伸出来的手顿在半空中,久久忘记放下:“轩哥哥始终记得莲蕊的病,有劳了。”说完摸索着转过头去不看他,弯着身子侍弄花草。
孝轩立在当下,不知如何进退,他本是听了师父的教导,知道这小小的决明子是难得的治眼良药,忙不迭从医馆跑来,想给她一个惊喜,却不料她一贯看不出表情的瞳中蓦然蒙了一层灰,恍若铅凝。
其实,莲蕊这眼疾,并非娘胎里带来。
儿时从她家门前经过,她总会眨巴着一双带星的眸望着孝轩,有时候还会递一些好吃的给他,她爹娘也和善,并不管他的出身,常招呼他到自家玩耍。
然而,在郡里有着好名望的黄府在当年帝权变更时忽遭大变,产业易主,家人也悉数被判了斩立决,只剩下她因为年少无过被老仆收养。
一次游戏中,她为了拾他做的风筝,瞒着他爬上高高的桂树,单脚踏空,从树上跌落。待他终于寻得大夫时,才发现那双瞳蒙了一层白翳,像浮云,像翅翼。
便再也看不见,看不见他,和他身后的世界。
自那时孝轩就暗下了决心,一定要拜最好的眼科大夫为师,治好她的眼疾,还她一片光明与无碍。
“好啊孝轩,你和爹爹告假,原来是跑来这儿看小媳妇了。”花店前一个明艳的女子横叉着腰,语气热烈,明媚春光挂在脸上。
然后并不顾花店里的僵持气氛,笑嘻嘻地把手上提着的纸包放在柜上,“这次新进的药材中有好几味治疗眼疾的,我拣了带来。”同样身为女子,又是大夫的女儿,夏笙深知眼盲的痛楚,虽与莲蕊性格截然不同,却仍与她姐妹情深。
可这回莲蕊却隐没了往日的笑容,光影下眉睫颤颤,仔细看去,仿佛结了露珠。
“夏姐姐,谢谢你。”过了半会儿,莲蕊才从怔忡中醒转过来,摸索着抽出水桶里一枝鲜荷,“这枝荷,在乡下的荷塘里初绽,就送给姐姐吧。”
“哪里的话?你又和姐姐客气了。”夏笙伸手就去接那荷花,埋头深深地吸了一口,“真香。”
“多谢你。”
铺子里来了熟客,说是府里要准备小姐的婚事。孝轩和夏笙帮着打理生意,与莲蕊告别后结伴走在回医馆的路上,孝轩想着刚才多亏有夏笙解围,诚心地道了谢。
“哪里的话?”夏笙从小就在医馆长大,接触人多,从没有藏过心思,对于这中间的是非纠葛她多少知道,却并不深究,自然也不知晓二人心里情愫的纠缠,“哪天治好了莲蕊,你大婚之日多敬我几杯喜酒便是。”她拿着那一朵鲜荷,欢快地哼着小调,不以为意。
他看着她欢快的模样,心里郁积着忧愁也一扫而空,天那么蓝,莲蕊也总会有一天能和自己看见那天上飞过的白鸽。
莲蕊分外用力地用手指掐自己的皮肉。
分明知道孝轩心里念着挂着的就是自己,她却执念以为那不过是因为自己眼盲显得孤苦惹他同情罢了。
她躲在角落里整理鲜花,一不小心,手指蓦然碰到玫瑰的梗刺,忙不迭吮吸着破皮的手指,思绪却飘荡开来——想不到,时光如此之快,那常来的小姐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而若算起来,她比自己还小了两岁呢。
想着这些的时候,她闻到一股清香,那并不是花香,是墨香。她虽然盲了,但对小时候骑在父亲膝上看他翻阅那些红缎子要函时鼻尖轻嗅到的味儿,还是念念不忘。
若家没有亡,那么是否可以好好地和孝轩生活在一起?想到这,脸上芳菲便不禁兀自开放。
“姑娘可就是这花店的主人,莲蕊?”来人顿了顿,“在下韩朝玉,即将参加全国的丹青大赛,试题是‘奇葩’,我知道姑娘的花店里总有些新奇的货色,所以……”
他刚从京城回来,急寻作画的素材,知道桂郡尚有这样奇特的花店,便一路打听过来,知道这花店的主人双目失明,便远远地站定,深怕吓着了她。
“所以想来,借花入画?”她抬头迎向他,他这才注意到她不动颜色的瞳里也有闪亮的光彩,“正是。在下并不白看,定有重谢。”
“呵呵。”她忽生了难得的笑颜,“若先生丹青夺魁,不如在我这小店亲书一面匾额,就当是酬劳了。”
他这才注意到,那素净的门扇上并没有一块可识记的牌匾,但她那如莲花一般纯净的脸又是活生生一块招牌。
“好!”他把扇子猛地在手心里一敲,“那我明日就来?”
“嗯。”她点头算作应允,又折回自己的角落。
天气越发炎热起来。
这天天刚亮,韩朝玉便径直来了花店,未料时辰尚早,铺面还未开门。
要了一壶花茶,坐在临街的位子,慢悠悠等着。
未经意间,那门倏忽一开,白色裙衫露出一角,接着是整朵芙蓉绽放在天光下,他喝着茶,忙不迭闭了一口气——春光分明已过,这会儿却倏地盛开在那临阳大道的一角。
袅娜娉婷,芙蓉比不上她的高雅,牡丹又不及她的圣洁——这样的女子才是真正的奇葩。
他兴起,展开画纸,毫尖与宣纸细语低喃,不多时便是一幅国色天香:墨香晕染,一笔一划,皆是情意;樱唇瑶鼻,浅浅笑意,是盛开在尘世之外的奇葩,仿佛要吸进那摇曳的春光,肆意地绽放于天地之间。
也是他心中爱意的破土绽放。
锣鼓声响,喧嚣冲天,韩朝玉得到丹青大赛头魁的消息传遍了桂郡。
听说他独发奇想,应“奇葩“之题,却以一出尘女子入画,评审赞他别出心裁,便把这丹青头魁的称号给了他。
一个月前起身离开,而今衣锦还乡。
“莲蕊。”他立在花店外面定定地看着她,想着若是那双眸子被点亮,不知增添多少怜爱。
“韩公子,是你?”她听到声音,转过头来对他微笑,“丹青大赛夺得头魁,真是该好好恭喜!”似玩笑,又认真。
“莲蕊,此次我请了宫里善治眼疾的薛御医,只要他为你施个小手术,你的眼疾便能痊愈!”他一把上前抓住她的手,心想主考官大人不仅力排众议给他高分,还向他引荐了善治眼疾的薛御医,真是吉人天相,“到时候你便可看见这人间大好景色。”
她赧极,努力抽去被他抓住的手,发丝贴在额前,细汗冒出:“韩公子。”
他方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忙退后了两步:“对不住,失礼了。”
薛御医来看过莲蕊的眼睛,心里暗叹,这幼时本因外伤而造成脑内淤血压迫神经导致失明的眼睛伤口却奇怪,然而并不声张,只说不需金石针砭,只消用化瘀散将脑内淤血化开,同时以成药固本,期间最好有专人伺候,以保平安。
孝轩定还不知道韩朝玉请了御医为自己治疗眼疾的事吧?不然他肯定兴奋得几天几夜都睡不着。算来,他已是多时没来花店了,莲蕊知道他升了掌柜,忙得走不开,医馆的小伙计将药拿来,问起孝轩的近况,回答也是支支吾吾,只说掌柜的希望她好好服药。
不知他看见自己眼睛复明的样子会是怎样的表情呢?她似揣了只兔子忐忑不安,有着对手术失败的恐惧也有着隐隐的兴奋。
十多年了,她终于有机会再见他,仿佛憧憬着未来而自顾自地笑着,那样子竟有些痴傻。
“莲蕊,该吃药了。”温和的男声把她召唤回现实。
她遵医嘱,来到韩府小住,韩朝玉亲自喂她汤药,日夜不歇,极尽情意。她却思量弗多,一心只想着尽快好起来看见孝轩,几味重药,最是苦口,她也没有觉察出,还是朝玉体贴,替她剥了一颗蜜饯,小心塞到她嘴里,手触到她的颊,手不禁一颤,停在半空中。
她觉察出异样,也不道破:“许久不见孝轩了呢,不如韩公子替我去看看他?”
“这……”似无意,韩朝玉叹了一口气,“好,我这就去,你好好歇着吧。”他替她掖好被子,离开了。
迷迷糊糊中她听见丫鬟的嬉闹声——“啧啧,那夏家医馆的掌柜和小姐的婚事可办得真热闹,听说郡里受了医馆恩惠的穷人富户都携了礼去贺呢。”“是啊,那夏家医馆平素都行善,一对新人更登对得不得了……”
咯噔。
她们说的是孝轩和夏笙?
后面的话她已无心去听,顾不得身上只一件内衫便急冲冲地向医馆跌绊着跑去。
祝贺声、锣鼓声响彻在耳,她料不到那个心心念念的男子竟真的选了夏笙,恍惚中她仿佛看见新人着喜服拜堂的情形,那一行泪就噙在眼眶,落了下来,最后整个人再难支撑,瘫软下去。
远远的,有一道光看着她昏倒在医馆门口,一种复杂的情绪,自眼底渗出。
最后,决绝而不动声色。
莲蕊斜靠在床上,行尸走肉般地任凭薛御医施药,众人只盼她尽快好起来,能解少爷的相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