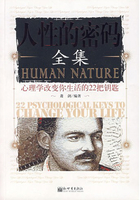旁人的神情旭祺全然不睬,只盯着柳先生细看。哎,他忠于父王,也料定曲玲珑会在紧要关头倾向父王,便做了推卒进河的恶人,然而父王……
只见他此刻静静凝神,瞳孔里映出曲玲珑坦荡身影,似有不忍,又不经意地与承王目光相碰,倏忽偏转开去。
【陆】
“先生,你当年喜欢的,是我母亲吧?”
皇朝上下面临抉择正值一片动荡时,柳隐州仍气定神闲地为旭祺授课,但旭祺哪里有心思,见窗外幽幽篁影摇曳,忽而发问。
柳隐州身形顿了顿:“世子何出此言?”
“母亲深爱父王,为何数年来一直待在南疆?而柳先生又为何在左臂暗系黑布以示哀悼?若说出于主仆情谊其实也无可非议,但先生却处处刁难曲姑姑,昨日更是将她推向刀尖浪口,你对父王忠心不二,我绝不相信你与顾丞相暗勾结而发难父王,那么,便只剩另一种可能——”
为何柳隐州明知曲玲珑在父王心中地位超然却敢顶撞?为何他一表人才却迟迟不娶妻?这一切的一切昨日尽在旭祺心中有了答案。
“你也是因此,才爱屋及乌,甘愿辅佐父王,以助他登上帝位吧?”
只是柳先生太过心狠,竟要以这种为爱而选择牺牲自己的方式让曲玲珑从父王的身边消失,又以看着心爱之人为自己牺牲却无法拒绝的方式让父王登上帝位。
柳隐州不置可否,只淡然道:“世子你还太小……”
【柒】
潜龙阁中,皇族、朝臣并列,贤王与承王的神色益发凝重,却都沉默。
这一刻的到来,对他们来说,仿佛既是一种命运的安排,也是一种尘埃落定般的解脱。
“曲姑姑,多加小心。”——
旭祺偶习术数,知道潜龙阁的暗格处藏有机关,一旦行错,便会引发暗箭流矢连珠迸发。他是真心希望玲珑能安然取下遗诏,并不管这遗诏会对他以后带来怎样的影响。
曲玲珑闻言顿足,轻绽开笑容,不知怎的,旭祺只隐隐觉得那笑容不详。
“嗖嗖——”风声掠过,无数弩箭连珠发射,从四面八方悉数射下。众人目不转睛看着,却都全部退出五丈之外:这固然是多年未见的稀奇事,身为人臣,当然也要以悠悠众目证明曲玲珑没有暗中耍心机。只是曲氏虽有秘技,她失忆毕竟已久,谁能担保没有差池?
“不好!”那轻盈身影一顿,似折了翅膀的蝶般陨落。一时间所有人都愣在当场——曲玲珑失手了!
“玲珑。”承王与贤王不约而同地冲上前去,也就在这一刻,埋伏在皇城各处伺机行事的将士听见二王共同的哀呼纷纷从外冲了进来,顷刻间剑拔弩张,吓得朝臣纷纷闪避。
“都退下!”二王共同挥退麾下将士——这是以防万一之策,如若遗诏中的储君名单不是自己,那么这一场消弭了十余年的争伐又将兴起。
只是,谁能料到,这双能起解秘辛的掌匙之手却再也抬不起来了?
“旭祺……”紧咬的唇间,一声低不可闻的呻吟,旭祺尚未反应过来,就被侍从牵到玲珑跟前。
她拼着最后一丝力气,牵过他的手,郑重交到承、贤二王交叠的手中。而那明争暗斗了许久的两个人一瞬不瞬地望着她,见她似隐隐噙了笑,终于一同将她眼角的泪光抹去。
亦为她阖上那闪亮的,双目。
【柒】
“看来陛下闲得很。”柳隐州踏雪而来,随手向空中急抄,抓得几只翩飞的竹蜻蜓,折断弃地,“兵乱之际竟有兴致在此侍弄木石之技。”
“先生不觉得这样萧索的冬日惶惶没有一丝生气么?”旭祺不似往常玩笑意味,一脸怅然:“听说景承太子年轻时也最喜木石技艺。”
“那陛下可曾想过硝烟弥漫处百姓的疾苦?”
——自曲玲珑于潜龙阁开锁失手后,承王被迎回东宫,复称景承太子,竟以干政罪名废了王妃顾氏。雷霆手段,极其迅速,连对南景虎视眈眈的几大邻国都不得不侧目。
而后过继侄儿旭祺,立其为帝,自己却云游四海远遁了踪影。朝臣虽腹诽,但至此,空置了多年的帝位终于后继有人,也就在众人期待南景复兴到来之时,兆兴二年,新帝胞弟旭柏拒受亲王称号及封邑,以靖远元帅原部二十万兵士起兵桂郡,易帜叛乱。
柳隐州此次前来,本欲以帝师身份劝诫他早日剿灭叛军,不料被他这样一发问,语气明显顿了顿:“不错。如今陛下也偏爱这丧志玩物。”
“是因为血脉相连吧。”旭祺拍了拍落在衣上的竹屑,饶有意味地直视着柳隐州,“当日先生不是问我如果遇到这般情境会如何选择么?我只当旭柏一时任性,与我这个兄长赌气罢了。况且——太皇太后也屈尊求我放过他。”
“太皇太后?”柳隐州不禁愕然。
【捌】
昭蔼二十年的事已经快要湮灭,旭祺只在陈旧的卷帙中见过当时的记载。
那一年发生的事太多太多,太子刺帝君于宫中,贤王在南疆战死,最后虽被证实俱是谣传——行刺帝君者最终被帝君身旁宫人刺伤,待矫健营捉拿时亦被发现是刺客易容,而贤王侥幸被当地百姓搭救,逃出生天。但彤书写就再难更改,银朱铁笔只得又新添引注。
而后,便是景霖帝猜忌钧仁欲盖弥彰,撤了他太子封号降为承王,重惩曲氏……
这一切的一切,看来不过恍似一场梦,未来得及等他分神,便被掌宫提醒太皇太后请他有事相商。
“那二妃四嫔我已选定,至于皇后人选……”太皇太后骆氏还未说完便听到旭祺一口应承:“但凭皇祖母定夺。”
他知道,无须他回答,骆氏心中已有人选,念及满朝名门姝艳中可登上这后位的,除了骆氏女子,还能有谁?
却听骆氏笑道:“如若这样,我便为你选娶长风郡曲氏之女,曲语彤。”晶指翩挥,懿旨已下。旭祺愕然,继而听骆氏道,“我年前回长风郡祭奠先祖时曾见过此女,真是觉着有些像她啊。”
旭祺心里莫名一痛,也无法猜测骆氏究竟要说些什么——她端坐于高堂上目光深邃,淡淡道:“曲氏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如今也该还他们一个清白了。”
那突兀的“委屈”与“清白”二词,让旭祺不禁呆了片刻。
见他错愕,骆氏倒似有些惊讶:“你不是将当年的史官都找到并询问了一遍么?我还以为你都知道了呢。”
那些真相太过骇人,连宁可杖毙也不愿更改自己笔下所写的史官多年后回忆起来都不禁微微颤抖——
“我本是先帝侍妾,当年他巡视北域时我已有月余身孕,却不料尚未等他平安归来,你那皇祖父就已控制宫中形势,先皇后为我腹中孩子着想,奋不顾身骑马夜奔三千里告知先帝后继有人,而后与他共担生死……”那些被保护而不能奋起斗争的痛楚在经历了皇朝的动荡之后弥久深重,骆氏想起先皇后临别时抓着她的手让她一定要保护好孩子时那种深切的期许,忽然黯然落下泪来,“多年来我忍辱负重,负上背弃先帝的骂名不过是想让仁儿安然度过余生,为先帝保留一丝血脉。”
旭祺听完,才悟到骆氏所指先帝是指景华帝,而那个为骆氏带来了无上荣耀的皇祖父景霖帝,却成为她一直深恨的人。
“那么,景霖帝当日驾崩也不是药力过猛,回天乏术?”旭祺看见骆氏笑得灿若桃花的脸不禁一凛。
“不错,他并非沉溺于声色犬马被淘尽了身子,以致药石无效,其实早在昭蔼二十年,我便下了杀心——”
是了,那也便是“假太子行刺帝君”一案的真相,而幕后主使,正是景霖帝万分宠爱的骆氏?
旭祺暗自腹诽,骆氏仿佛知晓他所想,苦笑着摇头:“并非我想杀他,只是他欺人太甚——可怜仁儿韬光养晦,欺瞒了所有人装疯卖傻,本也是不喜看见兄弟二人为帝位相残,却被那人以他胸无大志,不堪胜任南景一国之君为由,命令玲珑刺杀。仁儿处处提防,哪里又提防得了最亲近之人呢?”
那次小聚,钧仁没有见着景霖帝时还以为是他体谅自己多时未见玲珑,故意制造二人单独相处的机会,正欲与玲珑倾诉衷肠时,玲珑却忽然刺来,他没有提防,竟被连刺了数下。若非骆氏早有察觉,叫人跟着他暗中保护,又有死士易容扮作他死在当场,怕是根本躲不开这一局。
“什么?曲姑姑与太子?”旭祺讶然,“那,那曲姑姑与太子有私,还为他生了孩子的传闻?”
“不错。玲珑虽与他们两个都交好,但一直以来,却都倾心仁儿,若非想与玲珑携手世外,仁儿也不会枉顾帝位。而她当年坠崖,也并非为了安儿殉情,是因为她亲手杀了自己的心爱之人,良心不安罢了……”
其实这不是道听途说来的稗史。当年的史官夏书命是南景开国以来少有的倔强人,常以死谏言,虽然在卷帙中只余只言片语,而后又被景霖帝贬为庶人流放民间,却在天桥边摆了说书摊,以求真相得以大白。
只是后来世事跌宕,正史被歪曲成野史,旭祺也只是年少出街偶尔听得,才渐渐起了疑。若非手下言之凿凿,连他自己也绝难相信那穷困潦倒的天桥说书先生竟是当日不惧天家威严,敢以死撞柱维护清誉的夏大人。
这样的话……难怪当日顾丞相极力促成曲玲珑取下遗诏,原来依他对事实的了解,定是认为曲玲珑念着旧情,一定会站在景承太子一边。
“那,那个孩子?”旭祺心中思量,蓦然抬头撞上骆氏目光——
“不错,那个孩子,是你……”她一步步迫近他,目光中透出霸道与无奈:“告诉我,祺儿,如若将来柏儿与你为敌,你能否放过柏儿?”钧仁、均安一母同胞如今尚且反目,而旭祺与旭柏本就无血脉牵连,又有争锋相对之势,更难猜测来日如何。
“是。”不知是不是错觉,旭祺隐隐觉得骆氏的神情像极了当日玲珑将他的手托付到二王掌中的神情,“但凭皇祖母心意。”
【玖】
这日旭祺正在御书房批阅奏章,忽听门外高声笑语,见曲语彤形似跃兔蹦跳进来,不禁微微皱眉:“后宫不可干政,你擅自闯进御书房来便是大罪,但朕今日心情好,就罚你……罚你在我这御书房中找出云照国进贡的乌有宝珠,此珠形如鸽蛋,光胜星辰,如若找到,朕非但不罚你,还重重有赏。”
其实房中哪里有什么乌有宝珠?取名“乌有”也是存心戏耍她一番罢了,不料曲语彤听见“重重有赏”却兀自认真。目光四处逡巡,忽似鹞鹰轻轻翻腾,只两三下便取来一个八宝锦盒——
“锦盒藏于藻井之上极隐秘之处,这宝珠啊肯定在里面。”说着不顾旭祺神色倏变,手起手落,“啪”的一声,锦盒机窍洞开,却哪里有什么宝盒?不过一卷明黄绸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