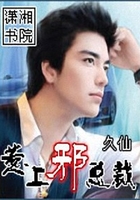“怎么了?”
“有就给我拿过来,没有就算了。”她坏脾气地挂了电话。
“什么东西。”他挑一挑眉,放下电话,去了她的房间。
她横卧在床上,盯着液晶电视,在看一部好莱坞电影。
“到底怎么了?”他坐在床尾,握住她的手。
“头疼、牙疼、胃疼……”
“你就说你哪儿不疼吧。”他依旧毒舌,很没同情心的样子,手却摸了摸她的额头,“还是发烧,记住,下次先说最重要的症状。”
欧阳离有气无力地打开他的手,趴在床上,把脸埋进床单,“你滚吧。”
“去医院吧。”
“你去死吧。不去。”
燕江南笑着走到床头,用座机打电话给一位医生朋友,说了她的症状,问买什么药合适,末了又说:“要不你过来一趟得了。”
那边的人则讨饶道:“刚做完一个大手术,你就让我睡会儿吧。这儿疼那儿疼的那是顽固性的病,得调养。发烧要是不太厉害的话,用白酒按摩就成。”
燕江南轻斥一声:“你睡,睡死你得了。”
朋友不以为意,交待了几句才挂上了电话。
燕江南下楼,从酒柜里选了一瓶白酒,倒了小半碗,拿到楼上,拍拍欧阳离,“你是去医院还是让我给你退烧?”
“都不要。”欧阳离做个手势,“你滚。”
燕江南随手拿过她放在床头的书,把碗放在书上,尚床跨坐在她身上,扯下她的白色外套。
欧阳离这才急了,扭头瞪着他,“就这么给我退烧?哪个蒙古大夫教的你?”
“你怎么自我感觉那么好呢?好像我随时都会把你非礼了似的。”燕江南以眼神示意她去看那碗酒,“朋友说这法子不错,行得通更好。动不动就吃药,你早晚得胃癌。”
欧阳离嘴角一抽,“你这么没口德,死了一定是下拔舌地狱。”却也没挣扎,乖乖趴在床上。他这不好那不好是真的,但平时还是有分寸的,尤其今天她并没惹他……惹到他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燕江南解开她的吊颈小上衣,褪到她腰际,瞥一眼内衣细细的肩带,忍下了逗她的冲动。活蹦乱跳的小豹子变成了小病秧子,换了谁也得大发善心。
酒液浸润双手之后,自她肩颈开始按摩。手下她的肌肤显得愈发细致嫩滑,仿佛儿时吃过的果冻一般。他皱了皱眉,呼出一口气,发现这是正人君子才做得来的事儿……他对她,做不了正人君子。他有点儿后悔了,早知如此,就该把她扔到医院里。
欧阳离亦是难以适应现状,身体绷紧的同时,贴着脸颊的手,抓住了一缕长发,一点点用了力。为了避免尴尬,她刻意转移注意力,侧头看着那一小碗酒,“嗯,这酒不错,好香。”
“给你用,真浪费了。”燕江南轻轻笑着,继而开始和她闲聊,从而阻止自己把注意力都倾注在她的身体上,“你和家人的关系这么恶劣,我觉得你也有责任,脾气太爆,谁受得了你。”
欧阳离从胸腔里哼了一声,“我什么缺点都有,就是没有装可怜那一项,那是欧阳晓的特权。再说了,我对他们够客气了,换了别人,早把他们那套破房子给拆了。”
这话题还是不说为妙,说多了她更生气。燕江南转而问道:“你姑姑对你挺好的吧?”相伴十几年的人,如果对她不好,她应该会想方设法融入家庭,从而得到亲情的温暖。
“挺好的。”欧阳离的语声明显的转为柔和,“我姑姑是我长辈,也是我朋友。她只给建议,从来不说你不能怎样、你必须怎样。有时候想想,我其实挺幸运的。”
“的确,缘分不在长久,她让你愿意一辈子都记得,这才是最难得的。”燕江南的手滑到她腰际,手上的动作有了几分犹豫,不知该轻该重,他没来由的认为女孩子都是很怕痒的。
欧阳离不管他怎样,一点儿反应都没有。可能是思绪陷入了在国外的回忆之中,连身体都放松下来,让他更觉柔弱无骨。他拍了拍她,“据说女孩儿都心软,所以才怕痒。”
“我冷血,用不着你提醒。”欧阳离语气淡淡的。
“你不是,你只是运气不太好。”
欧阳离笑着揶揄道:“你运气好,为什么比我还冷血?”
“你最好还是别在这时候气我,别给我犯罪的理由。”燕江南挑起她的内衣肩带,弹了她一下。
欧阳离立时噤声,不再跟他唱反调。渐渐的,她觉得后背发热,继而蔓延到全身。习惯了他的双手之后,感觉很舒服。她闭上眼睛,觉得神经像是被麻醉了一样,什么也不愿意想,什么也没力气想。真好。
碗里的酒见了底,燕江南侧身倒在她旁边,随手把书和碗放到地毯上,给她拿过枕头和被子,柔声问她:“牙疼胃疼好点儿没有?用不用给你去找药来?”
“不用了吧,困了。”她睁开眼睛,目光朦胧,“你不去睡嘛?”
他拥住她,“确定你没事儿了我再上楼。”
“没事了,有事我再……”
他的手指按住她唇瓣,“睡吧。”
她缓缓地阖上了眼帘,过了好一会儿,把被子分给他一半,挪到他怀里,头枕着他的手臂,“江南,你爱我么?”并没睁开眼睛,似是梦中呓语。
“不爱怎么样?爱又怎么样?”他面对她的一个原则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因为一不留神就会被她钻了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