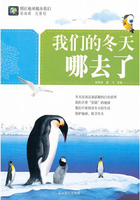听着水溶似含嘲弄的一席话,黛玉一皱眉,淡然一笑道:“民女蒙王爷所救,正思无以为报,只是才疏学浅,怎么堪做这王府的!”
话未说完,便被水溶打断:“本王相信自己的感觉,潇湘姑娘一定不会令本王失望的!”说着唇圈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笃定道:“对吗?”
听着对方意有所指的话语,黛玉一惊,难道,水溶猜到自己用的是假名字了,怀疑自己的身份了?他的话里,分明意有所指。
敛敛心神,佯作镇定地道:“王爷器重,民女自不敢推辞,只是王爷处理的均是朝中大事,这文书一类民女从未接触过,如果有半点疏漏,民女罪无可恕倒在其次,只怕带累的是王爷!”
黛玉的话堂而皇之,水溶却倏尔轻笑,一双眸子波光潋滟,盯住了黛玉的如花娇颜,扯起一抹笑意:“这你放心,不过是要你帮着誊写抄录而已,最后把关的还是本王!本王都不担心,潇湘姑娘又何必杞人忧天呢。”
黛玉蹙着眉,微微一笑:“似乎民女没有推辞的余地了!”
水溶满意地笑了笑,细长的手指轻轻地点着书案,眸子一眯道:“自明晚开始,晚膳后准时到内书房,时间不长,一个半时辰便尽够了!”语气不容置疑,令黛玉没有丝毫的拒绝余地。
黛玉心里一动,这倒是个好机会,自己该抓住才是,遇到哪天水溶高兴,自己顺便可以提出来。想到此,脸上也是一松,微微颔首,眉眼间溢出微微的笑意。
见她水眸闪动,面露轻松,不似往日的清冽,浅笑盈盈,唇角微翘,整个人清雅如菊,水溶心底也仿佛轻松了许多。
自翌日起,黛玉每到晚膳后,便来到内书房,帮着水溶誊写抄录些文书表奏,并不复杂,也不吃力。连着几日,黛玉心里兀自犹豫着,想向水溶打听荣府的消息,但知晓水溶的脾气,心里也委实有些怵头,只得耐心地寻找着合适的时机。
这一日,天气清朗,闲来无事,来到紫姑处,见其忙得不可开交,也不敢打扰,便转身出来,迎头却见墨雨端着一壶茶,见了黛玉便笑道:“潇湘姑娘!”
黛玉停下步子,含笑点头:“怎么,王爷回来了吗?”
墨雨道:“是呢,王爷今天回得早,我得赶紧把茶送过去,潇湘姑娘,我去了啊!”说着向外书房走去。黛玉未做多想,信步往园内而来,
书房内,水溶正与长史柳晏说着什么,柳晏立在地下听着,不时地点头。
水溶看着案头的某处,黑瞳波澜不兴:“贾府的案子到现在也没头绪,父皇虽然亲自下了令,但至今也没审问出有用的口供来。那些似是而非的供词,根本站不住脚,但听父皇的意思,似乎一定要定贾府的罪,先生可知缘由何在?”
柳晏脸上闪过一丝深沉,思忖着道:“殿下,皇上今天又让你掺与此案的审理,想必有他的用意。听殿下的口气,似乎知道了些什么?”
水溶扫了扫他,眯起长眸,眉锋一蹙:“那一日,本王无意中听到了父皇向戴权报怨,你知道父皇提到了谁?”
柳晏眼神一闪,看着水溶没有作声。
水溶脸色一凛,沉声道:“皇上提到了隐太子,本王的皇伯父!”
“隐太子?”柳晏一皱眉,贾家当年是隐太子一党,难不成贾家之事与隐太子有关?不由低声道:“殿下还听到了别的什么没有?”
水溶脸色有些阴沉:“父皇声音虽小,但本王仍听了个七八分,听他话里的意思,这些年他一直在暗中派人查访隐太子的骨肉。另外,他还提到了秦邦业,似乎颇有怒意,骂他欺瞒了这么多年。”
说着一皱眉,墨眸闪着幽幽的光:“这秦邦业,不过是个小小的营缮司郎中,连上朝面圣的资格都没有,为何父皇会对他如此震怒?”
“秦邦业?”柳晏拧着眉,蓦地眸子射出精光,此时看去根本不象王府的长史,倒象是一个深藏不露的高人。他的身份确实如此,虽名义上是水溶的长史,实则是他的智囊。自小看着水溶长大,蒙淑妃器重在水昊天面前美言,但为报淑妃知遇之恩,婉辞了中书令的职位,却甘愿在北静王府做一个长史,职位虽低,但实际才学渊博,见解非凡。一些重大的事水溶均会与他商议,征求此人的意见,故在府里地位却是极高,人人尊重不敢小觑。
水溶神色冷峻,眯了眯长眸:“先生想到了什么?”
柳晏瞅着他一笑道:“秦邦业虽然官职卑微,但此人与贾府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水溶英眉一挑:“哦,说来听听!”
“殿下难道忘了,秦邦业的养女,嫁给了宁府的贾蓉,后来因病去世,王爷还亲自路祭的!”“噢,”水溶若有所思,随即眸子一亮:“先生,你的意思是说?”
柳晏脸色抖然严峻:“这秦邦业是隐太子的人,皇上登上大保后,对隐太子的人甚是优待,所以这一干人等并未予以追究。这秦邦业无子,据说从育婴堂抱了个女婴,后又抱了个儿子,女儿长大后便嫁入了荣府,只可惜这一家三口均命不长。”
停了停闪了闪眸子道:“皇上为何对一个小小的营缮司郎中发怒,殿下难道不觉得耐人寻味吗!”
见水溶若有所思,遂继续道:“据说,隐太子只有一女,隐太子伏诛时那个孩子尚在襁褓之中,后来夭折了!这只是众人的说辞,至于是真是假,那便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