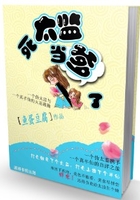少他妈的跟我瞒天过海,他又揪着我的脖领子把我关回去。
被抓来的这些人,十之八九家里人都不知道我们的去向,只能干着急,每个人都忧心忡忡,这么被折腾下去,早晚是个死,而且死无葬身之地,跟老头一样,到最后,只能把我们当失踪人员来处理。只有那个半大小子视死如归,他是个孤儿,整天就是靠小偷小摸过活,一人填饱肚子,一家子都不饿了,死就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留胡子的爷们儿告诉我,你不能轻易把家庭住址告诉给造反派,免得连累了家人,这群王八蛋心狠手辣,像老剧作家这样折磨致死的冤魂,我见过多了。我没回答他,但是他的话我记住了,就是我死,也不能叫我爸我妈和我奶奶跟着倒霉。
造反派叫我们把帽子自己保存,保存好还则罢了,保存不好或是丢了,后果自负,吓得我们都把帽子撂在高处,省得半夜让老鼠叼走。也只有在批斗会之后,我才发现我的帽子上写的是什么,居然是反党反毛主席的急先锋。光看这么个罪名,我就顺着后脊梁沟冒凉气,不寒而栗。看管我们的人有三位,不是瘸子,就是瞎了一只眼,估计都是武斗时的伤号,他们一早晨起来,饿着肚子就叫我们念一遍《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然后就参加劳动,所谓的劳动就是把一个大桶里的硫酸,装进一个个葡萄糖瓶子里,拧紧,我偷着问半大小子,这是做什么用的?他说这是土制手榴弹,扔出去,能把人烧个半死。我又问,装硫酸也不发个塑料手套?留胡子的爷们儿说,你离水龙头近一点儿,一洒在手上,就赶紧用水冲,这样才不至于伤手。我只好照着他的办法,干活时加着十二分的小心。
我们这些人当中,有两个去打扫厕所,脏是脏了点儿,却没有危险。我说我想去打扫厕所,半大小子说,你想得倒美,那是个肥缺,得会溜须会拍马才行。打扫厕所的这二位,打我们跟前过的时候,都扬着脸,高高在上,对我们不屑一顾的样子。半大小子就故意捂着鼻子说,哎呀,哪来的臭味,熏死人了。那二位赶紧走开了。我干上两个钟头,就直不起腰来了,留胡子的爷们儿说,你怎么缺心眼啊,每一瓶就装一半硫酸,出力少,又显得干得多。我一想也对,满满一瓶子的硫酸真要泼在一个人身上,绝对得要了对方的命,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其实就是助纣为虐,要少缺德的话,只得能偷工就偷工,能减料就减料。到吃晌午饭时,干活多的,多给半拉窝头,少干的就少给,病了,没出工的,就饿一顿。我干得不多不少,便仍然给我一个窝头。造反派说,这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半大小子说,这里比劳改队还他妈的凶,劳改队起码不饿你,这里饿死你活该,那个编剧本的老头就是四天没管他饭!
我想,我要是死在这,我爸我妈都找不着我的骨灰。留胡子的爷们儿说,别琢磨死,要活下去,要这么死,也是轻于鸿毛,死得没价值。开头,这里的窝头我吃不惯,里边都是炉灰,半大小子说,这是造反派成心撒在里边的。为了活下去,我嚼也不嚼,就往嗓子眼里掖,省得硌掉牙。留胡子的爷们儿还告诉我,受了多大的委屈,也别发牢骚,这里有人爱打小报告。我问,都落魄成这样了,还打小报告能有他什么好处。有好处啊,留胡子的爷们儿说,可以多给他半勺白菜汤和半拉窝头。他这么一说,从此在大庭广众之下,我都不敢说话了,只能装聋作哑,到处都是奸臣,一不小心,就会掉陷阱里头。到下午,我们可以不干活了,出去挨斗,我突然发现,比较起来,挨斗要比干活轻松得多了,不就是敲个小锣,自己骂自己吗?只要谨记一条,挨斗的时候,千万不能反驳,他们就是说你往天安门扔原子弹,你也点头说是,否则拳打脚踢都是轻的,我们当中有一个中年汉子,造反派说他偷窥女澡堂,他说没有,结果叫围观的群众一顿臭揍,把耳朵给打聋了,还天天闹耳朵底子,流脓。最好的办法是,他们往你脑袋上扣屎盆子,你就接着,要不干脆你就自己替他们扣,准保你能平安无事。
一天到晚,你怎么总也不洗脸,都快叫人认不出你了,我问留胡子的爷们儿。
我就是要叫人认不出我来,留胡子的爷们儿对我说。
为什么呀?我转动着干涩的舌头问他。我能看出,这个人以前一定是个风光过的人,不应该这么邋遢。
为什么?还能为什么?我就是怕丢人,不光丢我一个人的人,还给我祖宗三代的脸上都抹黑!留胡子的爷们儿突然喊起来,我吓了一跳,赶紧过去捂住了他的嘴巴。
天都凉了,你怎么还光个脚丫子?一天,留胡子的爷们儿问我。
我说,鞋被踩丢了,我的挎包跟帽子也不知叫谁拿走了。
仓库门要关上之前,要晚点名,一点还就是三次。
他们为什么要点这么多次呀?我问。留胡子的爷们儿说,他们不识数呗。半大小子警告我,你可不能跑,你要跑,我们都得连坐,挨个跟你受罚。我问,有人跑过吗?半大小子说,没有,要是逮回来非得砸折你的腿不可。点完名,看守嘭地撞上了门,哗啦啦地用铁链子拴上,拴好几遭。
到晚上,我凄然地倚在墙角,走心思,留胡子的爷们儿问了问我的遭遇,我也没瞒他,这时候,半大小子警告我们,你们不许交流案情,攻守同盟。留胡子的爷们儿啐他一口,滚一边去,他又拍了怕我的肩膀,睡一会儿吧,养精蓄锐。我也实在太累了,嗯了一声,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老鼠爬到我脚面我都不知道。
起来起来,半夜有人把我叫醒,跟我一起走。
叫醒我的是那个留胡子的爷们儿。往哪儿去?我问他。
赶紧脱离虎口,不然我们非得叫他们折磨死,他说。
走得了吗?我问他。他竖起一只手指嘘了一声,爬到铲车的驾驶室的上头,一纵身,攀到天窗上。
我尾随其后,也爬到仓库的房顶上。
这头是江边,我们去那头,他弯着腰一个劲儿疯跑,我也不敢多嘴,只得跟着他,我知道,现在要是被造反派抓住,会有什么可怕的结果,所以两条腿不住地哆嗦。
现在我们可以喘口气了,不知跑了多远,他突然停住脚步说。
这是一条背静的胡同。见他如释重负,我知道是脱险了,也松了一口气。我问他,下边我们怎么办?他说,武汉是待不下去了,只能往北走。我问他,为什么非得往北走?他说,我在信阳有个朋友,是在美国留学时的患难之交。
你还留过学?我很新奇。他的年纪,我推算也就三十多岁,可是看上去要大许多,属于未老先衰。
这些鸡毛蒜皮以后再说,我们趁天不亮赶路要紧,他说。
我怎么称呼你?我问他。我不能稀里糊涂地跟他亡命天涯,起码得知道他姓甚名谁、何方神圣吧。
我姓曹,你就叫我曹大哥吧,留胡子的爷们儿笑一笑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就漂洋过海了。
你在美国学的是什么,我问他。
政治经济学,曹大哥冲我挤咕挤咕眼睛,没想到吧?他说,正是抗战期间,烽火硝烟,谁会想去读什么政治经济呀,我偏偏犯神经,大老远的去学那些没用的东西。
我听说政治经济学也是一门很重要的学科,我说。这时候,我已经跟随他穿过汉关码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不等天亮,我们就能出江岸站,那就万无一失了。但是这中间要经过两所大学,现在大学区是最危险的区域,数他们闹得欢。
我之所以回国,是以为我能报效祖国,他说。
那结果呢?我问。他说,结果我闲了十几年,不是让我到船厂下放劳动,就是让我在渡口体验生活,我的专业就这样荒废了。我们俩一边说一边匆匆地贴着道边走,昏黄的路灯这时候显得特别的刺眼,幸好有一半路灯,已经叫造反派和淘气的孩子都给拿弹弓打碎了,还不那么亮如白昼。
你是不是很害怕?他问我。
有点儿,我说。想到我竟然遭遇到这样的飞来横祸,委屈得慌,一股咸味涌上了嗓子眼。你怕吗?我反问曹大哥一句,他仿佛经受不住我探寻的眼睛似的,扭过头去,尽量地不瞅我,等他抬起头来时,我发现他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天一亮就太冒险了,我们只能先躲一躲,夜里再说,曹大哥说。我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只能听他的。
在这之前,我要洗一把脸,曹大哥拉着我到处寻找水龙头,洗个脸,他花了整整二十分钟。
他洗完,我洗,我问他,你不是不洗脸吗,怎么突然间变主意了?
情形不同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凌晨时分的空气清新多了,散发着江水的馥郁气息。我们七拐八拐来到一座辛亥年间建造的楼房前面,他敲敲门,没动静,就又敲了敲,随着一阵踢踢踏踏的脚步声,有人来开门了。我感觉到他的呼吸急促起来。出来一个年轻女人,找谁?她问。当她看见是曹大哥的时候,一下子扑上去,搂住了他的脖子,这么长时间,你躲到哪里去了,找也找不着你?曹大哥推开她,示意我在旁边,告诉她,这是我的小难友。年轻女人伸出手来,跟我握了握,我觉得她的手很软和,也很温暖。进来说话吧,她说,她的脸泛起了幸福的红晕。我估计,她一定是曹大哥的女人,但一定不是跟他扯了结婚证照了结婚照的女人。我们跟着她上了楼。
先给我们这位小兄弟弄点儿吃的吧,他怕是早就饿坏了,曹大哥把脏衣裳都脱掉,扔地下,身上只剩一条裤衩子,还裂个口子。
做一碗挂面汤吧,年轻女人嫣然一笑说。
趁她去厨房的工夫,我问他,这是谁?他说,我女朋友。我很惊奇,你这么大都没成家?他说,她家里不同意。我又问,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这个女人太洋气,太雍容华贵了,跟他的确不般配。
我们是在加利福尼亚认识的,她比我小几岁,曹大哥说。我心说,难怪呢,这个女人也喝过洋墨水。
挂面端来,我跟曹大哥立马狼吞虎咽起来。
年轻女人微笑着坐在一旁,看着我们吃。
这么多日子,你究竟做什么去了?等我们吃完,她才问,我都快急死了。
嗨,说来话长了,曹大哥苦笑了一下。
你睡一觉吧,养足精神,晚上我们还得赶路,曹大哥对我说,你就在这间客厅睡,我去别的地方。他的眼睛里闪着一丝狡黠。凭第六感觉,我知道他们俩准是要做点儿什么,具体要做什么,我不是很清楚,但是绝对属于见不得人的那种。亲嘴是肯定的,亲嘴之后呢,我就实在是想象不出来了……
干那个,就得脱成了光屁股,杜寿林曾经给我形容过。
我蹑手蹑脚地走出客厅,这里一共有三个门,三个门都一模一样,我在走廊里转悠了一圈,不知他们到底是进了哪间屋子。
这时候我听见低沉的哭泣声。
我跟个台湾特务一样把耳朵贴在门缝上,哭泣声中断了,取而代之的是剧烈喘息声,再后来就是女人喃喃的说话声。我想象着她如何扭动着匀称的腰肢,又如何呼扇着两片殷红的嘴唇。我突然觉得自己很无耻,竟做出这么卑鄙的勾当,就踮着脚尖儿溜回到客厅里,躺下,闭上眼,假装睡着了。可是我内心深处隐隐燃烧的那颗小火苗,并没熄灭,我真的嫉妒曹大哥了,他竟然在这么僻静的地方藏了如此美丽的一个女人。
要是秀园在这就好了,我也能亲亲她,她要恼了,最多也就掐我一把,或是瞪我一眼,我不怕,豁出去了。
我歪倒在沙发椅上,一条腿蹬在方桌架上,等胡思乱想累了,就睡了。
月亮都老高了,你也该起来吃晚饭了,曹大哥把我叫醒。
果然,我溜溜睡了一整天,要是不叫醒我,我还能睡。
快来吃吧,不然就都凉了,曹大哥的女人显得更热情,也更漂亮了。她张罗我们坐下,所有的菜都用盘子盖着,打开,有肉,有鸡蛋,还有腊肠,闻起来喷香,我已经很久很久没尝到荤腥了,馋得直流口水。
我们喝一杯酒吧,曹大哥提议。那个女人跟个花蝴蝶似的跑走了,过一会儿,又跟花蝴蝶一样地跑回来,拿着一瓶酒,给我们一人倒一杯,我说我不会喝,曹大哥说,怕什么,是葡萄酒,1946年的法国货。我只好捏着鼻子一饮而尽。
那个女人就讲究多了,她先跟曹大哥碰了碰杯,还当地响一下,说上一句祝你一路顺风,才喝。
很平常的一句话,竟让曹大哥眼窝湿了,他抑制住自己的激动,给我们仨又倒上一杯,来来来,再喝,他说。我照旧一口就干了,一口一口地抿,我受不了,忒辣。他们俩也仍然喝得很雅致,很有派头,却不再说话,只是一味地你瞧着我,我瞧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