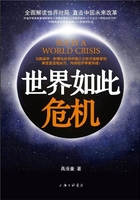我的学校和我的家长所给我的知识反倒有限。在所有的课程中,历史课是我的最爱。但是老师讲的,总跟古书里讲的不一样,简直把我闹糊涂了,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李自成和洪秀全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嘿,石磊,你想什么呢?江晓彤问我。我赶紧终止了我的沉思,我打岔说,我发现一路上,我们遇到的所有串联的队伍,都打着旗子,只有我们不打,我记得我们上次在延安不是买过一面旗子吗?杜亦慌忙从她的书包里找出旗子来,从道边撅个树枝子,当旗杆。江晓彤个头最高,自然棋手应该由他担任。
中途,我们还跟一队中央民族大学的大三学生来个碰头好,本来想跟他们攀谈一阵,可是他们嫌我们是毛孩子,还吹牛说,他们走到哪里,省委书记都得出面接待,哪像我们,跟一群残兵败将似的那么狼狈。叫他们这么一贬,我们都抬不起头来了,直臊得慌。记住了,无论到哪里,也别给咱北京人丢人,临走,他们嘱咐我们。等他们一走远,我们的怒火才熊熊燃烧起来,有什么了不起的,竟敢对我们指手画脚!江晓彤说。杜寿林也说,我们要是跟他们一般大,肯定比他们还威风。我虽然没说什么,但是我的屈辱感一点儿都不在江晓彤之下,我走得比谁都快,把他们远远地甩在后面。你跑这么快干什么,又不打狼,江晓彤在身后气急败坏地喊道。我没停下,依然以急行军的速度前进。
石磊,等我们一下,尤反修招呼我。
我站住了,一屁股坐在地下,因为早晨滴水未进,我早饿得肚子咕咕叫了,我跟尤反修要了半拉烧饼,一口就吞进肚里。尤反修笑着说,你知道你像个什么吗?我反问她,我像个什么?他说,你就像一只追着自己尾巴打转的小猫。
请你严肃一点儿,别耍贫嘴,我面无表情地瞟她一眼,用外交辞令对她说。
是不是你还惦记着人家唐家会呢?尤反修冲我做了个鬼脸,凑近我的耳边低声地问道。我惊讶地瞪她一眼,两手交叉在胸前,谁是唐家会呀,我见都没见过这位?我说。
就是抱孩子的那个女人呀,你装什么傻?尤反修退了退下巴磕。
原来她叫唐家会!相处这么久,我还真的不知道她姓什么叫什么,也不知道她是哪里的人。尤反修说,她是河北人,今年三十二岁,正月初六的生日,在家里排行老六,所以小名叫六儿。尤反修居然什么都知道,现在看来,间谍应该是她的代名词。你是怎么知道的?我问她。是她自己告诉我的,她说。我心说,这个叫唐家会的真不够意思,我对她一口一个姐地叫着,她却什么都不肯跟我说。尤反修说,不怪你不知道,因为你从来也没问过人家。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有点儿沮丧。
一辆插满红旗坐满农民的卡车从我们身边疾驰而过,他们唱着歌,一派斗志昂扬。江晓彤说,看看人家多精神,再看看我们,跟逃荒似的。他重新整队,打着红旗,唱着歌,雄赳赳气昂昂地上路了,很是引人注目,果然,有路过的车停下来,问我们,你们要去哪儿?没等我跟江晓彤回话,尤反修却反问司机,你的车去哪儿?
我的车到宁乡拉化肥,司机笑呵呵地说。尤反修同样笑呵呵地说,你的车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司机晃了晃脑袋说,那好,都上来吧,我捎你们一箍节。
我们正求之不得呢,赶紧攀住车帮,七手八脚地爬上了车,司机说,你们接着唱,不然我会犯困。
仿佛这是个先决条件,我们要是不唱的话,也许司机会把我们赶下车去,我们还得用两条腿追赶人家的汽车轮子。迫于无奈,我们只好拣会的歌,唱了一遍又一遍,不间断。
我的嗓子都冒烟了,杜亦实在受不了,开始打退堂鼓了。坚持,坚持就是胜利,江晓彤鼓励她说。
这条小河里的水可以喝,你们润润嗓子吧,唱这么半天,够干的了,好在司机还挺善解人意,他中途踩了刹车,叫我们两手捧着透明的河水,滋润一下。他自己也喝了个饱。
哎呀,我又想上厕所了,准是喝水喝的,江晓彤说。还没到宁乡,除了我和杜寿林之外,他们的肚子都开了锅,一趟又一趟地往茅房跑。杨东升问我跟杜寿林,你们俩怎么没反应?我说,我们俩都是在农村长大的,到六七岁才进城,喝河里的水喝惯了。看来,继续赶路已经不可能了,我把他们安置在一家小饭馆里,要几碗面条,自己跑到药房去,买跑肚拉稀的特效药,药房是昼夜服务,晚上值班的是个老中医,我把病症跟他介绍完,问他,大夫,他们该服什么药管用啊?老中医嘬嘬牙花子,你最好还是把患者叫来,稍微诊断一下,比较保险。我只好又回去,拉着大队人马来到药房,当他看到我们的阵容如此壮观,不禁有点儿惊讶,但反应也仅限于此。他检查的结果是细菌感染。
江晓彤问,怎么才能迅速根治呢?老中医说,我可以给你们开一服中药,喝下去就见效。我说,我们人生地不熟,到哪里去熬药啊?老中医说,我这可以代客煎药,不过你不许说出去。我纳闷,为什么呀,要是你真把他们几个的病治好,我还打算给你送锦旗呢。他摆着两手说,我靠边站了,只允许我看夜打更……江晓彤铿锵有力地说,你要是治好我们的病,就是为革命作出了贡献。老中医咬咬牙说,好吧,你们等着。他到里间屋熬药的时候,郑建国说,他不会对我们进行阶级报复吧?我想不会,但是为安全起见,我还是尾随着老中医进到里边去,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有些形状可疑的草药,我都要仔细问问:这是什么?具体疗效是什么?有毒没毒?不管怎么样,眼下阶级斗争还是极其复杂的——
你自己先喝一口尝尝,老中医把药端出来,倒进一个个小碗里,叫江晓彤他们喝,怕有意外,我逼着他试一试,没什么异常,我才让江晓彤他们服用。老中医并没怪我,只是笑一笑。
那一晚上,我们就宿在药房里,虽然挤一点儿,但是药房后身有个厕所,随时可以解决江晓彤他们的燃眉之急,而且老中医还能照顾他们。不过,要是我们领导来了,你们万万不能说是我留下你们的,老中医说。那我该怎么说,我问他。
你最好跟他们说,你们是强行进来的,我拦也拦不住,老中医用哀求的目光注视着我。
我答应你就是了,我说。
转天,到药房开业的钟点,江晓彤他们已经见好了许多,药房的经理不但没敢跟我们吹胡子瞪眼,还口口声声地说要向首都的革命小将学习,要向首都的革命小将致敬。临出门,经理还给了我们几盒西药,我付钱,他死活不要,脸上的笑纹简直就像是一朵牡丹。
是歇两天,还是继续前进?我征求大伙儿的意见。
他们都说,轻伤不下火线。嘴硬归嘴硬,但是腿不听使唤,我们排队走了三个钟头,才走出去不到十公里,按这个速度行进,恐怕一个礼拜也到不了益阳。我们现在不叫行军,而叫磨洋工。
我们怎样才能跟当年的中央红军一样,一口气走上它二万五千里呢,我们休息的时候,杜亦天真地问道。
后边有国民党军队追着打,我们走得就快了,我跟她开玩笑说。那时候,什么脚上起泡了,腿肚子转筋了,鞋后跟开绽了,这些不是问题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主要是没逼到那份上,逼上了梁山,林黛玉也照样能打家劫舍。
谬论,别听他的,他说的都是一派胡言,尤反修把杜亦拉到她身边,仿佛怕我把她拐走似的。
这时候,阳光正是一天最充足的时候,女生怕晒黑了,都拿张报纸遮着脸,突然,一阵隆隆的轰鸣声,好似从地底下响起,我们都本能地站住,寻找着轰鸣声的发源地,江晓彤说,不会是什么地方爆炸了吧?难说,最近许多造反派都配备了武器。
我们正迟疑呢,头顶一个炸雷,吓得我们趔趄了一下,接着,劈里啪啦,豆大的雨滴呈四十五度角倾泻下来。
而太阳对此却熟视无睹,依然灿烂。尤反修兴奋地跳着脚嚷嚷着,你们看,太阳雨,太阳雨。雨滴落在她的头上、身上和行李上,她仿佛一点感觉都没有。我过去一把将她拽到树下,你腹泻还没好利索,又想淋病了,发高烧?她冲我吐了吐舌头,指着太阳说,真是不可思议。很快,雨就停了。
这时候一个奇异的景象出现在我们面前,成千上万的青蛙排成队,从马路这头向马路那头进发,它们拥挤着、跳跃着、欢叫着,如此壮观的场面,这辈子我还是头一回见到。马路上仿佛铺上了一层绿油油的地毯。我们每个人都惊呆了,眼睛里堆满了感叹号。我的妈呀,这简直是青蛙大迁徙呀,我说。柳纯沛说,我要是把我的所见所闻都告诉给生物老师,她准不信,认为我是编瞎话。突然,老远来了一辆吉普,我们拼命地摇晃着两只手,叫它停下来,免得轧到青蛙,它大概觉得它的那辆车绝对装不下我们这么多搭车的人,不但没减速,反而踩了一脚油门,呼啸而过,车轮下立刻血肉横飞,我们的尖叫声、蛙鼓声和吉普的发动声搅成一团,惊心动魄,我们许多人赶紧捂上了眼睛,不敢看只有一条腿的青蛙从我们的脚面爬过去……
赶快离开这,赶快,江晓彤挨个催促着大伙儿。
太惨了,太惨了,尤反修喃喃地说。
我们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过青蛙占领区,一直跨过一条铁道,青蛙的踪迹才消失。我们把行李丢在地下,一屁股跌坐在上边,呼呼地喘着粗气。
杜亦呢,杜亦怎么不见了?尤反修大惊小怪地叫起来。
在附近找找,会不会解手去了,我判断。
杜亦你在哪儿呀,杜亦快给我出来,尤反修扯着脖子喊道。
周围一点儿回音都没有,我们不禁担心起来。
半个钟头以后,我们在一条芦苇环绕着的垄沟旁边找到了杜亦,她蹲在那里呕吐,差一点儿就快吐脱水了。见我们来,她想站起来,可是,她的两条腿软得就是不听她使唤。
哎呀,你的鞋跑哪儿去了?尤反修问杜亦。我一看,杜亦确实光着脚丫子。我把它扔了,因为我踩在青蛙的尸体上了,杜亦使劲儿咬着指甲说。尤反修训斥她说,瞧你这点儿出息。江晓彤也说,就是嘛,万一赶上核战争怎么办,难道你要当逃兵不成吗?我说,少废话,赶紧把鞋给她找着是正经,光个脚丫子怎么赶路呀。我们四散开来,在芦苇丛中展开了大规模的搜索,终于在两个不同的地点找到了两只相同型号的鞋,我没直接给她拿过去,而是在小河沟里刷了半天,刷了个干干净净。
给你,我把鞋递给杜亦,快穿上吧,哪踩在什么青蛙的尸体上了,你净瞎说。
杜亦摆弄着她的鞋,很奇怪,她的鞋怎么会这么干净,刚才明明有血污来着。尤反修说,还瞅什么瞅,这么大姑娘,光个脚丫子,也不嫌个寒碜。杜亦的脸腾地一下子红了,赶紧背过身去,把鞋穿上。可是,没人搀扶她,她还是走不动,尤反修说,你呀,真够脆弱的。我悄声对她说,别怪杜亦,昨天下泄,今天又上吐,搁谁,谁也受不了。尤反修说,那倒是。
以前听过很多八路军风餐露宿急行军的故事,总觉得很浪漫,江晓彤小声地对我说。
现在一试,满不是那么回事,对不对?我问他。其实,我也有这么一种感觉。要不是有女生在跟前,我恐怕早哭好几回了,又累,又困,又渴,还叫虱子咬得浑身痒痒,现在,脑袋一沾枕头就着,连想着某个女生摆弄自己鸡鸡的力气都没有了。就这样,我们的青春期提前结束了。数学、物理、化学和地理,都远离我而去,仿佛跟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了,可是,闲下来,我又常常会想起它们来,尽管过去我是那么的讨厌它们。这次出来串联,我并不后悔,我的所得远远大于所失,人是怎么来到这个世上的暂且不说,起码我知道人是怎么走的了。